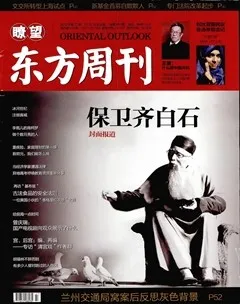胡福林不辭而別
胡福林出于對顧氏學問的崇拜,暗中與顧頡剛建立了親密的師生關(guān)系,想不到這一關(guān)系竟為幾年之后胡在昆明出走埋下了伏筆。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北方高校與科研機構(gòu)紛紛南遷。隨著淞滬戰(zhàn)事吃緊,位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也相繼起程遷往長沙等地。武漢會戰(zhàn)在即,湖南全境震動,遷入長沙的高校與科研機構(gòu)再度遷往昆明。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學所等均隨之遷滇,繼續(xù)開展工作。
1940年,日軍對昆明轟炸日趨加重,為求得一張安靜的書桌,史語所等駐昆明學術(shù)機構(gòu)再一次醞釀搬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派所內(nèi)研究人員芮逸夫親赴四川考察,準備遷入四川南溪縣李莊鎮(zhèn)。
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史語所發(fā)生了一件離奇事件,這便是胡福林(厚宣)的悄然出走。
胡厚宣,河北省望都縣人,1911年12月20日出生在大王莊一個生活清苦的教師之家。福林是早期的名字,抗戰(zhàn)勝利后改為厚宣。此君自幼好學,1928年于河北保定培德中學考入北京大學預(yù)科,兩年后順利升入史學系。當此之時,中研院史語所正由廣州搬到北平北海靜心齋辦公,北大校長蔣夢麟聘請該所的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名流大腕前往兼課,以壯北大文學院聲威,胡福林算是傅斯年等人的學生。
1934年,胡氏畢業(yè),被傅斯年、李濟選拔到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工作。從此之后,胡福林追隨梁思永赴河南安陽殷墟參加了第十、十一次考古工作,并單獨主持了侯家莊西北岡王陵1004號大墓的發(fā)掘,成績顯著,為同人稱道。
殷墟最后三次發(fā)掘(十三次至十五次),共出土有字甲骨18405片,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小屯北地YHl27坑出土的一整坑有字甲骨。當時在工地清理不便,連泥帶土一同運到南京史語所住地——北極閣大廈整理。在董作賓領(lǐng)導(dǎo)下,由胡福林與所內(nèi)技工關(guān)德儒、魏善臣等經(jīng)過八個月的努力方告完成,共清理出有字甲骨17096片——這是殷墟發(fā)掘以來在甲骨文搜集方面最大的收獲。
史語所南遷后,胡福林追隨董作賓整理殷墟出土的全部甲骨,兼做《殷墟文字甲編》的釋文事宜。1940年8月23日,住在昆明郊區(qū)龍頭村的史語所助理員胡福林向傅斯年請假,說是有位叫許心武的好朋友,在重慶北碚替自己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要親自護送家眷赴渝,并說一個月后立即回昆明銷假,需預(yù)支九、十兩個月的薪金以作旅費。傅斯年再三躊躇,最后—咬牙答應(yīng)下來,囑對方快去快回,不要誤了所內(nèi)搬家事宜,胡氏點頭答應(yīng),此事算告—段落。
當傅斯年來到考古組主任李濟住處,把胡福林請假赴渝之事講過后,李濟表示堅決反對,認為全所搬遷在即,許多器物需要整理裝箱,且人手又少,若胡此時離開,對史語所的工作極其不利。
李濟的觀點與傅斯年原本相同,如果胡福林非要離開,待把家遷到李莊安靜下來后再作行動,這樣于公于私都說得過去。本來就有些不情愿的傅斯年經(jīng)此一說,頗有悔意,遂立即找到正在整理器物的史語所考古組助理研究員石肆如,讓他趕快找到胡福林并轉(zhuǎn)達傅、李二人的意見,希望對方暫且留下,待搬到四川后再行赴渝。
石璋如得令,急忙跑到胡氏的宿舍與史語所駐地可能匿身的地點搜尋,想不到尋了半日也不見胡福林的蹤影,后經(jīng)多方打聽才得知胡氏已悄然離開昆明了。而胡離滇競與顧頡剛和錢穆二人暗中操縱有關(guān)。
胡福林在北京大學史學系就讀的時候,具體地說是1931年下半年,時任燕京大學專職教授的顧頡剛受聘為北大歷史系兼課講師,每個星期講幾點鐘的課。作為學生的胡福林出于對顧氏學問的崇拜,暗中與顧頡剛建立了親密的師生關(guān)系,想不到這一關(guān)系競為幾年之后胡在昆明出走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