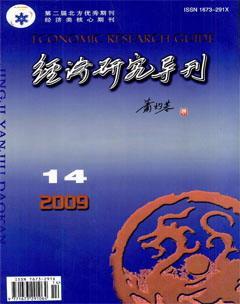假日制度改革對酒店經營的影響及對策
徐東亞
摘要:假日制度改革以來,對旅游業造成的影響顯而易見。酒店經營過程中出現了私人消費增加,本地顧客集中化,需求層次攀升,節日關聯性產品受寵等特點。研究假日期間顧客在酒店的消費特點以及酒店可以采取的措施和對策,將有助于酒店滿足顧客新需求并順利實現利潤目標,并促使其在未來經營中持續穩健發展。
關鍵詞:假日制度;酒店;經營策略
中圖分類號:F29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4-0152-02
自1999年國務院調整公民節假日以來,黃金周為拉動內需、刺激國民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酒店業也因此受益匪淺。但在假日經濟為社會各界所看好時,也暴露了種種問題。因此,2008年1月1日起,國務院修訂后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開始正式實施。節假日中酒店經營業績往往處于頂峰位置,占到全年主營業務收入的相當比重,節假日制度的改革必然對酒店行業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研究假日制度改革對酒店經營的影響特點,并有針對性地設計適銷對路的新產品,促進節假日期間酒店產品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協調,提高酒店行業對新假日制度的適應性是當前的重要課題,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假日制度改革對酒店經營的影響
(一)私人性消費日漸增加
節假日是親朋好友共同聚會的日子,它起到了聯系溝通感情紐帶的作用。新假日制度頒布后,全年休假時間增加,各個假期之間時間趨于分散化,無疑為大眾提供了聯絡親情、友情的機會。從各大媒體報道中可知家庭聚會,親朋好友聚餐在酒店消費已經是習以為常[1]。從目前酒店業經營現狀看,在節假日中家庭聚會、親朋好友的聚會明顯多于平日的商務宴會、會議用餐。種種跡象表明顧客中有血緣關系、情感關系的消費人群在節假日中數量急劇增加。那么這部分酒店消費市場的異軍突起為酒店業未來經營指明了新方向。
(二)周邊顧客帶動本地消費趨勢明顯
本次新增加的五個短假期時間為一天,采取與周末合并休假方法,這種新的時間周期限制和傳統假日本身所反映的文化特殊性,使得絕大部分市民在五個短假期中會選擇城市周邊的自助游或自駕游方式。可見,短途旅游促進周邊客源在本地酒店消費增加,使得本地區消費傾向趨勢明顯。同時,由于本地消費的特殊性,容易產生連帶需求,例如,餐后的各種娛樂活動、夜晚住宿等,這些服務使酒店可開發系列化配套產品,吸引顧客紛至沓來。
(三)需求層次攀升
傳統節假日這些特殊的日子,使聚會意義變得重大。由于外部促銷因素的刺激,節假日成了大眾釋放消費熱情的引爆點。再者,中國人在特殊場合中講究場面、求名動機等內部心理因素摻雜,會使得顧客對消費價格的敏感度有所降低,從而提高消費的心理傾向,促使高檔商品需求相對旺盛。因此,酒店可在特定時段提供系列化的高端消費的產品供顧客選擇,并可在需求旺盛期適當浮動價格,以實現利潤的保證。
(四)節日關聯性產品受寵
本次方案新指定的傳統節日有清明、端午、中秋三個。傳統節日變成法定假日。節日與假日融為一體,使我國的節日傳統風俗得到繼承與發展。這種情況必然會增加傳統節日有重要關聯性的產品消費需求,尤其表現在傳統食品方面。酒店可在傳統節日美食上大做文章,除了推出傳統佳肴之外,在節假日中設計酒店體驗類活動適當進行菜肴創新,如邀請顧客共同參與制作傳統特色食品(中秋的月餅、端午的粽子、除夕的餃子等)。由此借傳統民俗活動拉近顧客與酒店的距離,通過情感溝通來留住顧客從而使節假日活動與酒店產品達到完美契合。
二、新節假日中酒店經營策略
(一)節前促銷,營造氣氛
鑒于旅游業中各子行業之間的關聯性密切,在節假日前夕,酒店與旅行社、酒店與景區結成利益同盟以便聯合促銷,尋求雙贏。不同區域中的酒店也可以進行橫向水平促銷或采取廣泛營銷的方式,依托其他各類分銷渠道如網絡訂房公司、網絡旅行社、全球分銷系統等,并借助話題營銷、事件營銷、活動營銷、品牌營銷等方式做好節前的促銷工作,共同打造出節假日前的促銷氣氛。而對于酒店自身而言,則更具有優越的條件來營造熱情而愉快的氣氛,比如,酒店大堂和餐廳等公共區域是進行假日主題布置的重點,通過裝飾物、海報、背景音樂等突出節日氛圍。另外,員工是最生動最鮮活的氣氛營造主體,是酒店促銷不可忽視的一部分。酒店可設計員工的特殊佩飾或迎賓專用語言或員工促銷的方式,提醒客人消費。
(二)文化為魂,創新不斷
每一個傳統假日都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每一個節日代表著豐富的傳統內涵,其背后蘊藏著無限的商機,可為酒店產品創新提供不斷的靈感。酒店經營者應該在深入了解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的基礎上,加強與文化的有機融合,發現其潛在的商業價值,挖掘文化內涵,比如,除夕的年夜飯,從需求和供給的關系來考慮,完全可以把活動的時間合理延長,推出家庭歡聚套房,來擴大消費等,但是要避免特殊節日的酒店產品流于形式、落入俗套。產品的創新靈感不僅來自于酒店經營者,員工從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是發現顧客消費需求的重要渠道,經營者為鼓勵員工提供創意靈感的積極性,可設立創意信箱,向員工征集酒店節假日經營中好點子,并頒發適當的獎勵。建立為節假日經營思路創新的渠道后,使實際工作有著豐富的源泉。
(三)構思主題,精心設計
節日的時間不同、季節不同、表現內容不同都會促使酒店設立不同的假日主題。因此,酒店在滿足游客舒適、溫馨、方便、安全功能的基礎之上,還要精心設計主題以滿足顧客的物質需求和精神享受。酒店經營者應不斷挖掘當地特色文化的同時對每一個假日需要進行針對性的設計,通過放大文化的符號滲透在酒店的各個層面,對酒店大堂,客房,餐廳,等進行主題化的鋪陳,展示出風情別樣的民俗特色,創造出無法模仿的獨特魅力,比如,清明節以踏青為主題,早餐著重推出清明團,大堂中擺設幾只風箏作為裝飾,端午節研制雄黃酒、邀請客人DIY等方式參與體驗等等,讓客人感受酒店不同的表現形式。主題設計可以深入到酒店的經營活動之中,從員工的服裝到藝術品都可以與主體風格協調起來。
(四)溫馨服務,人文關懷
顧客在消費中越來越重視服務質量,注重酒店對客人的人文關懷,比如細節服務就能讓客人為之感動。從硬件細節角度,部分酒店在節假日中推出的家庭房廣受青睞,這就是體現了從顧客主觀角度出發,讓其感受到家庭的溫馨。長遠來看,家庭系列的溫馨套房可滿足有兒童和老人家庭的需要。再者從軟件上更加可以大做文章,在海口喜來登酒店,酒店每天派出一名高層主管擔任“微笑握手天使”,每天與新入住的客人握手交流,詢問旅途情況、介紹景點交通、提醒注意事項、征求意見并免費郵寄明信片[2]。從服務員培訓工作出發,酒店大力提倡服務親情化,不僅要求服務員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基礎,還要注重對客服務態度和藹可親。此外,通過酒店文化建設努力做到員工與酒店成為一體,各部門信息溝通便捷,各個服務環節有效合作,讓顧客在假日更加感受到賓至如歸的感覺。
(五)整合資源,實現最優
節假日經營期間往往要考驗酒店的資源儲備狀況以及經營者的統籌協調能力。從節日前夕經營者必須要做好資源分配規劃,通過安排達到人力物力的合理配置。建立資源統籌配置假日協調小組,切實做好酒店中物資的準備工作,如活動主題所須的材料是否供應充足,財政預算是否到位,節假日的用工安排是否有充足的可調動的人員等等,使之與本酒店的實際運營能力相適應。同時節假日期間酒店與其物資供應商保持暢通的信息通道,保證完成節假日的目標業績。
三、結束語
新休假制度使得旅游人數的季節分布趨于均勻,從而擴大旅游市場,成為拉動我國經濟的新引擎。對于酒店業要在未來經營中占取主動,不僅要重視休假制度改革所產生的影響,還要根據假日的主題特色及時調整經營策略,正確抓住消費市場特點,適應顧客休閑娛樂需求,開發新產品,搶占新市場,走不斷創新持續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