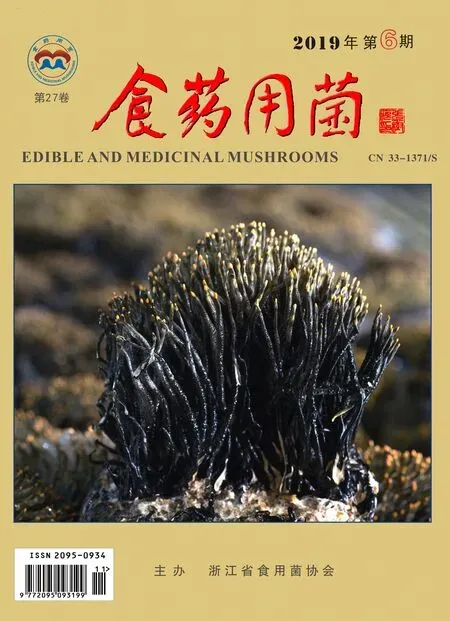野生樺剝管菌馴化栽培初探
杜忠偉 胡志強 亢學平 李 建 王 旭 王 鑫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農業科學院,吉林 延邊 133000)
樺剝管菌[Piptoporus betulinus(Bull.ex Fr.)Karst.]又名樺孔菌、樺滴孔菌、樺多孔菌,市場流通名為“白靈芝”。隸屬于真菌界(Fungi)、擔子菌亞門(Basidiomycota)、層菌綱(Hymenomycetes)、非褶菌目(Polyporales)、多孔菌科(Polyporaceae)、剝管菌屬(Piptoporus)。該菌生于樺樹的樹干或倒木上,主要分布在我國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甘肅、四川、云南、貴州、新疆、西藏、河南、陜西、福建、安徽、湖南等地[1,2]。
子實體中等至較大,無柄或幾乎無柄。菌蓋扁平,扁半球形,近肉質至革質,靠基部著生部分常凸起,大小 4~24×5~35(cm),厚 1.5~9.0 cm,表面光滑,初期乳白色,后呈褐色,有一層薄表皮,可剝離露出白色菌肉,邊緣內卷[3]。樺剝管菌是一種木材褐腐真菌,可分泌纖維素和半纖維素酶,能高效分解纖維素。嫩時可食用,子實體可分離多孔菌酸、蹄菌酸等多種藥用物質,有抑制分枝桿菌、抵抗化膿小球菌生長、抑制小白鼠肉瘤、抵抗小白鼠及猴子的脊髓灰質炎等作用[4,5]。
目前我國未見有人工栽培的報道,而野生的樺剝管菌在民間已有很長的食用和藥用歷史,作為一種藥用大型真菌應該得到重視與開發。因此,我們對采集的野生樺剝管菌進行人工馴化栽培試驗,以期為開發應用研究提供基礎資料。
1 材料與方法
1.1 菌株來源
采集自長白山地區樺樹林中的野生大型真菌,經形態學鑒定,確定為樺剝管菌(P.betulinus)。對子實體進行組織分離獲得菌種,編號為YBHB-1,保存于延邊農業科學院食用菌研究所。
1.2 母種培養基制作
PDA培養基:馬鈴薯200 g/L,葡萄糖20 g/L,瓊脂粉20 g/L,蒸餾水定容至1 L,pH自然。采用20×200(mm)的玻璃試管,接種后放入25℃恒溫培養箱中培養,觀察記錄菌絲的定植時間、長勢、顏色、滿管時間。
1.3 原種培養基制作
按照玉米粒80%、木屑10%、麩皮8%、石膏1%、白灰1%的培養基混合配制,含水量60%。選用750 mL專用菌種瓶裝料,接種后放入25℃恒溫培養箱中培養,觀察記錄菌絲的定植時間、長勢、顏色及滿瓶時間。
1.4 出菇試驗
培養料配方:樺樹木屑76%,麥麩20%,黃豆粉2%,白灰1%,石膏1%,含水量60%~65%。采用15×30×0.06(cm)規格的聚丙烯塑料袋裝料,每袋裝濕料重1.25 kg。裝好后放入高壓滅菌鍋,121℃滅菌2 h,冷卻至30℃以下,轉移至接種室接種。接種后置于25℃培養室,前期避光培養,后期給予適當的散射光促進原基形成,觀察記錄菌絲長滿袋時間和原基形成時間。
形成原基后轉移至出菇實驗室,根據其原始生長環境特點,保持生長溫度不高于25℃,相對空氣濕度為80%~85%,保持散射光照,通風良好,促進子實體生長。觀察記錄子實體的形態特征。
2 結果與分析
2.1 馴化條件下的樺剝管菌菌絲生長
通過對樺剝管菌母種、原種及栽培種的培養發現,其菌絲在PDA培養基中生長速度快,且菌絲潔白、粗壯,少有氣生菌絲產生。原種接種后第2天開始萌發吃料,經過15天左右菌絲基本長滿原種瓶,18天完全長滿瓶。栽培種接種后3天菌絲萌發,35~40天菌絲長滿袋,此時菌袋表面菌絲不濃密但粗壯,部分菌包會吐水,有異味,菌包不緊實,隨著光照的刺激會在菌包表面長出圓球狀的原基(表1)。
2.2 出菇試驗結果
出菇情況詳見圖1。原基形成后進行開口出菇,選擇在長出原基的部位劃口,不要劃傷原基。經過15天左右培養,原基分化形成半圓形子實體。通過比較形態特征,發現其與野生的相似,子實體半圓形,初期顏色潔白,后期在菌蓋表面產生深棕色色素,使菌蓋表面形成深棕色菌皮。菌柄短小,待菌蓋完全形成后測量子實體大小為8~10×5~8(cm),厚度1~3 cm。采收成熟子實體,經烘干后菌蓋表面出現裂紋,稱重為9~20 g/個。

圖1 樺剝管菌子實體形態特征
3 結論與討論
對采自長白山地區的野生樺剝管菌菌株YBHB-1進行馴化栽培試驗,根據原生環境,選用樺木屑作為主要栽培原料,成功獲得栽培子實體。研究發現,其菌絲在PDA母種培養基和玉米粒為主的原種培養基中生長快速,在以樺木屑為主的栽培種培養料中生長正常。菌絲長滿菌袋后,表現菌絲不濃密,菌袋不緊實,易產生黃水,能使木屑培養基腐爛,產生異味。后期在菌袋表面形成圓球狀原基。出菇培養期間發現,該菌子實體生長階段需要充足的氧氣,在18~25℃下均能形成子實體。
劉欣等的研究表明,樺剝管菌對白樺木材具有較強的降解能力,且其腐朽后的木材呈紅褐色,易粉碎[6]。李翠珍等研究表明,樺剝管菌是一種典型的褐腐菌,可分泌纖維素和半纖維素酶,分解木材中的纖維素和半纖維素[7]。根據本研究結果,它是一種分解能力較強的木腐菌。
2016 年,Ma?gorzata Pleszczyńska等報道,樺剝管菌人工栽培獲得成功,并證實人工栽培的子實體與野生的具有相當的抗癌特性[8]。樺剝管菌作為一種藥用真菌,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木材的降解機理、藥用價值及有機污染物降解作用等方面[9,10],未見對其栽培特性的研究報道。我們利用菌株YBHB-1進行栽培試驗,成功獲得子實體,為進一步開發利用樺剝管菌提供了基礎資料。未來將探索研究其最佳生長條件和規模化生產,使之成為一種能廣泛開發應用的藥用真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