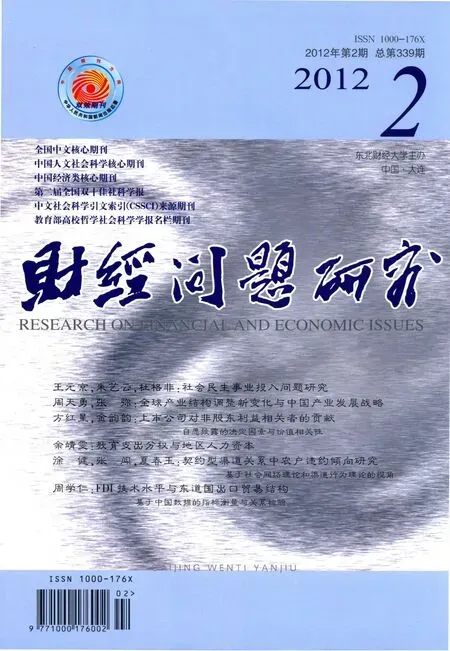FDI技術水平與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
——基于中國數據的指標衡量與關系檢驗
周學仁
(東北財經大學 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遼寧 大連 116025)
改革開放以來,外國直接投資 (FDI)和出口貿易從規模上對中國經濟的粗放式增長發揮了重要促進作用。但在現階段,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急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優化經濟結構,其核心是轉變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生產要素結構和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在此背景下,FDI和出口貿易不僅要從規模上同其他經濟增長方式相互協調,而且要從質量和結構上加強自身優化,即提高FDI技術水平和改善出口貿易結構。但是,如何衡量FDI技術水平和出口貿易結構,二者之間是否存在關聯,中國目前的FDI技術水平和出口貿易結構處于何種狀況,怎樣才能有效地優化這兩個經濟變量等,這些問題仍沒有統一的認識和成熟的研究框架。因此,有必要對中國FDI技術水平和出口貿易結構進行準確地衡量與評價,并對二者之間的作用關系進行研究。
一、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對FDI技術水平的專門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的差別更多地體現在FDI技術水平衡量指標的選取不同。Javorcik等[1]、許羅丹等[2]、Fortanier[3],對不同來源地的 FDI對東道國技術等方面的影響展開了研究。郭熙保和羅知的研究將FDI技術水平作為特征變量之一研究了FDI特征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4]。他們采用了FDI來源國每百萬人中技術人員數的加權平均值來衡量FDI技術水平,權重為相應來源國流入中國的FDI流量占中國FDI流入總量的比重。
與FDI技術水平相比,關于貿易結構的研究則豐富和深入得多。自從Leontief[5]對美國貿易結構進行經驗分析并得出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論”以來,對貿易結構的經驗分析受到了廣泛重視。目前,多數學者認同商品的貿易結構等同于要素的貿易結構[6],并且認識到了國家間的技術差異在解釋貿易結構中的重要性[7]。Trefler在分別假設各國技術結構相同和技術結構不同的基礎上,對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進行了經驗分析[8]。結果顯示,技術差異的引入并沒有使要素稟賦理論被證偽,這一結論得到了許多其他研究的支持[9],也符合Leontief提出的觀點[5,10]。
鑒于技術因素在衡量貿易結構中的重要性,一些學者運用勞動生產率、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標開發出多種不同的貿易結構衡量方法。Grossman和Helpman對技術與貿易的關系進行了系統的研究[11]。Feenstra[12-13]、Feenstra和Kee[14]等,詳細論述了貿易產品的種類及其與技術進步、生產率之間的關系,驗證了貿易產品的種類是決定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差距的重要因素。詹曉寧和葛順奇從出口產品構成、參與世界貿易品的技術含量,以及各國在不同技術含量產品中出口增長的變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國貿易競爭力在全球的位次[15]。關志雄用產品的技術附加值衡量產品的技術含量[16]。Holst和Weiss用技能密集部門與非技能密集部門勞動增加值之比作為權數,提出了顯示勞動技能貿易指數(ELST)[17]。王永齊從資本品和消費品進出口的相對數量角度構造了貿易結構衡量指標,并研究了中國的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18]。Hausmann等提出用“產品對應的收入水平”衡量產品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從而作為產品技術含量的衡量指標[19]。Lall等提出了“復雜性指數”的概念來衡量不同產品的復雜程度[20]。樊綱等通過完善關志雄[16]的貿易結構分析法,用顯示技術附加值賦值原理作為識別貿易品技術附加值高低的理論基礎,提出了四種基于貿易品技術分布的貿易結構分析方法[21]。Rodrik利用編碼協調制度六位碼 (HS-6)產品分類標準計算了中國出口產品的生產率水平,發現中國出口產品的生產率水平大約是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所體現的生產率水平的3倍左右[22]。杜修立和王維國進一步修正了樊綱等[21]的貿易品技術含量指標的權重賦值方法,提出了一套分析經濟體出口貿易技術結構的新方法[23]。魯曉東和李榮林分析了傳統的RCA指數在衡量比較優勢時的優劣,并在構造比較優勢指標的基礎上研究了中國對外貿易結構、比較優勢及其穩定性[24]。楊汝岱和朱詩娥以生產要素密集程度作為衡量貿易品結構的指標,發現中國對外貿易產業和技術結構均呈現較強的階段性特征[25]。施炳展和李沖望利用改進的標準化貿易均衡指數 (NB)和轉移矩陣技術,研究了中國貿易結構的動態演進特征[26]。
現有文獻關于FDI與貿易之間的研究很多,但關于FDI與貿易結構之間關系的研究不多,國內只有少數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江小涓認為,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和技術這類“易流動”的要素在各國之間流動和重組,能夠較快改變各國原有的要素結構和貿易結構。通過引進FDI和購買先進技術等方式,中國在保持勞動力豐富這一特點的同時,迅速增加資本和技術存量,不斷增加出口商品的資本和技術含量。計量分析表明,跨國投資作為各種要素跨國流動的重要載體,對出口增長與出口結構升級具有顯著影響[27-28]。冼國明等[29]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結論。李輝文論述了一國改變要素稟賦的兩種途徑:自身發展導致的變化和國際要素流動導致的變化[30]。
蔣瑛和譚新生的研究發現,FDI對發展中東道國的貿易結構升級和貿易競爭力提高具有正面效應,然而引進FDI并未使中國貿易競爭力得以真正提高[31]。周靖祥和曹勤認為,出口貿易存在巨大利潤空間與政策空間,并促成FDI流入規模逐年擴大;但隨著FDI的流入,中國出口貿易結構并未優化,需要通過政策措施調整FDI的流入規模與方向,進一步實現貿易結構升級[32]。
二、指標衡量與評價
1.中國FDI技術水平的衡量與評價
(1)指標設定
從FDI承載技術因素的特點和FDI流入東道國的過程來看,FDI技術水平可通過來源地的技術水平、FDI在東道國行業技術分布結構和FDI在東道國的實際產出效率三個角度來衡量。與之相對應,可采取如下三個衡量指標:
一是FDI來源地技術指數,即FDI來源地技術指標的加權平均值。來源地的技術指標主要包括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每百萬人口中研究人員數、專利申請數量、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等。①歷年的《世界發展指標》(世界銀行)和《國際統計年鑒》(中國國家統計局)均采用上述四個指標來衡量一國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在綜合考慮數據的代表性和可獲得性等因素的基礎上,本文選取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為衡量FDI來源地技術水平的指標,加權方式為相應來源地的FDI流量占東道國FDI流入總量的比重。即有如下公式:

其中,FTCcountry為FDI來源地技術指數,FDIi為來源地i流入東道國的FDI流量;FDIi為東道國FDI流入總量;techi為來源地i的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
二是FDI行業技術分布結構指數,即FDI在東道國所分布行業的技術水平的加權平均值。其值依據東道國各個行業的技術水平,再以不同行業的FDI流入量所占比重為權重來求加權平均值而得。
三是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用東道國外商投資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來衡量。其值通過計算外資工業企業的單位從業人員所能實現的工業增加值來獲得。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FTClabor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IAVF為外資企業工業增加值;LF為外資企業從業人員數。
如上三種方法分別用于衡量FDI流入東道國不同階段的技術水平特征,三者之間存在著較強的相關性。FDI來源地技術指數,可衡量FDI流入東道國之前的基本技術水平。雖然擁有高技術的國家不一定通過FDI轉移高端技術,但不可否認的是,FDI所轉移的技術水平與來源地技術水平具有較強的相關性。FDI行業技術分布結構指數假定,FDI在東道國各行業上投入的技術均不低于相應行業的平均技術水平。基于此,可通過行業技術水平及FDI的行業分布來衡量FDI在東道國所投入的總體技術水平。但該指數的缺陷是,在實際計算過程中東道國的行業技術水平很難確定。與前兩個指標相比,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更能體現出FDI技術在東道國經濟環境中所發揮的實際效果,而且該指標易于計算。綜合以上因素,本文選擇FDI來源地技術指數和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作為衡量中國FDI技術水平的指標。
(2)指標衡量與評價
首先,選取74個經濟體作為來源地樣本,②74個經濟體包括28個發達經濟體、46個發展中經濟體。經濟體類型的劃分參照了聯合國貿發會議的《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利用公式 (1),計算出1994—2010年中國的FDI來源地技術指數。③本文所有計算過程所使用的數據,均來自各年度《世界發展指標》、《中國統計年鑒》以及聯合國貿易統計在線數據庫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http://comtrade.un.org),有必要進行平減或標準化的數據均進行了相應處理,文中不再贅述。計算結果顯示,來自所有經濟體樣本的FDI技術水平在1994—2005年是逐漸提高的,但在2006—2008年出現了明顯的下降,2008年之后又有所回升。其中,在1994—2010年間,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FDI技術指數總體上呈不斷提高之勢,但來自發達經濟體的FDI技術指數從2001年之后逐漸下降。
其次,選取1994—2010年中國外資工業企業的工業增加值及其全部從業人員數,利用公式 (2)計算出中國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計算結果顯示,1994—2010年,中國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總體上呈上升趨勢,但在2006年之后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被中國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超越。
總體來看,盡管1994年以來中國FDI技術水平的總趨勢是上升的,但在2005—2006年之間,中國引進FDI的技術水平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不僅來自發達經濟體的FDI技術指數明顯下降,同時,中國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相比也不再具有優勢。這兩種計算結果,顯然與關于外資在中國技術優勢的一般認識不符。盡管中國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升值得肯定,但FDI技術水平所表現出來的不良趨勢及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
2.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衡量與評價
(1)指標設定
出口貿易結構的衡量方式是多種多樣的,這主要取決于對出口貿易結構研究的視角、所依據的基本理論與核心要素。本文所要計算的出口貿易結構,主要是指一國出口貿易品的技術分布結構。這種衡量方式,首先需要算出所有產品的技術含量。現有研究通常將產品的技術含量賦值為各國 (或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的加權平均值[16,20,21,19,23]。①樊綱等[21]、關志雄[16]等利用人均GDP來衡量顯示技術附加值的基本思路是:在經濟學中,技術往往是生產率的代名詞;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表示一個國家的技術要素豐裕程度,進而可用勞動生產率來近似替代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一般用平均每個勞動者所創造的增加值來表示,而在忽略了人口結構的差異時,人均GDP可以作為比較各國勞動生產率的指標。這樣,人均GDP就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顯示技術附加值。在加權方式上,關志雄[16]和Lall等[20]以各國出口該產品的世界份額為權重;Hausmann[19]、樊綱等[21]以各國該種產品出口的比較優勢 (進行了標準化處理)為權重;杜修立和王維國[23]以各國該產品在世界總產出中的份額為權重。
其次,通過計算一國所有出口貿易品的技術含量加權平均值得到該國的出口貿易結構指數,其加權方式為各出口貿易品的出口額占該國總出口額的比重。本文在參考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一國出口貿易結構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XTC為一國出口貿易結構指數;QXi為該國產品i的出口額;QXi為該國所有產品的出口總額;ptechi為產品i的技術含量,該指標又有如下計算公式:

其中,yij為出口產品i的第j個經濟體的人均GDP;QXij為第j個經濟體的產品i出口額;m為產品i的出口額排名靠前的經濟體數。在實際計算過程中,本文選取出口額排在前15位的經濟體的人均GDP的加權平均值作為產品i的技術含量水平,因而m=15。
(2)指標衡量與評價
利用公式 (4),本文對1994—2010年國際貿易分類標準 (SITC3)三位數分類下的260種產品的技術含量進行了計算。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和相關經濟體的產品出口額,即可對中國出口貿易品的技術分布結構進行分析和國際比較。
首先,以產品的技術含量為橫軸,以相應產品的出口額為縱軸,可畫出中國出口品的貿易額與技術含量散點圖 (如圖1和圖2所示)。圖1顯示,1994年中國出口貿易品主要集中在中低技術產品上,中等技術產品和高技術產品所占比重偏小;圖2顯示,2010年中國出口貿易品主要集中在中等技術產品上。與1994年相比,2010年中國出口貿易品的技術分布更接近正態分布,由過去“兩頭大、中間小”的分布結構演變成現在的“兩頭小、中間大”的分布結構,說明中國出口貿易結構得到了優化。

圖1 1994年中國出口品的貿易額與技術含量散點圖

圖2 2010年中國出口品的貿易額與技術含量散點圖
其次,按照產品技術含量水平的降序排序,并按順序將產品數劃分成五等份 (依次定義為高技術產品、中高技術產品、中等技術產品、中低技術產品和低技術產品),可分別求出各技術等級下出口貿易品所占比重,從而得出一國出口貿易品在各技術等級上的分布情況。為了進行縱向和橫向比較,本文利用1994年和2010年中國、美國、德國、日本、韓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的數據,計算并畫出中國與相關國家出口貿易品的技術等級分布圖 (如圖3和圖4所示)。圖3顯示,1994年,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的高技術產品和中高技術產品出口比重較大,與之相比,中國中低技術產品和低技術產品的出口比重較大,明顯不具有競爭優勢,但換個角度來看,中國與這幾個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出口貿易互補性還是較強的;在“金磚四國”中,中國出口貿易品的技術等級分布結構要好于印度 (中等技術以下產品出口比重占80%以上),與俄羅斯 (1996年數據)、巴西是相似的,但中國中等和中高技術產品出口所占比重略遜于后兩者。圖4顯示,與1994年相比,2010年中國中等技術產品出口所占比重增加,低技術產品出口所占比重有所減少;同時,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所占比重大幅減少,中等技術產品和低技術產品出口所占比重增加;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技術等級分布與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的相似度進一步提高,但中國在高技術產品和中高技術產品上出口比重低于印度和巴西,低技術產品出口所占比重又高于這兩者。總體而言,縱向上看,中國出口貿易品的技術等級分布結構有所改善;橫向上看,中國出口貿易與發達經濟體的互補性下降,競爭性增強,在“金磚四國”中,中國也面臨較強的出口競爭壓力。因此,中國出口貿易品的技術等級分布結構仍需進一步優化。
最后,利用公式 (3),對1994—2010年中國出口貿易技術結構指數進行計算并繪制發展趨勢圖(如圖5和圖6所示)。根據產品技術含量取值方式的不同,出口貿易結構指數又可分為絕對指數和標準指數,區別在于前者的ptech值使用的是未經標準化的技術含量 (單位為美元),后者的ptech值使用的是經過標準化的技術含量 (無量綱化值)。①由于某個技術含量在一個時期可能意味著高技術含量,但隨著世界技術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另一個時期則可能只意味著低技術含量。對于這種變化,從出口貿易結構絕對指數上是看不出來的,但是,出口貿易結構標準指數因使用了更能體現不同技術含量在不同時期相對大小的標準化值,可以彌補這一缺陷。計算結果顯示,1994—2010年,中國出口貿易技術結構絕對指數呈不斷上升趨勢 (如圖5所示),這一方面得益于中國出口貿易品的技術等級分布結構的確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要歸功于世界技術水平的進步和多數產品技術含量的提高。然而,圖6顯示,1994—2010年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標準指數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僅在個別年份有小幅提高,這說明,在世界產品技術體系整體進步的背景下,中國出口貿易品的技術分布結構并未得到實質性優化,反而有所劣化。

圖3 1994年中國與相關國家出口貿易品的技術等級分布

圖4 2010年中國與相關國家出口貿易品的技術等級分布

圖5 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絕對指數

圖6 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標準指數
三、關系模型構建與實證檢驗
在東道國經濟體系中,FDI技術水平一般是外生變量,它會通過技術外溢、人力資本積累等效應,對東道國內資企業的綜合技術水平產生正面影響。這樣,東道國生產產品的平均技術含量就會得到提升,出口貿易結構就會得到優化。但究竟FDI技術水平對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具有怎樣的作用,需要通過如下實證過程來分析和檢驗。
1.關系模型構建
假設一國經濟體系中只包括兩個企業,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各生產一種產品。那么,該國的出口貿易結構指數就是這兩種產品技術含量的加權平均值,加權方式為兩種產品各自出口額所占比重。即有如下關系式:

其中,XTC為一國出口貿易結構指數;Xf、Xd和X分別為該國外資企業出口額、內資企業出口額和全國總出口額;af和ad分別為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產品技術含量。
設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所生產產品的出口率分別為λf與λd,則有Xf=λfYf,Xd=λdYd。Yf和Yd分別為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總產出,設二者的生產函數滿足如下形式:

其中,Af和Ad分別為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綜合技術水平;Lf和Ld分別為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勞動力人數;Kf和Kd分別為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資本投入;α和β分別為勞動力和資本的產出彈性。假設勞動力和資本可在兩個企業間自由流動,則勞動力和資本分別在兩個企業中的產出彈性相同,因而兩個企業總產出水平的差異主要取決于它們的綜合技術水平和生產要素數量。
假設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產品技術含量可用各自企業的綜合技術水平來衡量,則有af=Af,ad=Ad。那么,將公式 (6)和公式 (7)帶入公式 (5),則可得如下關系式:

將上式進行整理可得如下關系式:

通過公式 (8)可以看出,一國出口貿易結構不僅受到FDI技術水平 (Af)和內資企業技術水平(Ad)的影響,而且受到兩個企業間的出口率之比、生產要素投入之比的影響。
2.回歸模型構建
根據公式 (8),可得關于一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函數關系式如下:

其中,Xfd=λf/λd,Lfd=Lf/Ld,Kfd=Kf/Kd。
根據函數關系式 (9),可構建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與FDI技術水平之間的回歸方程:

其中,c為常數項,ε為誤差項,t為時間,其他變量的含義與衡量指標情況詳見表1所示。

表1 方程 (10)中變量的含義與衡量指標
3.模型估計與結果分析
為了考察FDI技術水平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作用,本文基于1994—2010年中國的相關數據,對方程 (10)予以檢驗。考慮到中國FDI技術水平與出口貿易結構的衡量指標的特殊性和可代表性,將分別檢驗不同的FDI技術水平指標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絕對指數和標準指數的作用。相關變量的數據均經過取自然對數處理,方程估計方法為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利用Eviews6.0軟件輸出估計結果 (見表2所示)。

表2 FDI技術水平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作用的估計結果
從估計結果來看,不同指標衡量的FDI技術水平均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具有非常顯著的正面影響。這表明無論是以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來衡量,還是以FDI來源地技術水平來衡量,FDI技術水平的提高,既可以促進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絕對指數的提高,也可以促進出口貿易結構標準指數的提高。也就是說,FDI技術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優化。
內資企業技術水平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作用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表現。其中,當引入發達經濟體樣本計算的FDI來源地技術水平時,內資企業技術水平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絕對指數有明顯的正面作用;但對于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標準指數,內資企業技術水平表現出一定的負面作用,這種作用在引入發展中經濟體樣本計算的FDI來源地技術水平時也有明顯體現。
另外,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之間的勞動力數量之比,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絕對指數和標準指數均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這說明增加外資企業的就業人數對于優化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是有利的;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的資本投入之比,并沒有表現出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促進作用,甚至有些情況下還具有一定的負面作用。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
1.中國FDI技術水平升中有降,有些變化不符合一般認識
1994—2010年,無論從FDI來源地技術指數來看,還是從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來看,中國FDI技術水平總體上都是提高的,只在個別年份有所下降,但是其中有些變化并不符合一般認識。
首先,按照一般認識,流入中國的FDI技術水平應該是不斷提高的,并且來自發達經濟體的FDI技術水平應高于發展中經濟體。但是,2006年之后,中國FDI來源地技術指數不僅在所有經濟體樣本和發達經濟體樣本上出現了下降趨勢,而且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FDI技術水平還反超了發達經濟體。這是什么原因呢?實際上,來自發達經濟體的FDI技術指數下降,并不意味著流向中國的發達經濟體的FDI技術水平下降,而是由于中國從發達經濟體引進FDI的比重下降所致。根據相關資料,在2006年之前的多年里,中國從發達經濟體引進FDI所占比重一般在35%左右,但從2006年開始,中國從發展中經濟體引進FDI所占比重迅速提高,而從發達經濟體引進FDI的比重一路下降到2010年的17%。同時,在中國引進FDI的發展中經濟體來源地中,來自避稅港地區 (如中國香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毛里求斯、薩摩亞等)的FDI流入量所占比重較大 (近幾年占比在80%以上),但這些發展中經濟體的R&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比較低。因此,盡管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FDI技術指數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并不大,不足以彌補來自發達經濟體FDI技術指數的下降,結果是以所有經濟體樣本計算的FDI來源地技術指數出現下降趨勢。
其次,2006年之后,中國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被內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超越,這顯然不符合我們已經習慣接受的一般認識——與外資企業相比,中國內資企業的生產效率較為落后。但事實上,本文計算全員勞動生產率所選取的規模以上內資工業企業,在研發經費和技術升級改造上的投入力度是逐年加大的。以大中型企業為例,2006年以來,中國內資企業人均科技人員科技經費支出一直保持快速提升趨勢,但外資企業這一指標自2006年之后出現了明顯下降,并于2009年被內資企業超越。因此,在科研經費投入上的此長彼消,是中國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超過外資企業的重要原因。
2.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絕對指數呈上升趨勢,但出口貿易結構仍急需得到實質性改善
通過中國出口品的貿易額與技術含量的散點分布圖,及中國出口貿易品的技術等級分布圖,均可以得出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有所改善的結論。其中,最為重要的變化是中國中等技術產品的出口額占比有較大提高。同時,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絕對指數一直呈上升趨勢,也從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相對于原有水平得到了明顯改善。但是,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水平與美、德、日等發達經濟體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與“金磚四國”印、巴、俄的出口貿易結構相似性有所增強,其結果是中國與這些經濟體的出口貿易競爭必將進一步加劇。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國出口貿易結構變化的同時,其他國家的出口貿易結構也在變化。那么,中國出口貿易品的技術分布結構是否在世界產品科技含量普遍提升的進程中得到實質性優化呢?對此問題,在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標準指數的計算結果中并沒有找到樂觀的答案。自1996年之后,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標準指數總體上呈不斷下降態勢。因此,盡管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在出口規模上表現優異,但其出口貿易品的技術分布結構仍急需止住惡化趨勢,并取得實質性改善。
3.FDI技術水平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優化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通過構建關系模型和回歸模型,本文檢驗了FDI技術水平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作用。結果顯示,不論是用FDI來源地技術指數,還是用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來衡量FDI技術水平,都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指數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因此,中國FDI技術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出口貿易結構的優化。同時,盡管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有較大提升并超過外資企業,但其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優化作用沒有得到驗證,相反,其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標準指數還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這說明,盡管目前中國規模以上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要好于外資企業,但是這種較高的生產率可能更多地被用在了生產較低技術水平產品上。另外,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之間的勞動力數量之比,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有促進作用,而資本投入之比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沒有表現出明顯影響。
總之,目前中國的FDI技術水平仍不高,出口貿易結構尚需完善,但好的方面是,中國FDI技術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優化出口貿易結構。中國要提高FDI技術水平和優化出口貿易結構,應該采取如下對策:一是更加注重引進高技術水平的FDI,提高來自發達經濟體的FDI所占比重,對來自避稅地經濟體的FDI應該加強審核與甄別,避免低技術水平的“假外資”大量流入中國;二是鼓勵外資企業增加在中國的研發經費投入,促進外資企業增加就業人數,提升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三是鼓勵和引導內資企業生產更高技術水平的出口產品,支持中國制造產品建立自己的國際高端品牌和國際營銷網絡,提高出口貿易品附加值和增強其國際競爭力;四是進一步完善國內的科技創新體系,增加對各領域的研發經費支持,提高各類企業的創新能力,進而從根本上改善中國出口貿易品的技術分布結構。
[1]Javorcik,B.,Saggi,K.,Sparetranu,M.Does It Matter where You Come From?Vertical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Nationality of Investors[R].Working Paper(3449),2004.
[2]許羅丹,譚衛紅,劉民權.四組外商投資企業技術溢出的效應比較研究[J].管理世界,2004,(6):14-25.
[3]Fortanier,F.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Host Country Economic Growth:Does the Investor's Country of Origin Play a Role?[J].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2007,16(2):41-76.
[4]郭熙保,羅知.外資特征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J].經濟研究,2009,(5):52-65.
[5]Leontief,W.Domestic Production and Foreign Trade:The American Capital Position Re-Examined[R].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53.
[6]Vanek,J.The Factor Proportions Theory:The N-Factor Case[J].Kyklos,1968,21(4):749-754.
[7]Helpman,E.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999,13(2):121-144.
[8]Trefler,D.International Factor Price Differences:Leontief Was Righ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6):961-987.
[9]Davis,D.R.,Weinstein,D.E.,Bradford,S.C.,Shimpo,K.Using International and Japanese Regional Data to Determine when the Factor Abundance Theory of Trade Work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3):421-446.
[10]Leontief,W.Factor Propor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Trade:Further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6,38(4):386-407.
[11]Grossman,G.M.,Helpman,E.Technology and Trade[A].Grossman,G.M.,Rogoff,K.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M].Amsterdam:North Holland,1995.
[12]Feenstra,R.C.New Product Varie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Pric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157-177.
[13]Feenstra,R.C.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Theory and Evidenc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2.
[14]Feenstra,R.C.,Kee,H.L.Export Variety and Country Productivity[R].NBER working paper 10830,2004.
[15]詹曉寧,葛順奇.出口競爭力與跨國公司FDI的作用[J].世界經濟,2002,(11):19-25.
[16]關志雄.從美國市場看中國制造的實力——以信息技術產品為中心[J].國際經濟評論,2002,(7-8):5-12.
[17]Holst,D.R.,Weiss,J.ASEN and China:Export Rivals or Partners in Regional Growth?[J].The World Economy,2004,27(8):1255-1274.
[18]王永齊.對外貿易結構與中國經濟增長:基于因果關系的檢驗[J].世界經濟,2004,(11):31-40.
[19]Hausmann,R.,Hwang,J.,Rodrik,D.What You Export Matters[R].NBER Working Paper(11905),2005.
[20]Lall,S.,Weiss,J.,Zhang,J.The‘Sophistication’of Exports:A New Trade Measure[J].World Development,2006,34(2):222-237.
[21]樊綱,關志雄,姚枝仲.國際貿易結構分析:貿易品的技術分布[J].經濟研究,2006,(8):70-80.
[22]Rodrik,D.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R].NBER Working Paper(11947),2006.
[23]杜修立,王維國.中國出口貿易的技術結構及其變遷:1980—2003[J].經濟研究,2007,(7):137-151.
[24]魯曉東,李榮林.中國對外貿易結構、比較優勢及其穩定性檢驗[J].世界經濟,2007,(10):39-48.
[25]楊汝岱,朱詩娥.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與競爭力研究:1978—2006[J].財貿經濟,2008,(2):112-120.
[26]施炳展,李沖望.中國貿易結構在改善嗎?——基于產品周期理論的分析[J].財貿經濟,2009,(2):89-95.
[27]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8]江小涓,等.全球化中的科技資源重組與中國產業技術競爭力提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29]冼國明,嚴兵,張岸元.中國出口與外商在華直接投資[J].南開經濟研究,2003,(1):45-48.
[30]李輝文.現代比較優勢理論的動態性質——兼評“比較優勢陷阱”[J].經濟評論,2004,(1):42-47.
[31]蔣瑛,譚新生.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外貿競爭力[J].世界經濟,2004,(7):51-54.
[32]周靖祥,曹勤.FDI與出口貿易結構關系研究(1978-2005年)——基于DLM與TVP模型的檢驗[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9):2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