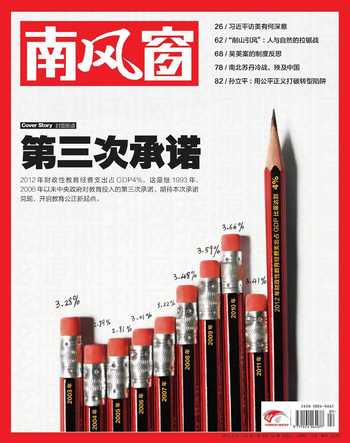四川平武:災(zāi)后重建農(nóng)業(yè)補貼之爭
燎原

“平武縣林業(yè)災(zāi)后重建資金,基本由林業(yè)局集中安排給所謂業(yè)主,由他們在公路邊象征性種幾畝應(yīng)付驗收時照相之用,騙取災(zāi)后補助款,有的根本就沒實施。”45歲的卿皇玉說。她是四川省平武縣宏宇核桃專業(yè)合作社的法人代表。
平武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國家確定的10個重災(zāi)縣之一,災(zāi)后重建的過程中,由河北省對口援建,扶植當(dāng)?shù)匕l(fā)展核桃、中藥等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但是,在扶植資金的分配上,卻出現(xiàn)了諸多問題,以致沒有拿到補助的人紛紛出來揭露套取國家災(zāi)后重建資金的種種潛規(guī)則,卿皇玉就是其中一個,她把實名舉報信寄給了四川省紀(jì)委等部門。
“這個事,省長已經(jīng)簽字,省紀(jì)委、財政廳也已經(jīng)介入調(diào)查,但省里還沒發(fā)布調(diào)查結(jié)果,作為被調(diào)查單位,不便對外發(fā)布。”今年1月初,在平武縣采訪期間,該縣林業(yè)局局長林昌斌向《南風(fēng)窗》回應(yīng)稱。
除了核桃之外,平武縣的中藥等產(chǎn)業(yè)補助也有類似問題。補助資金分配的不透明,讓當(dāng)?shù)氐姆N植大戶們頗多怨言,也把災(zāi)后重建的國家政策和資金在基層落地時的問題暴露于世。
核桃補助給了誰?
平武縣地處四川盆地的西北邊緣,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3萬多人傷亡,大量房屋倒塌。在災(zāi)后重建中,核桃、中藥材、茶葉和纖維林,被確定為四項特色產(chǎn)業(yè)予以重點扶持。
卿皇玉原本是四川內(nèi)江市隆昌縣人,汶川地震后,正是看重這些極重災(zāi)區(qū)在重建過程中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的機會才來到平武投資核桃產(chǎn)業(yè)。核桃種植在平武有悠久歷史。汶川地震后,平武縣專門制訂了《關(guān)于加快核桃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實施意見》,重點扶持龍頭企業(yè)、專合組織,扶持資金來源于中央林業(yè)災(zāi)后重建資金、河北援建資金和平武縣本級財政投入。
卿皇玉通過合作社的形式,跟當(dāng)?shù)卣按迕窈炗唴f(xié)議,租用土地,與村民合作建設(shè)核桃種植基地,到現(xiàn)在,基地已經(jīng)拓展到3萬畝,遍及平武縣的平通鎮(zhèn)和平南鄉(xiāng)12村。據(jù)她介紹,已種植的有1.3萬畝,是平武縣現(xiàn)有5個核桃合作社中規(guī)模最大的。
根據(jù)當(dāng)?shù)卣嫉南嚓P(guān)文件,核桃產(chǎn)業(yè)扶植資金總計超過869萬元,并規(guī)定了詳細的補助辦法,比如基地建設(shè)驗收合格后,每畝補300元;品種改良驗收合格后,每畝補100元;種苗基地建設(shè)50畝,驗收合格后每畝補1萬元……此外,品種改良、統(tǒng)防統(tǒng)治、加工企業(yè)補助、技術(shù)培訓(xùn)和專合組織建設(shè)等,也有補助。
“整個平武才18萬人,我的基地就涉及2000多農(nóng)戶,1萬農(nóng)民。”卿皇玉說,“可我卻拿不到分文核桃補助。”平武縣林業(yè)局作為核桃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責(zé)任單位,掌握著核桃項目實施和資金安排的權(quán)力。所以,卿皇玉把林業(yè)局作為重點舉報對象,她說,林業(yè)局安排的很多業(yè)主,很多就是在公路邊象征性地種幾畝應(yīng)付驗收,“少種多報”,甚至有的根本就沒實施,卻照樣套取補助,在她的舉報信中,還點到鎮(zhèn)、村和實施者名字并配了圖片。
不過,平武縣相關(guān)部門否認了這些舉報。“我們監(jiān)管很嚴,沒出現(xiàn)問題。”縣紀(jì)委書記雷仕會對記者說。林業(yè)局總工程師唐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說,“補助的獲取是按程序走,只有被納入產(chǎn)業(yè)發(fā)展扶持對象,才有機會獲取。”在唐光看來,卿皇玉不過是個賣苗子的,就給村民發(fā)點核桃苗子,就要51%的分成,管理、技術(shù)和服務(wù)都跟不上,“作為產(chǎn)業(yè)發(fā)展,應(yīng)看重怎么發(fā)展,而不是沖著補助來”。
“什么程序!其實就是‘按關(guān)系走。”卿皇玉則說,誰有關(guān)系誰拿走項目實施,之后少種多報或不種也上報,官商勾結(jié)套取補助資金。她舉了一個自己的例子:2009年2月,她和平通鎮(zhèn)椒子山村簽訂一份協(xié)議,椒子山村將1500畝的耕地(包括荒地)給卿種植核桃。但同年8月,平通鎮(zhèn)政府和另一梁姓業(yè)主簽合同,又將椒子山村的地給了這位梁老板實施,種植面積是3000畝。
“號稱3000畝,實際不過1100畝。”卿皇玉說,整個椒子山村可耕種的土地是900畝,外加荒地600畝,總共1500畝。她記得,當(dāng)時和村民簽協(xié)議時,椒子山村的村干部告訴她“全村就這么多地了,除房前屋后剩點種菜的,所有地都給你了”。
卿皇玉經(jīng)過調(diào)查后還得知,平通鎮(zhèn)政府和梁某簽的合同是低效林改造,但低效林改造沒有補助,“所以他們就把核桃樹苗栽到我基地,我已實施的200畝基地,也被搶去套取國家補助”。
不過,她的這些說法,現(xiàn)在椒子山村也不認可了。村支書龍仕培說,椒子山全村101戶334人,耕地(包括荒地)是4800畝,其余的是林地,梁老板的基地是通過政府立項,實施有3200畝,目前申請國家補助是2500畝,沒有占卿皇玉的基地。對龍仕培的反水,卿皇玉稱:“能理解他,因為有利益共同體的關(guān)系和來自上級的壓力。”
平武縣政府官網(wǎng)關(guān)于該縣的介紹顯示,全縣耕地面積41萬畝,農(nóng)業(yè)人口人均占有耕地2.55畝。采訪中,另一位知情人也向記者分析,椒子山村不大可能有4800畝耕地,平武縣耕地平均最多就是每個人3畝左右,即使以人均3畝計,椒子山全村334人最多也就1000多畝。
對“少種多報”的問題,唐光回應(yīng)說:“面積是用衛(wèi)星測量的,且基地不限于某一地方,基地面積比較分散,卿皇玉舉報時拍下發(fā)到網(wǎng)上的照片,其實只拍了部分基地。”記者提出查看基地具體面積等相關(guān)資料時,林業(yè)局則以“目前省紀(jì)委已介入調(diào)查,不好對外發(fā)布”為由,拒絕了要求。
五花八門的“套取法”
與核桃種植類似,在平武縣另外一個重點扶植的中藥材產(chǎn)業(yè),補貼資金引發(fā)的紛爭同樣很多。根據(jù)平武縣公布的《關(guān)于加快中藥材產(chǎn)業(yè)化發(fā)展的實施意見》,2010年至2012年,平武共安排1710萬元用于扶持中藥材產(chǎn)業(yè)化建設(shè)。
唐術(shù)平是平武縣政協(xié)委員,同時也是大橋鎮(zhèn)雷竹種植專業(yè)合作社理事長,是當(dāng)?shù)赜忻闹兴幏N植大戶,2008年還曾被平武縣委縣政府授予“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經(jīng)營營銷大戶”。可現(xiàn)在他也是一分錢補助都沒拿到,因此怨言甚多:補助資金的發(fā)放大都是“量體裁衣”—為方便套取而設(shè)門檻,結(jié)果“不合格的變成合格,合格的變成不合格”—如來自四川簡陽的徐某,地震后在平武辦的兩家中藥材科技開發(fā)有限公司,平武全縣關(guān)于川烏(一種中藥材名稱)的資金補助,基本都被徐某的公司領(lǐng)完了,徐高價賣種子給百姓,但收成時卻不回購,導(dǎo)致川烏爛在地里沒人收,政府卻扶持這樣的公司,讓他們領(lǐng)取高額的補助金。
“災(zāi)后重建資金應(yīng)用在刀刃上,要補助真正的生產(chǎn)者,而不是給那些專門套取國家資金的假生產(chǎn)者。”在唐術(shù)平和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眼中,一些公司“打幾根柱子,蓋幾間樣板房,挖幾個用于泡藥材的池子”,就去套取建廠資金、技改資金等災(zāi)后重建資金,“這些空殼公司平時不生產(chǎn),有人下去檢查時,才裝模作樣叫人搞一下”。
另一名政協(xié)委員則揭秘了重復(fù)套取的手法,如某中藥材公司在平武縣黃羊鄉(xiāng)草源村有厚樸(一種藥材)生產(chǎn)基地,每畝獲補300元,同時,在該地塊種烏藥,再一次重復(fù)計算,每畝又補300元。同樣還是這地塊內(nèi),又種蓮花白(包心菜),農(nóng)業(yè)資金每畝又獲補助100元。此外,因集中農(nóng)民土地統(tǒng)一經(jīng)營,這個老板還可獲得每畝300元的土地流轉(zhuǎn)費。
“重復(fù)計算領(lǐng)取補助外,還將荒山納入申領(lǐng)土地流轉(zhuǎn)費—其實,只有耕地才有土地流轉(zhuǎn)費,荒山荒坡是沒有流轉(zhuǎn)費的。”該政協(xié)委員說,他們這樣重復(fù)套取國家資金,沒有過硬的關(guān)系是不可能辦到的,既得利益者已形成一個緊密的網(wǎng)絡(luò)和利益鏈。
唐術(shù)平也說:“很多補助對象成了個別領(lǐng)導(dǎo)的利益代收人,有的企業(yè)沒補助就活不下去,存在意義就是要補助。”
平通鎮(zhèn)新元村毛山社社長張定興,地震后搞了個特種生態(tài)野豬繁殖基地,養(yǎng)豬場里養(yǎng)了100多頭野豬,但養(yǎng)豬場建設(shè)等費用全是自己支付,沒得到災(zāi)后產(chǎn)業(yè)發(fā)展資金的補助。“要拿補助,得送禮、得找關(guān)系。”張定興說。
而據(jù)記者了解,地震后,有個人在大橋鎮(zhèn)大安村新建了一個養(yǎng)殖場,就得到了政府補助。“這家養(yǎng)殖場養(yǎng)的牛不多,為應(yīng)付驗收,他甚至向親戚朋友借牛放到養(yǎng)殖場里。”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協(xié)委員反映。
據(jù)悉,這名養(yǎng)牛大戶的另一身份是平武縣大橋鎮(zhèn)畜牧獸醫(yī)站的負責(zé)人。在平武縣大橋鎮(zhèn)大城村曾當(dāng)了33年村支部書記的趙興義也感慨,補助資金不是落實給“種、養(yǎng)殖戶”,而是落實給了“關(guān)系戶”。
針對補助發(fā)放中的種種亂象,記者前往平武縣財政局進行核實,局長董曉宇表示:“確實有可能出現(xiàn)這種情況,(接下來)如果發(fā)現(xiàn)實施和規(guī)劃不相符或?qū)嵤┎坏轿坏模瑢⒉唤o予扶持金或責(zé)令整改到位。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反映屬實的,絕不手軟。情節(jié)嚴重的,嚴肅處理。”
被忽略的監(jiān)管領(lǐng)域
汶川地震之后,平武這樣一個極重災(zāi)區(qū),在遭受慘痛傷亡的同時,也迎來了國家各級部門的大量援建資金。在2010年四川省“兩會”上,時任平武縣縣委書記劉少敏透露,一年多來,平武縣的災(zāi)后重建投資達到120多億元,其中中央和對口援建省河北投入的資金就達到70多億元,這個數(shù)字比新中國成立以來平武縣投入的資金總和還要多。
事實上,對于大量援建資金的安全問題,從一開始,中紀(jì)委、國家審計署等就曾下發(fā)過各種文件,確立了監(jiān)管制度,過去的3年多里,也曾發(fā)現(xiàn)了很多問題。
以平武為例,2010年4月出版的四川省委機關(guān)刊—《四川黨的建設(shè)》,在介紹四川省紀(jì)委駐平武縣監(jiān)督檢查組“成績”時透露,經(jīng)一年多的監(jiān)督檢查,有108家的違法違規(guī)企業(yè)和監(jiān)理公司受到行政處罰,3家企業(yè)被取消中標(biāo)資格,罰金達310余萬元。
對口援建省的審計“成效”反映出的問題也觸目驚心。河北審計廳發(fā)布《河北省對口支援平武縣災(zāi)后恢復(fù)重建跟蹤審計結(jié)果公告(第4號)》稱,截至2011年5月底,平武縣部分援建項目施工單位高估冒算,虛計多計工程價款結(jié)算金額3.11億元。2011年11月15日,河北省審計廳副廳長李樹淼作客河北新聞網(wǎng)時透露,河北省對口支援平武縣災(zāi)后重建中,累計跟蹤審計108個項目,節(jié)約援建資金及挽回損失累計8.91億元。
不過,紀(jì)委和審計部門重點介入的大都是工程建設(shè)領(lǐng)域,災(zāi)后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發(fā)展過程中的各類激勵性、引導(dǎo)性補助資金則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但相較于道路、房屋等基礎(chǔ)設(shè)施而言,這類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扶植項目才是真正走出災(zāi)難陰影和生活困境,謀求長遠發(fā)展的利器。但這些項目從實施到資金監(jiān)管,主要由縣政府及相關(guān)部門推進,一般是由一個農(nóng)口部門負責(zé)一至兩個產(chǎn)業(yè),鄉(xiāng)鎮(zhèn)具體組織實施,完成后由縣委農(nóng)工委、監(jiān)察局、審計局、財政局等部門和實施的鄉(xiāng)鎮(zhèn)對項目進行驗收。
平武縣某局一名官員向記者透露,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的很多項目大都被地方權(quán)貴階層,以“分豬肉”的形式下放到鄉(xiāng)鎮(zhèn)實施。為什么這么多實施的企業(yè)和個人都是外來的呢?因為在后續(xù)出現(xiàn)爛攤子時,外來老板更容易卷鋪蓋走人,也不會影響在當(dāng)?shù)貫楣僬叩氖送尽^去退耕還林,也采取外來老板主導(dǎo)的模式。
“本地化實施、驗收,缺乏外來權(quán)力部門監(jiān)管,加上操作不透明、缺乏村民的主動參與,無法發(fā)揮村民的監(jiān)督作用。”采訪中,諸多受訪者道破了災(zāi)后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在當(dāng)?shù)毓賵鐾七M和監(jiān)管的困局,“擁有利益共同體的部門和鄉(xiāng)鎮(zhèn)間,彼此相互關(guān)照,許多驗收成了走過場”。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農(nóng)業(yè)合作社組織,事實上,也都是徒有其名,在基層官員的扶植下,外來投資者占據(jù)了絕對主導(dǎo)權(quán),農(nóng)民在其中淪為配角,也難以真正享受到國家的諸多補貼。
在上無政府強力監(jiān)管,下無村民有效參與的狀況下,一些在災(zāi)后重建中本應(yīng)發(fā)揮巨大作用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扶植政策和資金,問題不少,滋生了諸多不滿與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