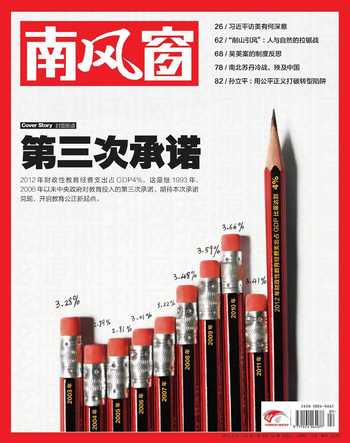鋼鐵業的寒冬
李威

春節剛過,鋼鐵業儼然成為最鬧心的行業。盡管去年第四季度已被看空和質疑,然而以鞍鋼股份為先,暴露出來的行業虧損情況仍然震動市場,行業堪憂。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去年其會員企業產品銷售利潤率在2.55%左右,連續兩年低于3%,在平均利潤6%左右的工業行業中排名墊底。
在“高產量、高成本、低效益”的帽子下,這并不是行業首陷泥淖。鏡頭向后,在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行業因為類似的原因,出現同樣慘烈的景象,不過很快復蘇到來。此次面臨不同的內外環境,行業是否能在短期內走出低谷,或者就如首鋼老總朱繼民所言剛剛進入寒冬?
轉折入冬?
日前,鞍鋼股份發布公告,預計公司去年約虧損21.15億元,A股和H股股價雙雙大跌。自1997年上市后,鞍鋼股份從未出現過年度虧損,2010年,公司盈利23.58億元。而今年,鞍鋼股份并非個案。
如韶鋼松山預虧約11.7億元,首鋼股份預減利潤96%,都成了鞍鋼股份的“難兄難弟”。令人頗感突然的是,在上半年平穩甚至小步快跑的局面下,四季度行業業績卻突然變臉,鞍鋼股份前3季度盈利2.32億元,添上第四季度的數據就變成了巨虧,77家大中型鋼鐵企業最后3個月的平均銷售收入利潤率分別約為0.48%、0.43%和1.04%,其中虧損企業在9月份為9家,年末該數字已接近30家。
鋼價大跌是“淪陷”的導火索,查閱鞍鋼股份相關資料,公司去年10月份產品出廠價均保持穩定,而在11月和12月,產品價格最高下調幅度達500元/噸。而高價鐵礦石、融資成本高、同質化競爭……這些老生常談的行業頑疾被視為罪魁禍首。
然而首鋼發展研究院顧問戴國慶認為,此次不同于2008年,這次轉折真要開始了,“從同比和環比數字看,鋼鐵行業的表現尤其是第四季度的表現近10年罕見,10月份利潤率數據創歷史新低。而且國家去年并未像前兩年一樣,對行業大念節能減排等政策緊箍咒,目前的態勢是市場自我調節的行為,這是行業積累到一定程度的轉變,鋼鐵行業的峰值真要到了。”在業界,鋼鐵行業的峰值充滿了戲劇性,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粗鋼產量躍過1億噸關口后,就有學者喊峰值到了,后來每到產量過“關”時,峰值說便如影隨形。
但近幾年,無論是學者還是政府部門幾乎無人再喊峰值,因為一喊就錯,就連鋼鐵業“十二五”規劃,也只是給出一個7.1億到8.2億噸的峰值預測范圍,時間區間則在2015年到2020年。戴國慶之所以提出來,是因為他覺得這次絕不是“狼來了”的翻版,“我國粗鋼產量自2000年以來,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十幾二十的速度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計算,去年的粗鋼產量已約為6.83億噸。從我調研的企業和主要省份看,這個數字至少還要再上浮10%,即約7.5億噸,才是目前行業真實的產量數據”。
由此,戴國慶估計我國人均年粗鋼產量已超過570公斤,而國際上公認的粗鋼年人均產量在400公斤到600公斤即為巔峰,“何況我國還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在農村”。而未來,再難以出現“4萬億”這樣讓鋼行業“高歌猛進”的利好,市場需求態勢非常不明朗。在去年行業一片“哀鴻遍野”之時,戴國慶參與一份給首鋼高層的內參寫作,提出“鋼鐵業即將進入寒冬”:“應該說,行業已經接近峰值,之后將長期調整。綜合相關下游行業的形勢,今年,我認為鋼產量極有可能是零增長或負增長,但也不排除出現微量如2%或3%的增長,最難的日子還在后面。”
糾結的“工具”
今年,唯一讓行業感到輕松的或許是地方政府換屆。目前我國大中型鋼鐵企業央企不超過5家,其余均為地方政府控股或參股的企業,被戴國慶稱為“體制改革最滯后的行業之一”。
如今,像寶鋼集團、河北鋼鐵集團這些大家伙年產粗鋼都在3000萬噸,投資以億為單位,職工以萬計數。對地方政府而言,這儼然就是一只天生會下金蛋的“雞”。戴國慶表示:“地方政府既缺錢又缺項目,還缺稅源,還想做大GDP,所以地方政府普遍以大股東的身份或行政干預讓鋼廠從銀行貸款,擴充產能,一舉三得。”這種能量被“4萬億”成倍放大,特別是隨著高鐵和房地產的推進,在2009年和2010年,粗鋼產量在4.8億噸的龐大基數下依然保持兩位數的增速,在2010年年產達到約6.33億噸。
這種體制之下,催生多大的產能泡沫不足為怪,企業也難談效益。河北某一鋼企的高管表示:“當地政府要我們反哺地方,出資投建一個幾億元的文化項目,我們八竿子打不著的行業,不過還得投。現在我們這些企業最大的難題不是產能過剩什么,而是擺脫地方政府的控制,我們能夠自主經營,而不是被當作一個棋子,一個不講效益的企業怪物。如果能盡快上市就好了,對比我們的同行,股權多元化后,公司的運營主動權千差萬別。”熊市之下,這種對比更為明顯,在虧損大軍中,如建龍鋼鐵、國豐鋼鐵等都活得還不錯。
地方政府在行業中的特殊角色帶來的另一層問題是兼并重組名存實亡,國家冶金工業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鄭玉春表示,目前國內幾乎所有的兼并重組都不具實際意義,“由于涉及地方稅收等方方面面的利益,有些想收購的企業進不去,不愿收購的企業卻被指定重組,如鄭州的一家鋼鐵企業,先是首鋼有意愿收購,但談了幾次都沒成功,最后還是由河南本地一家鋼企接盤。這家企業也不愿意接盤”。又如唐鋼和邯鋼等組建成河北鋼鐵集團,只是在集團層面有這樣一個“帽”,實際上還是各干各的。所以現在出現一個有趣的并購版圖,如寶鋼去收購新疆的八鋼,鞍鋼則去重組四川的攀鋼,“距離相距甚遠,協同效應何在”?
然而正是這種格局可能為2012年帶來變化,戴國慶表示,新政府新氣象,相信各地新上任的官員會努力沖刺GDP,以投資開路,而鋼行業可能會有所好轉,“這個具體要看3月到5月份的投資數據,到時就能更精確地預計今年行業的變遷”。
另辟蹊徑
鋼鐵困局的根源在于體制,而目前鋼鐵也如“只摸石頭不過河”。戴國慶認為,過去的10年,鋼鐵業的體制改革基本沒動靜,他對鋼鐵業“十二五”規劃表示不滿,“基本上沒有提到體制改革的問題”。
對于改革的方向,戴國慶表示國資委提出的兼并重組、推動整體上市、掌控鐵礦石資源、開放鋼鐵業等思路都非常正確,就是無法貫徹。這一點也得到鄭玉春的支持,不過鄭也認為鋼鐵業的改革難度很大。他舉了一個最為典型的例子,“如鞍鋼和本溪鋼鐵,一家是央企,一家是國企,二者在一個地方談了好幾年最終無果而終,這里面涉及中央國資委,地方國資委,地方政府,鞍鋼和本溪鋼鐵這5個主體,很難開解。很現實的問題是如本溪鋼鐵并入鞍鋼,領導職務和干部怎么安排,職工如何處理等等,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問題,容易出大亂子,國企人太多了”。
在改革未有實際動作之前,行業目前最好的發展辦法是尋求低層次的合作,鄭玉春表示:“對于爭奪鐵礦石定價權、解決同質化競爭等核心問題,都需要企業聯合起來,在兼并重組未能實質推動之前,可以先在某類產品方面比如家電板聯合起來,形成壟斷競爭之勢,此類做法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避免同質化的惡性競爭。此外,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可以先推動局部的兼并重組,盡管難度很大,但如果在某地方行政區域內,還具有一定的操作性,然后再以華北、華東這類大塊區域整合,容易形成聯合的基礎。”
而實際上,政府部門的鋼鐵“十二五”規劃努力方向多在沿海沿江戰略。鄭玉春說:“我現在也搞不明白這個策略的意義,我國鋼鐵北重南輕,沿海地區工業發達,需求量大,沿海沿江主要是為了貼近市場,然而現在沿海地區的工業在向內陸轉移,而我們還在大規模地讓鋼企搬遷至沿海地區,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曹妃甸、湛江等多個大型鋼鐵基地陸續獲批投建,以首鋼的搬遷為例,建設新基地花費了數百億的資金,2008年基本建成后,至今首鋼只說達到了生產標準,卻不談盈利問題。試想這么大的投資,需要多少年才能換回來?那么多陸陸續續搬遷的大企業將來會不會留下一堆爛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