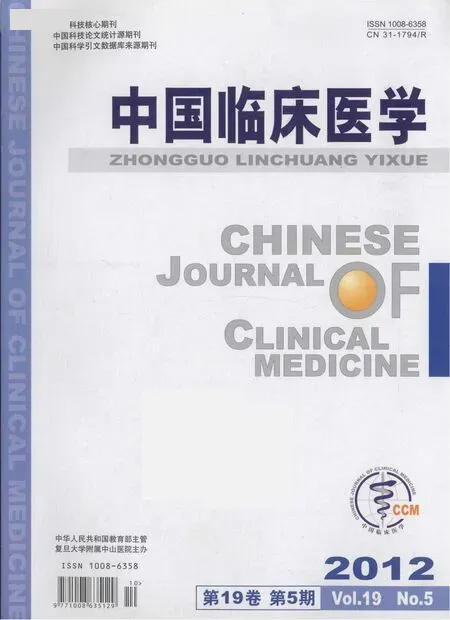微炎癥及氧化應激對慢性腎臟病患者腎功能的影響
沈文清 邢艷芳 黃麗 錢捷 梁敏靈
(廣州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腎內科,廣東 廣州 510150)
近年來,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s,CKD)的發生率越來越高。CKD患者進展至終末期腎臟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主要原因除了吸煙、高血壓和糖尿病等危險因素外,氧化應激和微炎癥作為非傳統因素也日益受到關注。研究CKD不同階段患者血清中微炎癥及氧化應激指標變化,并積極干預,對于延緩CKD及預防并發癥有重要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08年1月—2012年4月在廣州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腎內科診斷為CKD第1~5期的住院患者92例,其中男性55例,女性37例;年齡27~77歲,平均(53.7±14.3)歲。入選標準:病程>3個月,未進行透析治療。排除標準:腫瘤、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嚴重的肝臟疾病、外傷、近1個月內輸血、活動性出血、心腦血管事件急性期等;正在用糖皮質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劑的患者。患者的治療方案均為降壓、調脂、降糖等對癥支持治療。
1.2 一般情況及分組 患者原發病包括糖尿病腎病40例、高血壓腎病37例、慢性腎小球腎炎12例、痛風性腎病2例、梗阻性腎病1例。以簡化腎臟病膳食試驗 (MDRD公式)及 Cockcroft-Gault(C-G)公式計算患者腎小球濾過率并進行CKD分期,按分期分組,CKD1期12例、CKD2期16例、CKD3期22例、CKD4期22例、CKD5期20例。各組患者年齡、性別構成、BMI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1.3 觀察指標 所有患者均于清晨空腹采血。微炎癥的監測:超敏C反應蛋白(hs-CRP)、脂蛋白a[LP(a)]均采用免疫比濁法測定,試劑分別由北京利德曼生化技術有限公司和豐匯生物研究公司提供,用日本日立7170A全自動生化分析儀進行檢測。氧化應激狀態的監測: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采用分光光度法測定,試劑盒購自南京建成生物研究所。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1.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腎功能不同階段結果的比較采用t檢驗。腎功能進展程度與微炎癥、氧化應激指標變化關系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CKD各期患者的微炎癥及氧化應激指標的比較 (1)血清hs-CRP水平隨CKD分期的增加逐漸升高。(2)血清LP(a)水平隨CKD分期的增加逐漸升高。(3)CKD2~4期患者中,血清SOD活性隨CKD分期的增加而下降,CKD4期組與CKD5期組組間血清SOD活性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CKD患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微炎癥、氧化應激增強,且隨腎功能損害加重其微炎癥及氧化應激狀態逐漸增強,見表1。
表1 各組患者血清hs-CRP、LP(a)和SOD水平比較()

表1 各組患者血清hs-CRP、LP(a)和SOD水平比較()
注:a與1期比較,P<0.05;b與2期比較,P<0.05;c與3期比較,P<0.05;d與4期比較,P<0.05
組別 n hs-CRP(mg/L) LP(a)(mmol/L) SOD活性(μ/mL)CKD1期 12 1.88±1.22 255.32±104.22 94.23±21.13 CKD2期 16 2.45±1.66a 293.11±112.23a 91.33±15.26a CKD3期 22 3.35±1.87ab 316.25±106.24ab 75.14±15.25ab CKD4期 22 6.17±2.34abc 367.23±127.45abc 68.37±18.25abc CKD5期 20 7.41±2.63abcd 434.25±125.33abcd 70.41±15.21abc
2.2 血清hs-CRP、LP(a)、SOD水平與腎功能的關系 (1)CKD 2~5期的患者血清 hs-CRP(r=-0.973)、LP(a)(r=-0.942)與eGFR呈負相關(P<0.05);(2)CKD2~5期的患者血清SOD (r=-0.912)與LP(a)呈負相關(P值均<0.05)。SOD(r=-0.866)與hs-CRP呈負相關(P<0.05);(3)CKD2~5期的患者血清SOD(r=0.764)與eGFR呈正相關(P<0.05)。
3 討 論
本研究結果表明,CKD各期患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微炎癥和氧化應激增強,且隨著腎功能損害加重,微炎癥及氧化應激狀態增強。hs-CRP和LP(a)水平在CKD2期就已顯著升高,提示在腎臟損害早期炎癥介質已顯著增高。伴隨hs-CRP和LP(a)水平的增高,SOD水平降低,提示微炎癥、氧化應激均參與并促進腎功能的惡化。
氧化應激在腎病的發生和發展及其并發癥的發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多種病理損傷的共同途徑[1-2]。其機制包括:(1)直接作用于腎組織細胞膜的多不飽和脂肪酸,引起脂質過氧化,破壞細胞膜的正常生理狀態;(2)直接損傷細胞線粒體DNA;(3)使腎小球毛細血管基底膜磷脂發生過氧化,導致小球基膜通透性升高;(4)減少結締組織的透明質酸,破壞細胞間黏合,使微血管通透性增加;(5)誘導腎小球足細胞凋亡;(6)通過多種細胞因子抑制系膜細胞基質降解,加重細胞外基質沉積;(7)參與內皮向間質轉化,引起小管間質纖維化。此外,微炎癥狀態活化的炎性因子也可以通過白細胞膜上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復合物的氧化作用放大氧化應激反應,而氧化應激反應又進一步刺激炎癥細胞活化。隨著腎臟清除能力的下降,毒性代謝物堆積,導致hs-CRP和細胞因子水平升高,前炎癥因子損傷了血管內皮功能,促進了單核細胞黏附血管壁,改變了血漿蛋白成分,進而發生氧化應激反應。代謝產物、尿毒癥毒素在體內蓄積致使抗氧化應激能力減退,同時抗氧化物質的攝取減少和(或)生物利用度下降,增強的氧化應激反應導致脂質過氧化和脂蛋白結構及功能的改變,產生特征性的晚期氧化蛋白產物,如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能上調黏附分子如血管細胞黏附分子-l、細胞間黏附分子-1及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增強血中白細胞對血管壁的移行和黏附,造成細胞氧化損傷和脂質氧化改變,最終引起炎性反應。微炎癥狀態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氧化應激反應所導致的。氧化應激反應可激活血液中的中性粒細胞及單核細胞,活化補體系統。Himmelfarb等[3]以hs-CRP為炎癥指標,發現氧化應激指標丙二醛(MDA)水平與hs-CRP呈顯著相關。本研究結果表明,CKD患者抗氧化能力下降,且在CKD2期即已出現,并隨著腎功能減退而不斷加重。本研究中CKD4期與CKD5期血清SOD活性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樣本量較少有關,需加大樣本量進一步探討。
CKD患者普遍存在微炎癥和氧化應激狀態,它們存在于腎臟病病程的始末,參與腎臟病的發生、發展,是影響CKD患者預后的重要危險因素。本研究結果提示有必要對CKD各期氧化應激、微炎癥發生的影響因素及干預措施進行深入研究。
[1]Djamali A.Oxidative stress as a common pathway to chronic tubulointerstitial injury in kidney allografts[J].Am J Physiol Renal Physiol,2007,293(2):F445-F455.
[2]Susztak K,Raft AC,Schiffer M,et al.Glucose-induce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cause apoptosis of podocytes and podocyte depletion at the onset of diabetic nephrapathy[J].Diabetes,2006,55(1):225-233.
[3]Himmelfarb J,Stenvinkel P,Ikizler TA,et al.The elephant in uremia;oxidant stress as a unifying concep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uremia[J].Kidney Int,2002,62(5):1524-1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