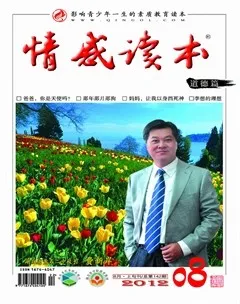鮮花與噩夢——重訪奧斯維辛
黃國榮
東歐之行,印象最深的是波蘭,最難忘的一頁是奧斯維辛。
這個位于波蘭南部的偏僻小鎮,被納粹制造成世界聞名的小鎮,1940年納粹和黨衛軍把它建造成了人間地獄,給波蘭乃至全世界人民制造了一個慘絕人寰的噩夢。
正值春暖花開的季節,一走進奧斯威辛集中營,春天的溫暖舒適立時被邪惡驅趕,焚尸爐、絞刑架、死亡墻、刑具、毒氣室,還有被害者一大倉庫一大倉庫堆積成山的皮鞋、眼鏡、假牙,像裝垃圾一樣載滿囚犯尸體的卡車……一件件實物、一幅幅照片,令人發指,心靈不住地一陣陣戰栗。
這個歐洲猶太民族最大殺戮中心的情況我不想復述。我只想說一說其中兩幅引我駐足凝視思緒萬千的照片。
一幅是4個赤身裸體的孩子,他們是兩對十多歲的雙胞胎。他們被饑餓折磨,兩條腿像兩根玉米秸一樣支撐著上半身,他們的每一根肋條骨在皮下清晰可見,那閉著和睜著的眼睛證明她們尚還活著,但都跟木偶一樣難有表情。其中3個睜著眼睛的孩子,目光里只有茫然,表達的內容只有一個:下一刻不知什么厄運在等著我。
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兒童主要是猶太籍和茨岡籍,還有波蘭和俄羅斯的兒童。來到這里,他們跟成年人面臨同樣的遭遇。黨衛軍里有個專門殘害兒童的魔鬼,他叫約瑟夫門格勒,一個屠殺兒童的怪獸。他在距地面150至156厘米的墻上分別畫了線,凡新押送到集中營的兒童都要到這里來進行篩選,身高不在這兩條線范圍之內的孩子當即就被送進毒氣室處死。在這兩條線之內的孩子,雖然暫時免死,但要跟成年人一起每天被強制勞動12個小時以上。納粹在他們每天必經的奧斯維辛大門上竟無恥地寫著(Arbeitmachtfrei)“勞動獲得自由”。
照片上的4個孩子因為是雙胞胎,他們的遭遇就比一般兒童更慘,他們還要供門格勒這個魔鬼做試驗。
門格勒對雙胞胎特別感興趣,他說“人和狗一樣,都有譜系,有人在實驗室里培養出了良種犬,我也能在里面培養出優良人種來。”被他試驗的孩子們,他們的眼球、脊椎、性器官任他試驗或摘除,任他做任何手術……
看著他們的照片,我心里一陣陣發緊酸楚。他們本該還在父母的呵護下嬌縱愉快地享受寵愛……可是法西斯們把他們的一切全粉碎毀滅了,只讓他們做一個個心驚膽戰的噩夢。
另一張照片是包括約瑟夫門格勒在內的納粹軍官們,看他們那賞心悅目的歡笑而又專注投入的神情,似在看眾多國際演藝明星的表演。但是,他們目光聚集的并不是演員的表現,而是一群經他們篩選出來被欺騙而快樂地走向地下室換衣服“洗澡”的新到人犯。這些剛剛下火車的人們哪知道,等他們脫光衣服后,立即會被趕入只有210平方米的“澡堂”里,大屋子天花板上的噴頭,從來沒有噴出過一滴水,每次進入這里的2000名囚犯,等到的是黨衛軍士兵從天花板上預留的小孔中往里灌入的氯化氫劇毒氣體。據記載,僅1942至1943年間,納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內就消耗氯化氫2萬公斤。
這些納粹軍官或許因囚犯們傻乎乎地受騙上當而好笑,或許為他們自己的“狡猾、聰明、毒辣”而開心。就是這個門格勒,他拿兒童的眼球做試驗,將他的藥注入孩子們沒經麻醉過的眼球,孩子們疼痛得慘叫著蹦跳,他卻借此瘋狂地取樂。他的一張木桌上擺滿了貼了標簽、編了號碼的淡黃色、淡藍色、綠色和紫羅蘭色的各種眼球……
也是他發明了更令人恐怖的壓力艙試驗。他把犯人關進一個壓力艙,隨著壓力的增強,記錄犯人的呼吸變化,直至犯人的身體粘貼在艙壁上,眼球鼓出,或肺部爆裂而死。
我把門格勒另一張穿白大褂的照片仔細端詳,我十分不解,他不也是個好端端的父母所生的人嗎!他有一張端正的長方臉,濃眉大眼,笑容可掬,他怎么會做出魔鬼所干的事情呢!顯赫的大企業家庭出生、會拉丁文和法文兩國語言、有醫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的高級知識分子,怎么會變成魔鬼的呢?
我從恩格斯的名言中找到了答案,他說:“人是什么?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人們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期望的目的而創造自己的歷史,卻不管這種歷史的結局如何……”(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恩格斯的觀點與荀子的觀點是一致的,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篇》)。他認為人性生來就有惡的成分,是不完美的,之所以有善的行為和完美的人格,不是人性自然生成,是后天禮儀制約,人為改變而成。
這就不難理解門格勒人性變異的原由。他從事人類學和遺傳學研究,他年輕時就夢想讓自己載入世界大百科全書。假如他順著這個做學問的道路走下去,他或許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醫學科學家。但1931年他加入了納粹黨組織下的青年同盟;1937年加入了納粹黨;1938年又加入了黨衛軍,在前線負傷后他到奧斯維辛集中營任醫學和實驗科研處處長、主任醫師。這個組織和環境,把他人性中“天使”和“善”的成分抑制、排斥,甚至驅除,使“野獸”和“惡”的成分得以營養、滋長,甚至張狂。所以形容人性變惡時常用“豺狼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些詞,這里的本性就是指獸性。奧斯維辛集中營這人間地獄的環境,讓這些納粹軍人人性變異獸性發作,毒害人犯變成他們娛樂的一種游戲,越恐怖、越殘酷、越血腥對他們越刺激,越有快感,觀賞犯人臨死的痛苦、掙扎、驚恐成為他們宣泄獸性的嗜好,他們完全忘了自己是人。
到1945年1月18日德軍失敗,他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到了隱藏、逃匿上,以至國際社會花了35年時間都沒能抓捕到他。1979年1月24日,是他自己在巴西游泳溺水身亡,他成為最后一個納粹。
在離開奧斯維辛集中營時,用來槍殺犯人的“死亡墻”前那一束束鮮花,給我沉郁、酸痛、冰冷的心境,吹進了一縷春風,一股暖意漫過我悲涼的心田。一位美麗的波蘭姑娘正和她的親人把一束玫瑰放到墻邊,我看到了她臉上的惆悵。墻邊的花束,有的絲帶上寫著集中營囚犯的編號,顯然是受害者的后人親屬所祭,更多的則沒有任何所指,顯然是獻給所有亡靈的。這一束束鮮艷的玫瑰、金菊、郁金香和蘭花,表明一個事實,人們沒有忘卻這個噩夢,更沒有忘記這些無辜被害的不幸者。我沒能見到更多的獻花者,但凝視這些鮮花,我仿佛看到了一個個少女美麗臉龐上的憂郁,看到了一位位少婦優雅身影包裹著的沉重,看到了一個個天真兒童的疑問……我想他們或許來自波蘭,或許來自俄羅斯,或許就來自德國……
一束束鮮花鮮艷水靈,都是剛剛放下。這個偏僻的奧斯維辛不像有些旅游景點那么商業味,沒發現這里有花店,這些鮮花都是前來參觀祭奠者遠道帶來。鮮花代表著美好,由此我堅信,他們來這里參觀祭奠,絕非要把這當仇恨來記惦,也絕不會把它歸咎于今天的德國人,更不會想到要對德國人民以牙還牙。人們來這里,抵御忘卻是要大家記住“人在特定的環境里會變成野獸”這個教訓,祈禱歷史悲劇絕不要重演。
離開集中營走進華沙和克拉科夫的市區城堡,因語言的障礙,我無法與波蘭民眾交流,但街頭、公園、車站,春光里旁若無人地捧著書本閱讀的少女、青年、婦人、老人隨處可見;肖邦、居里夫人、哥白尼一個個名人雕像,美人魚、華沙起義、猶太人紀念碑一組組城市雕塑,透射出豐厚的文化意蘊,標示著這個國家的文明進程。平靜、安逸、穩定、忙碌成為這里生活的常態和主流,我感受到一股由文化與文明構成的潛流在平靜之下兀自流動著。
胡曉宇摘自《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