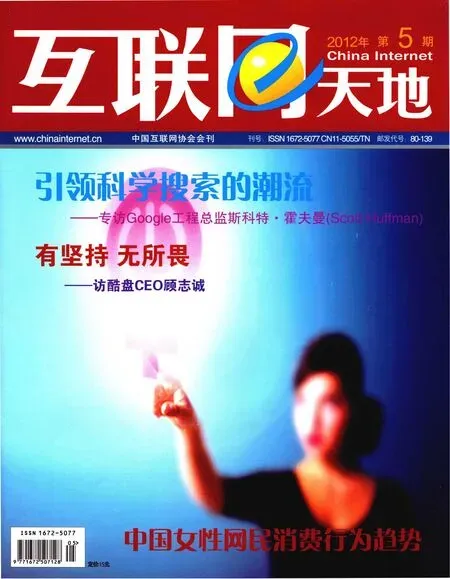互聯(lián)網時代垃圾信息的預防和遏制
文 四川通信設計院 程德杰
通過集全社會之力,通過系統(tǒng)的策略和手段,還是可以遏制住當前垃圾信息不斷泛濫的勢頭,將其危害限制在一定范圍內。
2012年中央電視臺的3·15晚會,爆出某電信運營商市級分公司縱容垃圾短信傳播,并通過提供技術服務平臺牟利的消息,一時間讓“垃圾短信”這個久已為人們所熟悉的話題,再次為人們所關注。
垃圾信息的危害性已經廣為人所知,相關的行政和司法懲治措施也在逐步完善,打擊力度也在逐年加強。但在潛在的巨額利益面前,垃圾信息的發(fā)布者,早已借助互聯(lián)網技術,成功地實現(xiàn)了垃圾信息發(fā)布技術和手段上的升級換代,更借助非法買賣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實現(xiàn)了垃圾信息推送的針對性。因此,總的來說,現(xiàn)階段國內垃圾信息的泛濫對普通大眾合法利益所造成的侵害,其影響仍呈上升勢頭。
作為一種隱藏在灰色地帶、游走于罪與非罪之間,以謀取利益為最終目的的社會行為,垃圾信息制造本身很難得到徹底根治。但通過集全社會之力,通過系統(tǒng)的策略和手段,還是可以遏制住當前垃圾信息不斷泛濫的勢頭,將其危害限制在一定范圍內。
簡單說,就是通過信息的分類、信息傳播責任的界定、信息受眾隱私數(shù)據(jù)的保護、信息安全立法,以及信息安全執(zhí)法等系統(tǒng)化策略,實現(xiàn)對垃圾信息制造和傳播的預防和遏制。
信息分類
我們處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各種各樣的信息充斥于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如何發(fā)現(xiàn)有用信息、隔離無用信息,已經成為我們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垃圾信息不僅包括手機上的垃圾短信、Email中的垃圾郵件,還包括互聯(lián)網SNS社區(qū)(如Facebook、Google+、微博等)中的垃圾信息。這其中既有面向特定、不特定人群的推廣或促銷信息,也有虛假、釣魚信息,甚至還有內嵌了病毒、木馬的有害信息。簡而言之,任何非為受眾所愿意接收的信息,都可以歸為垃圾信息一類。
對信息進行分類,識別和發(fā)現(xiàn)垃圾信息是遏制垃圾信息傳播,并對垃圾信息傳播行為進行有效懲治的基礎。
受益于電子郵件誕生以來和垃圾郵件斗爭的經驗,以及人工智能-機器語義識別技術的巨大進步,目前人們已經可以在信息源頭,通過機器內容識別系統(tǒng),實現(xiàn)較高準確率的信息識別和分類。
據(jù)了解,某些公司開發(fā)的垃圾郵件識別算法,可以實現(xiàn)98%以上的垃圾郵件識別率。微軟曾宣稱通過應用SmartScreen技術,其Hotmail郵件系統(tǒng)可以讓收件箱中的垃圾郵件比例降低到3%左右。

從技術角度來看,垃圾郵件和垃圾短信的識別,并沒有本質上的區(qū)別;從實現(xiàn)難度上來看,垃圾郵件的識別難度要遠高于垃圾短信。事實上,國內各大電信運營商和主要ISP的短信網關和郵件網關、以及互聯(lián)網出入境節(jié)點上,都已經部署了類似的內容識別系統(tǒng)。
因此,垃圾信息的識別已經具有相當?shù)募夹g基礎和較高的準確率,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用好信息分類技術,并將信息分類結果應用于垃圾信息的遏制上。
信息傳播責任界定
在當前技術水平下,通過機器識別,已經可以對垃圾信息實現(xiàn)較高的識別率,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抑制住垃圾信息的傳播。
目前來看,包括垃圾短信在內的垃圾信息的泛濫,傳播渠道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究其原因,無非是利益使然。今年3·15晚會上爆出的運營商協(xié)助垃圾短信傳播案件中,運營商通過協(xié)助垃圾短信制造者發(fā)送垃圾短信,每月可獲得數(shù)百萬人民幣的收入。垃圾信息傳播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可見一斑。
與廣受關注的垃圾短信相比,基于SNS的垃圾信息傳播其形式較為隱蔽,但其給垃圾信息制造者、傳播者所帶來的利益更為巨大。在國內某著名社交微博上,發(fā)起一次微博營銷推廣活動,其給信息傳播者所帶來的利益可以以數(shù)十萬計。顯然,這些營銷活動推廣的信息,并不一定是那些信息受眾所愿接收到的,大致也可以歸為垃圾信息的行列。
正是因為垃圾信息的傳播,存在著巨大的利益,才使得信息傳播者甘冒風險參與到垃圾信息的利益輸送鏈條中,使得垃圾信息的傳播在某些領域暢通無阻。
因此,在法律和法規(guī)中,明確信息傳播者應承擔阻止垃圾信息傳播的責任,從而阻斷垃圾信息傳播的通道,對于遏制垃圾信息不斷膨脹的勢頭十分必要。
信息受眾的隱私數(shù)據(jù)保護
央視3·15晚會中,與電信運營商助長垃圾短信被曝光所引發(fā)的關注度相比,羅維鄧白氏公司非法搜集和販賣個人隱私數(shù)據(jù)事件,似乎在普通老百姓心目當中并沒有掀起多少漣漪。
然而,正是諸如羅維鄧白氏這類公司對個人隱私的非法搜集和濫用,使垃圾信息的傳播和泛濫更加嚴重,并且和以前的廣播式垃圾信息相比,垃圾信息制造者在獲取了用戶準確個人資料基礎上,所制造的垃圾信息更具有針對性和迷惑性,因而也更有危害性。
公民的個人隱私數(shù)據(jù)保護,并非是互聯(lián)網時代獨有的話題,但在互聯(lián)網廣泛應用已經滲透到生活各個方面的今天,卻具有特別的意義。
通常一個人的收入水平、家庭成員、消費習慣、居住信息、聯(lián)系方式等個人數(shù)據(jù),在其朋友圈里,并不算是特別隱私的數(shù)據(jù)。但如若這些數(shù)據(jù)被搜集整理,并加以分析和挖掘,就會成為極有價值的商業(yè)信息。
這些有關個人隱私的商業(yè)信息,如果被別有用心者獲得,就有可能導致對于其個人不利的事件發(fā)生。近年來,層出不窮的短信詐騙、電話營銷騷擾事件的出現(xiàn),就是個人隱私數(shù)據(jù)被濫用的佐證。因此,有必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手段對信息受眾的隱私數(shù)據(jù)進行保護,在立法和執(zhí)法實踐上,明確因商業(yè)行為獲得用戶隱私數(shù)據(jù)的商家,有對這些數(shù)據(jù)保密的義務。
杜絕公眾隱私數(shù)據(jù)的非法傳播和搜集,對于遏制垃圾信息傳播、保護垃圾信息受害者具有十分主要的意義。
信息安全立法及執(zhí)法

毫無疑問,對于垃圾信息的預防和治理來說,法律是最有效的武器。事實上,自互聯(lián)網誕生起,世界各國都在遏制垃圾信息傳播方面開展了廣泛的立法和執(zhí)法工作。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信息安全立法起步并不算晚,在治理垃圾信息方面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根據(jù)Sophos的報告數(shù)據(jù),在全球垃圾郵件排名榜中,中國的排名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第4名下降到2011第一季度的前12名以外。這表明我國在抑制垃圾郵件工作上,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然而,中國在追究垃圾信息制造、傳播者的刑事責任、加大執(zhí)法力度方面,與其他國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在追究垃圾信息制造、傳播者,以及個人隱私濫用者的責任方面,多使用經濟處罰的方式,而較少使用刑事處罰。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國家在抑制垃圾信息產生和傳播上所做的努力。而與此相對的是,國外的垃圾信息制造者除了要承擔巨額的罰款外,還面臨著嚴峻的刑事處罰,因發(fā)送垃圾信息而被罰以重刑者,見諸報道的屢見不鮮。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加強互聯(lián)網時代的信息分類技術應用,有效識別垃圾信息,明確信息傳播者對于阻斷垃圾信息傳播通道的責任和義務,保護公眾隱私數(shù)據(jù),加強有關垃圾信息的立法和執(zhí)法工作,對于當下抑制垃圾信息膨脹的勢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