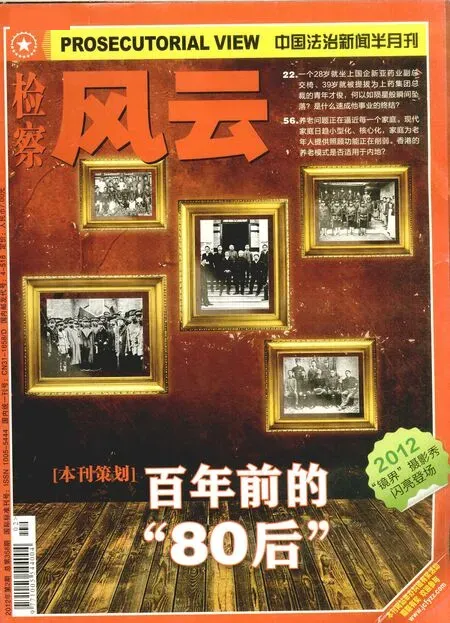龍宗智:我的興趣不在行政事務
文/方茹茹
龍宗智:我的興趣不在行政事務

龍宗智:
曾任西南政法大學校長,1954年生于成都,法學博士,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研究所所長。系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特邀專家咨詢員。
龍宗智教授有幾次華麗卻又不被很多人理解的轉身:為了讀書,已經是一名軍官的他選擇了大學;為了更好地進行研究,已經是大校軍銜的他寧愿放棄在軍隊里的優厚條件,轉業到地方做一名學者;為了潛心做學問,在校長位置上干得有聲有色的他不顧西政許多老師和學生的挽留,堅決不再留任……與龍宗智打過交道的人都說龍教授是個理性的人,對他而言,他只喜歡思考與研究,并不在意頭上的光環和優厚的待遇。
“我們作為“文革”后的一代多少還帶有一些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學法律可以把我們對于國家政治這種大問題的關心和對法律這種職業化的要求緊密聯系起來。”
記者(以下簡稱記):龍老師您好,恢復高考前,您在部隊里已經是一名軍官了,為什么還會想起讀大學,并選擇法律專業?
龍宗智(以下簡稱龍):就我們當時這一批人來說,選擇讀大學還是為了圓自己的一個夢,我們對于大學里自由的生活、活躍的思想還是帶有一些憧憬的。畢竟自己比較喜歡思考問題,在軍隊時間久了,有機會總還是愿意去學校里讀讀書。
為什么會選擇法學?在當時,“文革”的影響依然存在,社會對于政法工作還心有余悸,但一位中學的老師提醒過我,法律還算是文科里面的一個專業性比較強的學科,不像其他有些社會科學那樣給人萬金油的感覺。現在想想當時也算是歪打正著,再加上學法的人可以把對國家政治命運的關注和對研習法律技術層面的關注結合起來,法律的意義也越發凸顯出來。
記:現在法學界都清楚您所在的西政1978級是神話般的一個年級,您周圍的同學也是人才輩出,您能不能回憶起當時的一些場景?
龍:西政的1978級,確實不是單一的某一年級,它是因“文革”中斷十余年后人才的一個集合,現在學術界很活躍的一些學者,如賀衛方、梁治平等,在當時還都是小字輩的學生。就課程設置而言,那時也沒有法理學,就是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還有人會提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我們當時的一批同學中,雖然仍有人有“文革”時留下的“左”的思想痕跡,但多數人已經打破了思想桎梏,獲得了一種較為理性的思維方式當時很多同學思維的活躍性,已經遠遠超過老師了,而且求知欲特別強,很關注社會問題
記:您讀博期間寫的畢業論文獲得了國家級優秀博士論文的榮譽,這可能不僅是您的榮譽,也是西政這個學校的榮譽。您是怎樣完成一篇優秀博士論文的?
龍:在讀書的期間肯定要注重于學術,工作當然也需要做好,但我覺得好不容易有幾年能全身心地投入看書,就要抓緊時間多抽出一些空閑來投入到學習之中。我當時雖然也兼著職務,但讀書上還是下了工夫,這還是主要取決于自己。
記:我們也注意到,您有些文章,尤其是一些隨筆涉獵比較廣泛,對法文化也有相當的關注。
龍:我主張法學研究有較寬的視野,尤其是研究程序法與司法制度的學者,如果視野狹窄,雖然對某些技術問題仍能做出知識貢獻,但總的看深度有限。
記:您的經歷不同于很多人,作為軍隊中的法律實務者,您有很強的學術思維。對于這一點,您是怎么看的?
龍:當時我常向《人民檢察》投稿,算是這個刊物的重要作者,還得了好幾個年度文章和征文一等獎,后來也參加高檢的修法研究及一些學術性的活動。因此,在專業研究方面,沒有局限于軍隊的環境。我常常想的是軍隊中相對比較簡單和模式化的精神環境,對我是不太適合的,我需要尋找一個更適合的精神空間,所以后來就離開了。
“在中國的大學體制下,要想當一名好的校長,是不可能有大學普京式的人物的……如果說我為西政還做了一點事情的話,就是試圖去營造一種學術氛圍,政法大學不是干訓學校,我們需要提倡一種理性主義的精神,一種可以自由討論的精神。”

主要著作:
龍宗智教授自稱是一位“跳躍于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人物”。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刊物發表法學論文及研究文章200余篇,著作(含合著)十余部,提出并論證了刑事訴訟的“兩重結構”理論和“相對合理主義”。
記:看您的簡歷,您在軍隊還是很受重視的,您也可以到地方部門,去當一個官,選擇到學校做老師可能會有點犧牲吧?
龍:我當時下地方,是復員為民下去的。我從士兵一步步上去,既有學歷又有基層經驗,當時是受重視有發展前景的干部。我打復原報告,一些領導感到很吃驚。當時確實也有多個選擇,也猶豫過,但選擇以后就沒有什么后悔,也覺得挺合適。中國雖然是官本位,但適合自己的也許才是最好的。而且,不當官也有了許多輕松。前段時間看南方人物周刊的一個訪談,被訪人說,他感到幸運的是,從事的專業、所受的教育以及個人的愛好三者結合了起來,所以感到生活和工作都有意義,感到快樂。我很有同感。
記:您來到西政的時候,至少西政已經不是當年您讀書時的那個西政了,當時西政的地位已經有所滑坡,您在上任的時候有什么想法?
龍:當時(2002年)西南政法大學需要一名校長,我是經舉薦、被考察后去了那里。其實,重慶教委和組織部門對我不太熟悉,可能是西政老師和干部的意見起了重要作用。不過,當時我還有些猶豫,猶豫的原因就是我內心并不是很喜歡做行政工作。但最后還是覺得自己可以有所突破,畢竟一個人不能總是按照自己的興趣辦事,還是要為社會做一些事情。
我擔任校長可能與一般校長的經歷是不一樣的,畢竟我不是做教育管理工作的,也不是從西政行政工作的基層走出來的,我屬于一個“空降”的校長。而且不像由北京派到地方上的一些“空降”官員,我沒有中央機關的背景。我對西政的很多內部事務還不熟悉。當時對西政如何開展工作,心中還沒有底,也不會有謀略于胸的感覺,更不可能有什么“三把火”,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記:那后來您是怎樣開展工作的呢?
龍:一般性的工作,只要有行政經歷大體上都能應付過去。經過一些時日,工作熟悉一些,干起來也就更順了。我雖然長期在實踐部門工作,但個人秉性還是一個學者。學者當官,有長處也有弱點。我認為自己的長處,一是頭腦比較清楚,處理問題大致不錯;二是出于公心,在位不謀個人好處;三是人際關系注意協調,這樣可以“借力”,有利于工作。但是學者也有弱點,就是有時不太會“來事”。比如,地方的院校,需要和地方搞好關系,我們不是不懂,就是不太愿意多下工夫,不愿過于勉強自己。
記:關于您主政西政的這段時間,外界對于您的關注也頗多,其中就有一種您本人不太認同的說法——西政普京,您為什么會對這個說法不認同?
龍:大致有三個原因,一是因為大學的性質,大學不是行政機關,簡單的命令在許多情況下是不行的;二是因為中國大學的體制,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書記、校長都在一線,都要管理,很難有非常清晰的職責邊界,可以說是一種“雙校長制”,如果校長像普京般強勢,那么難免與書記鬧矛盾;三是因為個人的原因。我說過,我的秉性是學者,比較理性,因此也不會過于強勢。應當說,這種說法主要反映了同學們對西政振興的愿望,可能也反映了對我的某種好感。政法大學的學生思想特別活躍,當時西政的網上論壇,學生們對學校的意見很多,罵人的不少,不過對我都還是比較支持,說好話的多,批評的很少。可能有一個原因,我經常參加學術講座并作評論,有時說話直抒胸臆,西政的講座評論又是批評為主,使他們這些“小憤青”感到這個校長有點“老憤青”的味道,所以多少有點認同感。
記:很多媒體在評價您主政西政這幾年時,往往會說到這幾年是西政發展過程中學術開放、思想活躍的幾年,您當時采取了哪些措施去營造這種氛圍?
龍:我也是一名學者,我從來沒有把西政校長這個位子當成一個官來做,沒有刻意地去采取措施,我只是想把大學營造成一個大學應有的樣子,當然,作為行政工作者,該做的事情要做,該處分學生的時候也要進行處分。但就學術和思想而言,我比較認同作為大學所應有的精神,大學也應當有屬于自己的氛圍。作為校長,我也沒有刻意地營造這種氛圍和精神,我最后一次對研究生的講話,提到了大學的精神,大學需要有一個學術自由的精神。我在西政當校長這幾年,如果說為西政還做了一點事情的話,就是試圖去營造一種學術氛圍,使這個學校像個大學。
西政是一所以法學為主的院校,不可避免有專業的局限,我當時希望西政的講座要盡可能地把視野放寬,吸引全國不同領域的專家來這里做講座。西政有一個非常好的傳統,就是學術的爭鳴和討論非常熱烈。每次專家講座的時候,參與的其他教師評議只能批評不能表揚,要有思想碰撞的火花,要有學術的張力。我們這批西政學者的共同努力,應當說對學術精神的培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我幾十年來一直在做行政實務,但我的興趣并不在這方面。作為一名學者,必須要有思想的火花,但有了思想,還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坐到冷板凳上進行系統整理。到了我這個年齡,很想再繼續做些自己的研究。”
記:2006年,當您結束了一屆任期之后,是什么原因沒有繼續留任,而是回到了川大?
龍:當初我在就任西政校長時,就只打算干一屆。時間到了,我就提出辭職。我的這個舉動,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也知道,繼續在西政擔任大學校長當然是個不錯的工作,但我并不喜歡做太多的行政事務。我這樣做不是第一次,當初就是從大校軍官復原為民,然后去當一名普通教授。這次也差不多,不過,這次是事先就考慮好了的。
記:您走的時候,西政的師生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如很多網上的評論一樣,他們對您都很留戀?
龍:確實有相當一部分老師和學生不希望我走,書記和學校其他領導應當說也不希望我走,因此我辭去校長職務后,根據學校決定還擔任了兩年校學位委員會主席、學術委員會主任和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主任,直到把人事關系辦到川大后一段時間。就我個人來說,我還是覺得人各有志,不必勉強。我幾十年來一直在做行政實務,但我的興趣并不在這方面。作為一名學者要有思想,但有了思想,還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坐到冷板凳上進行系統整理。到了我這個年齡,很想再繼續做些自己的研究,而行政事務會大量地占用我做研究的時間,所以我還是選擇離開了。還有一個原因,我不愿長久從事一件我認為由于受條件所限不太可能有很大進展的事。此外,還有一個個人的原因,家在成都,落葉歸根。當初我去西政當校長也是和川大有約定的,“下課”后回川大。我在川大也一直兼職做博導,因此,可以說不是從西政調到了川大,而是從西政回到了川大。不過我也曾不只一次說過,對于西政,我干一段就“下課”,沒有“將革命進行到底”,也常有愧疚感。
記:您回到川大以后,川大給您的職位是985工程的首席科學家,這個職位聽起來很有意思,在川大這樣一個綜合性的985大學中,安排一個社會科學和法學的教授擔任首席科學家,您對這個職位怎么看?
龍:985工程主要是理工科的事,文科教授也套用這個說法。這個位置對我來說并不具備太多的實際意義,我比較習慣于自己的研究,我不太愿意拉一個攤子,搞一幫子人來,又免不了行政化,免不了各種填表和麻煩事。因此,對于我們這樣的教授,什么位置、平臺,其實都沒有多大的意義。
記:您卸下西政校長的重擔,回到川大擔任教授后,工作是不是輕松了很多,您近期有什么打算?
龍:現在我的事情也不少,但比較自由。我的研究在司法制度、證據制度及刑訴法三個方向。這些年研究刑事證據制度有一些心得,出了一本《證據法的理念、制度與方法》,也有其他一些成果,仍在研究其他相關方面的一些問題。
記:回顧這么多年的學術研究過程,您認為自己主要的學術心得與貢獻是什么?
龍:借用鄧正來先生的一個表述方式,在專業研究領域,我的探索主要圍繞一個主題,即“中國刑事司法的形構及其正當性”。由于中國司法構造與法治推進過程的獨特性,以西方既有的理論范式來分析也許難得其解,由此,我提出了兩個所謂的理論:一是在1990年代初,提出了中國刑事司法的“兩重結構”理論,這個理論在后來做了一定的修正與發展。二是在1990年代末,提出司法改革與司法操作中的“相對合理主義”。然而,更多的,應當說是更有意義的研究,是針對中國司法制度與操作中各種需要解決的問題所做的分析。如在《法學研究》發表的關于中國訴訟實務中證明方式的文章——“印證與自由心證”。這篇文章提出的中國刑事訴訟中的“印證證明模式”,應當說已經被實務界普遍接受,因為已有不少文章認可并運用這一證據分析方式。這是我的實務心得以及多年思考和比較研究的一個結果。我不敢保證自己的觀點都正確,但是一般能夠做到見解新鮮并切中現實,較容易得到理論和實務界兩方面的認可。
記:龍老師,您算是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批法學學者了,經過30年的發展,現在的中國法學和您上課時期的法學已經截然不同了,學術界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作為曾經的大學校長,您如何評價這些問題?
龍:在我看來,學術界的人主要可以分兩類,一類是做學問,另一類是吃學問,做學問的人不管條件有多艱難,也會繼續努力;吃學問的人只是把學問當成了謀生的一種工具。同時,現有的社會評價機制又督促著很多學者不得不多發論文,中國當前學術界的大環境使得一些老師在評價機制面前壓力特別大。我們現在的各個部門法年會或是其他重要會議,動輒幾百人,但所提交的論文,多數沒有什么價值。不過,對于青年學者,寫出有分量的文章通常需要一個過程,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相信,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些問題是會逐漸改善的,我持一種謹慎的樂觀態度。
記:龍老師,在中國的法學家中,您的視野是很開闊的,作為一名“跳躍于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學者,您認為中國法學研究的主要問題在哪里?
龍:我是從刑訴法領域出來的,我感到現在這個部門法領域的主要學者都在關注司法實際。我因出身和經歷,歷來關注實踐,而其他一些長期在學校從事研究的學者近年的實證研究也做得很有成就。因此,一味批評法學界理論與實踐聯系不夠我認為過于隨意。
法學研究的主要問題還是社會留給法學領域的研究空間不夠,中國的法治有著這樣或是那樣的束縛。同時,中國法學界還有一批學者忽略了他們應有的責任,缺乏直面現實,解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這方面或許應當有所改善。
編輯:董曉菊 dxj5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