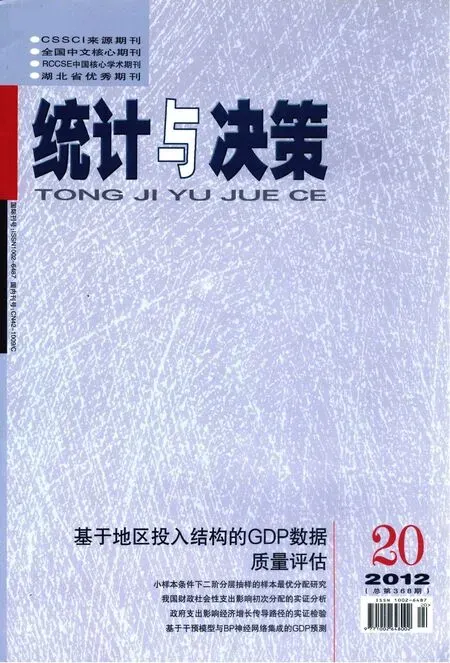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政府保費補貼額度的測算
梁來存
(湖南師范大學商學院,長沙 410081)
0 引言
關于農業保險的政府補貼問題,已有不少的研究。Wright和Hewitt(1990)在研究中披露了1989年美國農業部所作的一項全國調查,該調查對沒有參加聯邦農作物保險的農民對他們之所以不參加保險的原因進行了排序,結果發現,排第一、二位的分別是保障太低和保費太高[1]。Calvin和Quiggin(1999)發現,農民參與聯邦農業保險項目的原因中,風險規避僅僅是一個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為了得到政府的補貼[2]。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對農業保險需求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對于美國農民,隨著其初始財富達到一定程度后,風險規避減弱,購買農業保險的動機降低[3]。我國學者柯炳生(2001)認為農民和保險公司在保險信息上存在著不對稱性,農民的行為難以有效監督,保險公司的操作成本很高,難度大,加之農業風險的復雜性以及高成災率,導致農業保險費率高。根據美國的經驗,如果沒有政府的較大幅度補貼,農業保險很難推行。美國農業保險的補貼占保險費的2/3左右[4]。孫香玉、鐘甫寧(2008)認為農業保險市場上的需求曲線并不總能與供給曲線相交,在兩者不相交的情況下存在未實現的潛在經濟福利,而政策性支持可能導致其實現,增進經濟福利[5]。聶榮、Holly H.Wang(2011)認為,由于農民收入中源于種植業和養殖業收入的比重在逐步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的情況下,購買保險的預期收益不高,因此,農民對投保沒有動力。這在經濟發達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6]。
本文將基于效用函數研究政府保費補貼額度的區間范圍,推導政府保費補貼額度的下限和上限;并以湖南為例,在測算效用的基礎上,就政府的保費補貼額度進行具體的分析。
1 政府保費補貼額度上、下限的推導
1.1 政府補貼上、下限的界定
我國農民是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主體,收入不高。結合這一實際情況,本文假設,農民的風險傾向隨著其收入的變化而變化:當農民收入水平較低時,農民的收入僅能滿足其第一層次的生理需求,沒有能力顧及第二層次的安全需求,對于風險的規避程度較低,這時農民對于風險的態度可以看作是風險偏好型;當農民收入達到中等水平時,農民有能力考慮安全需求,對風險的規避意識不斷提高,這時農民對于風險的態度屬于風險規避型;當農民收入達到較高水平時,農民具有面對農業風險的經濟能力,可以依靠自已財富獨立面對自然災害,這時農民對于農業風險已不太在乎了,其風險傾向逐步轉向風險中立型。
農民取得收入后,主要用于這樣四個方面:一是再生產投資,即生產消費;二是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消費;三是儲蓄,可理解為未來消費;四是購買農業保險,即保險消費。設農民所消費的是收入所能夠購買的所有這四個方面的組合,根據農民的風險傾向假設可以作出其消費效用隨收入變化的曲線圖,如圖1所示。它刻畫了有風險選擇的情況下農民消費的效用狀況。

圖1 農民效用隨收入變化曲線圖
在圖1中,橫坐標表示某農民的收入水平X,縱坐標表示該農民的效用U。圖中的效用曲線表示農民在沒有風險的情況下對應每一種確定的收入水平所獲得的效用。當農民收入水平較低,即X<X1時,農民屬于風險偏好型,效用曲線是凹的,U/(X)>0,U//(X)>0,在這一階段,農民沒有經濟實力購買農業保險;當農民收入處于中等水平,即X1<X<X2時,農民屬于風險規避型,效用曲線是凸的,U/(X)>0,U//(X)<0,這一收入階段的農民會考慮購買農業保險;當農民收入水平較高,即X>X2時,農民由風險規避型轉向風險中立型,效用曲線逐漸轉為近似一條水平的直線,這時,農民對是否購買農業保險不十分在乎。
政府的補貼力度直接關系到農民是否購買農業保險。政府對農民進行保費補貼,即相當于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農民的農業保險購買力。在沒有購買保險的情況下,農民的收入水平(X)等于自身收入水平(S),即X=S;在購買保險并有政府保費補貼的情況下,農民的收入水平(X)由自身收入水平(S)、農民支付的保費(c)、政府的保費補貼(T)三者決定,即;X=S-c+T。當農民收入水平(S-c+T)達到X1時,這時的政府補貼即為政府保費補貼的下限,記為T1;當農民收入水平(S-c+T)達到X2時,這時的政府補貼即為政府保費補貼的上限,記為T2。
1.2 政府保費補貼下限的推導
在農民處于低收入層次、風險偏好型階段時,政府的補貼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使農民由風險偏好者轉變為風險規避者,以達到刺激農業保險需求的目的。在農民風險傾向轉變的這一拐點上的政府補貼即為政府補貼的下限(T1)。
在拐點的左邊,農民的收入水平較低,無力購買農業保險,可把農民看作是風險偏好者,這時農民關于收入(X)的效用函數為U1(X),效用曲線呈凹狀。在拐點的右邊,農民處于中等收入水平,農民屬于風險規避者,這時農民關于收入(X)的效用函數為U2(X),效用曲線呈凸狀。
令

求解式(1),即得到拐點上的收入水平X1。
前已述及,農民的收入水平由自身收入水平、農民自已支付的保費、政府的保費補貼三者決定,即X=S-c+T。在拐點處,X1=S1-c1+T1。若農民支付的保費(c1)與政府的保費補貼額(T1)之比為d,則有:X1=S1-dT1+T1,即:

式(2)即為政府保費補貼的下限。
可見,影響政府保費補貼下限的因素有四個:一是效用函數的具體形式,即U1(X)、U2(X)的函數形式;二是拐點處農民的收入水平X1,這一收入水平是農民由風險偏好型到風險規避型的分水嶺;三是農民自身的收入水平S1;四是農民、政府在總保費中的支付比例d。
1.3 政府保費補貼上限的推導
當農民收入水平處于中等水平時,即X1<X<X2,其風險規避程度會隨收入增加而增加,購買農業保險的欲望隨之而增強。但當收入水平較高時,即X>X2,農民對農業風險已經不再敏感,購買農業保險的欲望相對穩定,因為此時農民擁有的財富足以使自已能夠承擔所面臨的農業風險。所以,政府補貼不能過多,應當以農民收入水平達到X2時為限,此時的政府補貼即為政府保費補貼的上限T2。
當農民的收入水平超過X1以后,農民屬于風險規避者,效用函數為U2(X),效用曲線呈凸狀,則U/2(X)>0,U/2(X)≠0。對于某一確定的農民純收入S,當政府的補貼趨于無窮大時,效用的一階導數U/2(X)會趨近于0。這就是說,不可能利用效用函數的一階導數為0來求得效用達到最大時的X2。
但可以這樣設想——在政府的補貼下,當農民的收入效用值達到某一理想的滿意水平U0時,此時的政府補貼即為政府補貼的上限T2。政府的補貼如果超過T2,政府補貼的利用效率就會明顯降低。
仍以d表示農民支付的保費與政府的保費補貼額之比。在政府的補貼下,農民的收入水平X=S-c+T=S-dT+T,相應的效用函數值為U2(S-dT+T)。
令:

求解式(3),即可得到政府保費補貼的上限值T2,這時,農民的收入效用達到了理想的滿意水平U0。
可見,影響政府保費補貼上限的因素有四個:一是效用函數的具體形式,即U2(X)的函數形式;二是農民理想的效用值水平U0;三是農民自身的收入水平S;四是農民、政府在總保費中的支付比例d。
2 實例分析
這里以湖南農業保險為例進行研究,旨在探討湖南農業保險的政府保費補貼額度的區間范圍。選取的時間區段為1988~2010年。
2.1 農民收入效用的測度
2.1.1 測度效用的方法:功效系數法
功效系數法是根據多目標規劃原理而建立的一種評價方法。在評價某一整體的綜合狀況時,一般有多種指標,而這些指標的性質和度量單位往往不同,不能直接相加或綜合,需要通過一定形式的函數關系將其轉化為同度量指標,再將這些同度量指標加權綜合,使之形成一個綜合指標,稱之為總功效系數,以此評價整體的綜合狀況。
前已述及,農民取得收入后,主要用于四個方面:一是生產消費,即再生產投入,二是日常生活消費,即衣、食、住、行、用等,三是未來消費,即儲蓄,四是保險消費,即購買農業保險。顯然,一方面,農民將收入在這四個方面進行不同比例的分配,會產生不同的總效用;另一方面,就這四個方面進行相同額度的消費,產生的效用也各不相同。所以,要得到農民取得收入后消費的相應效用,需要同時考慮這兩個方面。功效系數法恰好能夠滿足這一需要。
2.1.2 指標體系及其數據來源
農民關于收入的效用狀況從其消費的四個方面來衡量。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指標體系作如下設置:農民收入水平采用指標“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元)”。收入運用的這四個方面依次選用“人均生產費用u1(元)”、“人均生活消費現金支出u2(元)”、“農戶人均儲蓄借貸支出u3(元)”、“人均農業保險保費收入u4(元)”這四個指標來反映。指標數據均來自于相關年份的《湖南統計年鑒》。選取的時間區段為1988~2010年。
考慮到政府2007~2010年對湖南農業保險進行了保費補貼,“人均農業保險保費收入u4(元)”這4年的數據為已經剔除政府保費補貼后的保費收入。之所以這樣處理,是為了確保農民純收入與純收入運用的數量對應關系。
2.1.3 權重的計算
收入運用的四個方面,對于農民來說,每一方面的重要性是不完全相同的。某一方面對農民很重要,效用就大;某一方面相對不重要,效用也就相對較小。因此,應當確定上述四個指標的權重值。
根據農民現階段的收入水平,農民最關心的應當是再生產投入,即使壓縮日常消費、不增加儲蓄、不購買農業保險,農民也會盡力保證來年的生產投入。其次是日常消費,這是第一層次的需求。再次是儲蓄,最后是購買農業保險。儲蓄之所以比農業保險更重要,這是因為:農民儲蓄的目的在于為子女升學、養老、大病或其他緊急情況準備資金,儲蓄是必須的。農業保險只是為了應對可能的自然災害,購買農業保險的預期收益并不高,這樣,農民一般認為農業保險是最不重要的。
設pkm表示uk對um的相對重要性數值(k,m=1,2,3,4),pkm的取值及其含義為:pkm=1,表示因素uk與um具有同等重要性;pkm=3,表示uk比um稍微重要;pkm=5,表示uk比um明顯重要;pkm=7,表示uk比um強烈重要。um與uk比較得pmk,且這樣,可以將這里的判斷矩陣P寫為:

根據該判斷矩陣P,采用和積法,可以求出它的特征向量,即各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也就是權數分配:wk=(0.56,0.26,0.12,0.06)/。
上述權數分配wk是否合理,還需要對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檢驗使用公式:

由于

表1 湖南農民人均收入水平X(=S)與相應的總效用測度值U

所以,認為判斷矩陣P具有滿意的一致性,這說明權數分配wk=(0.56,0.26,0.12,0.06)/是合理的。
2.1.4 農民各年收入效用的測算
對于人均生產費用u1、人均生活消費現金支出u2、人均儲蓄借貸支出u3、人均農業保險保費收入u4這四個指標,就每一個指標,采用如下的功效系數公式計算其功效系數:

式(5)中,usk為uk的不容許值,這里取uk的最小值;uhk為uk的滿意值,這里取uk的最大值。zuk為uk的功效系數值。
根據計算的四個指標的功效系數值,再結合每一指標的權重值,即得到收入消費的總效用。即收入的總效用將wk、zuk(k=1,2,3,4)的數據代入,即可得到1988~2010年各年的總效用測度值。現將湖南農民人均純收入(S)與相應的總效用值(U)列于表1中。
表1實質上反映的是農民在沒有投保的情況下收入與效用的數據表。農民人均收入水平X采用的是農民人均純收入S,農民沒有投保時,X=S。而計算收入總效用時,人均農業保險保費收入u4是已經剔除了政府保費補貼的。所以,表1中的農民收入X與總效用值U的數據是對應的,反映了收入與相應效用值的關系。
2.2 效用函數的構建
根據表1的數據,先擬合U關于X的指數函數,得到的趨勢線為:

擬合優度R2=0.98。計算預測精度的平均絕對百分誤差指標MAPE=1.49<10,式(6)趨勢方程符合精度要求。
再擬合U關于X的冪函數,得趨勢線為:

擬合優度R2=0.89。計算精度指標MAPE=4.38<10,式(7)趨勢方程符合精度要求。
根據前述關于農民風險傾向的假設及其效用曲線的形狀,可以得出湖南省農民效用隨收入變化的效用函數為:

這是農民在沒有投保的情況下效用隨收入變化的效用函數。由于政府保費補貼即相當于增加農民收入,所以,這一效用函數在農民投保并有政府保費補貼的情況下仍然是適用的。
2.3 政府保費補貼區間的測算
2.3.1 政府保費補貼下限的測算
根據式(2),可以計算2011年政府保費補貼額度的下限T1。
2011年湖南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6567.06元,即S1=6567.06元。由效用函數可知,X1=3204元。根據湖南近4年農業保險試驗的實際,農民支付的保費與政府的保費補貼額之比為3:7,即d=3/7。代入式(2),得T1=-5896.12元。
注意到T1<0,其實這是很好理解的:當農民的收入水平X=3204元時,點(3204,83.01)為效用曲線的由凹轉向凸的拐點。2011年湖南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了6567.06元,已經越過了拐點,而政府保費補貼的下限T1是指拐點處對應的政府保費補貼水平。
2.3.2 政府保費補貼上限的測算
2011年政府保費補貼的上限T2可以由式(3)進行計算。
由于2011年湖南農民人均純收入為6567.06元>3204元,根據效用函數式(8),應當采用效用函數U?2(X)=15.13?X0.22。S=6567.06元,d=3/7,如果設農民滿意的效用水平U0為97,代入式(3)得:

求解式(9),即得到政府補貼的上限值T2=238元,此時農民滿意的收入效用值為97。
同樣,當農民滿意的收入效用值取其他值時,可以求得政府保費補貼額度的相應上限水平。
3 研究結論及政策啟示
3.1 研究結論
(1)關于政府保費補貼額度的范圍。
政府保費補貼的下限旨在實現農民由不具備農業保險購買力的風險偏好者轉變為風險規避者,是農民在這一轉變的拐點處的政府保費補貼額。影響政府保費補貼下限的因素有四個:一是效用函數的具體形式;二是拐點處農民的收入水平;三是農民自身的收入水平;四是農民、政府在總保費中的支付比例。
確定政府保費補貼的上限旨在提高政府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若政府補貼超過上限,農民效用水平增長極緩。它是通過事先設定農民某一理想的效用水平來計算的。影響政府保費補貼上限的因素有四個:一是效用函數的具體形式;二是農民理想的效用值水平;三是農民自身的收入水平;四是農民、政府在總保費中的支付比例。
(2)關于湖南農業保險的研究。
湖南全省平均來看,2011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已經越過了政府保費補貼下限對應的收入水平,農民已經屬于風險規避者,處于中等收入層次,農民的效用水平將隨著政府補貼的增加而提高,收入每增加1%,效用水平提高0.22%。當理想效用值為97時,政府保費補貼上限為年人均238元。
值得說明的是,如果就湖南的各地區而言,由于各地區農民的人均純收入不一樣,所以,各地區農業保險的政府保費補貼會有各自的特殊性。
3.2 政策啟示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認為,我國(本文以湖南省為例)農民平均來說屬于風險規避型,農民的風險規避意識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強,農民效用隨著政府保費補貼的增加而提高,所以,政府保費補貼對推進農業保險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政府的保費補貼不能搞“一刀切”,應當因地制宜,根據各地農民的收入水平確定相應的政府補貼額度:當某地區農民的收入水平較低時,政府不僅必須提供保費補貼,而且不能低于政府保費補貼的下限;當某地區農民的收入水平為中等水平時,農民屬于風險規避型,政府的保費補貼增加,農民的效用水平就會提高;當某地區農民的收入水平較高時,政府的保費補貼最好不要超過政府保費補貼的上限,以確保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7]。
[1]Wright,B.D.,J.D.Hewitt.All Risk Crop Insurance:Lessons from Theory and Experience[J].Giannini Foundation,California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Berkeley,1990,(4).
[2]Linda Calvin,John Quiggin.Adverse Selection in Crop Insurance:Actuarial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ncentives[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9,1(81).
[3]Serra,T.,B.K.Goodwin,A.M.Featherstone.Modeling Changes in the U.S.Demand for Crop Insurance during the 1990s[J].Agricultural Finance Review,2003,63(2).
[4]柯炳生.美國農業風險管理政策與啟示[J].世界農業,2001,(1).
[5]孫香玉,鐘甫寧.對農業保險補貼的福利經濟學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8,(2).
[6]聶榮,Holly H.Wang.遼寧省農戶參與農業保險意愿的實證研究[J].數學的實踐與認識,2011,(4).
[7]王韌.歐盟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機制及啟示[J].求索,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