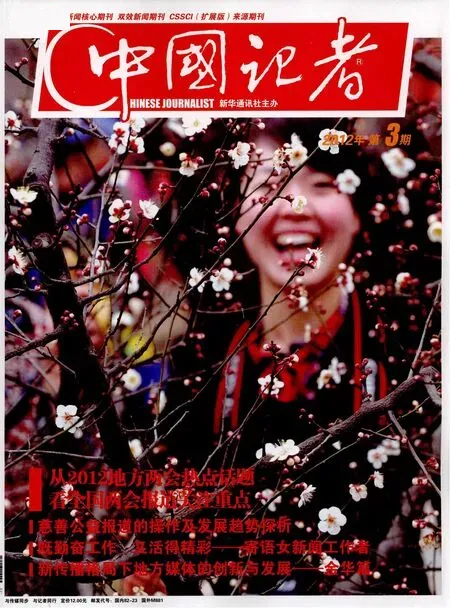金華:一份新型城市黨報的發展觀察
□ 文/ 本刊記者 張 壘 王清穎
從北京到金華,如果搭乘飛機,有兩條路可走。
一是飛到杭州蕭山機場,再從蕭山到金華,兩小時車程;二是飛到義烏機場,再從義烏到金華,開車四十分鐘。
這個頗為獨特的路線圖一下子就給金華定了位——既繞不開省城,也離不了“縣城”。來自上下兩方面的壓力是金華報業面臨的首要問題。
兩年前,總部位于杭州的《錢江晚報》《都市快報》陸續進入金華,部分報紙在金華的廣告營業額迅速向千萬靠近。金華下轄義烏、永康、東陽、蘭溪四個縣級市,其中歸屬義烏市委主辦的《義烏商報》年廣告營業額6700余萬,隸屬省報集團的《永康日報》《東陽日報》,年廣告營業額均在3000萬左右。
就單張報紙廣告經營額來說,《義烏商報》高于《金華日報》(《金華晚報》廣告經營額與《金華日報》相當);《永康日報》《東陽日報》約為《金華日報》的三分之二,緊隨其后。
浙江縣域經濟極為發達。與其他省份不同,浙江各縣財政直接上繳省廳,地市從縣級經濟繁榮中分潤有限。與其他地市不同,金華歷史上就是“府小縣大”,今日義烏自不必說,而即使是在清代民國,即有“小小金華府,大大蘭溪縣”之說。金華號稱“八婺”大地,但同時,金華至少有八種以上的方言,乃至于土生土長的義東(義烏東部)人聽不懂義烏話。
不是玩笑。在以金華打頭的報紙上,縣市廣告只占其廣告總額的百分之五六。
考慮到這種現實,《金華日報》與《金華晚報》總計23萬上下的發行量、億元左右的廣告經營額(根據金華日報社2010年的數據推算),實屬不易。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金華本地市場的潛力已經得到相當大的開發,進一步發展很容易落入“內卷化”的困境——收入利潤的上升以單位效益的遞減為代價。
在多元經營方面,金華日報社以房產為核心的多元經營收入已遠超報紙主業,2011年其收入是主營業務的兩倍。但危機亦潛伏其間。以2010年的統計為例,金華日報社多元經營中除房產外的另兩項主營業務——商務彩印、金報傳媒收入之和僅占其多元經營總收入的6.45%。在宏觀調控的大勢下,地產的護佑自然失速。
總而言之,外地媒體大舉進入、延展空間先天不足、主營業務潛力長期釋放、多元經營缺乏支撐、新媒體威脅逐漸清晰——這正是觀察金華報業發展的起點。
主業之策
從外部審視,如此下頂上壓,左推右攘的競爭環境,每一項都足對地方報紙的長期發展構成嚴重沖擊。
跳出金華之外,這也是中國地市報當前共同面臨的困局。也許城市屬下區縣并不強勢,但經濟欠發達同樣導致地市報發展缺乏“腹地”;也許其經營并不過分倚重房產,但究竟如何做實“文化產業”也乏現實之徑。
就金華來說,兩個“獨特”,讓其穩住陣腳。
一、作為黨報的《金華日報》和《金華晚報》一樣,都是市場強勢的報紙。無論發行量還是廣告經營額,《金華日報》稍稍占優。
二、面對下屬縣市報紙強大的競爭優勢,金華日報社堅持“異地” 辦報:《浙中新報》扎根義烏,《蘭江導報》居于蘭溪。甚至,就在今年1月1日,金華日報社還剛剛創刊了《金華日報·永康金報》,并有意在東陽籌辦類似專版或子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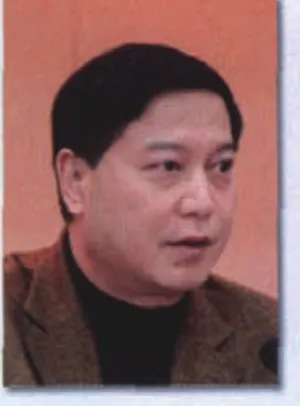
陳 東,金華日報社社長、總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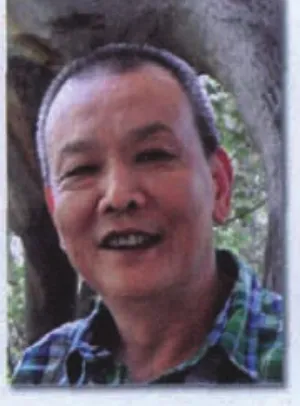
黃 健,金華日報社副社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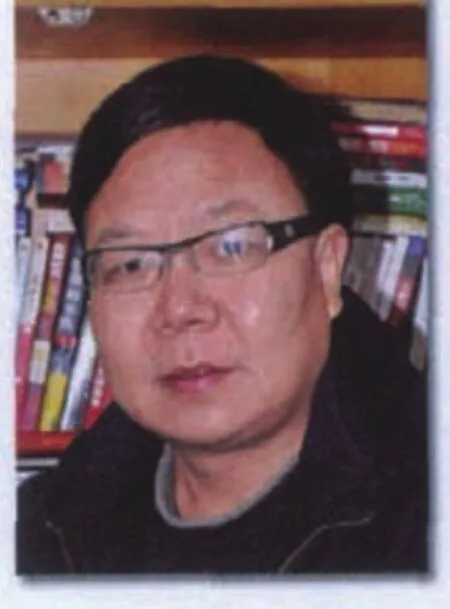
童 飆,《金華晚報》總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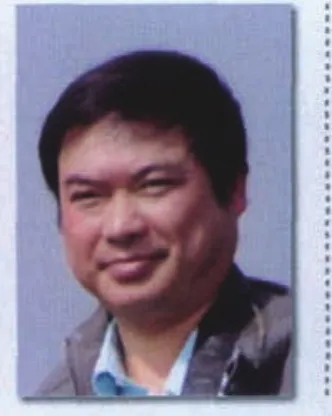
鐘曉靈,《蘭江導報》總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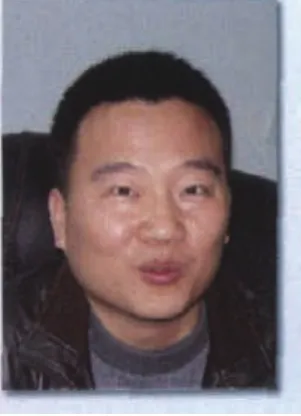
呂濟強,金華日報社永康分社副社長。
面對省內大報滲透,兩份本地市場的強勢報紙可謂“雙保險”,而“異地辦報”則解決了“府小縣大”的難題。
做大空間,黨報強勢走市場
在金華日報社社長、總編輯陳東看來,《金華日報》是一份新型城市黨報。其定位可歸結為16個字:“領導滿意、群眾喜歡、市場強勢、政治領銜”。其黨報色彩毫不含糊:“中心不突出,領導不滿意,一切等于零”。陳東要求日報對市委、政府的重大會議活動的報道必須“準確、充分、及時、規范”,同時還要體現三句話“突出主題詞、扭緊關鍵詞、盯住潛臺詞”。
“領導關心的是報紙在重大活動中的喉舌作用能不能充分發揮,要幫忙而不添亂”。在陳東看來,此外,領導也是一名普通讀者,自然樂見黨報發行量高、影響力大。“我們有12個版,領導重點關注的是一版、二版,后面的版面可以把報紙可讀性做強,還有很大空間。”
在金華報業的歷史中,創辦晚報并不意味著報紙可讀性的轉移。陳東回憶其領銜創辦《金華晚報》之時,日報并沒有騰出任何可讀性強的版面交給晚報。并且,在晚報逐漸壯大之時,反而又從晚報抽出骨干,創辦日報“周末版”,不斷增強日報的可讀性。
正是在這種相互的“補臺”中,日報和晚報攜手站穩市場。日報突出時政報道,“解讀性新聞”是其重要板塊;晚報強調“昨夜今晨”,把民生新聞作為增強其競爭力的第一步。
斗轉星移。隨后我們會看到,在報業市場競爭的流變中,黨報在市場上的強勢還有了另外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
以“補位”應對“競爭”
兩個支柱的格局既成,金華報人“馬步”立就。
面對競爭,金華報人們“反求諸已”,不斷通過競爭對手的行動發現自身內容的弱點和覆蓋的盲點。
作為黨報,日報突出權威性,同時必須面向全市廣為覆蓋。而晚報則緊抓住金華城區的市本級。“我們一定牢牢三倍于競爭對手密集發行。”《金華晚報》總編輯童飆認為,市區高密度覆蓋,“是生存之道”。換句話說,就是要讓自己“把格子畫滿”,造成受眾對報紙的高度依賴。現實中,一家外來報紙試圖走上公交,占領移動渠道,金華的報紙馬上跟進,并迅速在新的渠道中再次形成強勢。
在內容上,面對競爭對手更為活潑、靈動的特性,《金華晚報》提出“特色晚報”與“活力晚報”的定位,強調年輕,活力、新鮮。增設“探索發現”“時尚周刊”“人文周刊”,取消“夕陽紅”,相關內容并入“家周刊”。一時間,鮮活之氣充溢版面。
經過改造后,作為“超市”的報紙年輕、好看。故事和服務資訊成為多數新聞的“友好界面”。
尋找報紙增量空間
金華的難題是:除市本級之外,在金華屬下其他縣市,金華日報社則是一個真正的“外來戶”。二則,金華屬下的強勢各縣報業市場本身競爭就極為嚴酷。因應不同環境,金華尋找報紙增量的模式各各不同。
在義烏,《浙中新報》進駐前,該地已有10多家包括中央級報紙在內的媒體在此競相追逐。在永康,本地報紙《永康日報》早在1997年就開始走向市場,2000年前后,報紙自費訂閱率就已達80%,廣告經營額過千萬,利潤高達600萬。
正是于此,金華日報社下決心把原為全市發行的經濟信息報《浙中新報》變成一張市民報,同時編輯部從金華搬到義烏。找準定位,埋頭做事。面對當地《義烏商報》,新報“扎下根來,甘當老二。”當前,年廣告額近1500萬。盈利數百萬。其8萬份的發行量中,5萬集中在義烏。
永康的策略則與此不同。從設立永康分社,籌辦《金華日報·永康金報》之初,金華日報社就決定以黨報的特性來拓展這一市場。如果把《金華日報·永康金報》和《永康日報》的頭版并排放在一起,一定會給人異樣的感覺:《永康日報》報型瘦長,大幅人情味濃烈的照片,標題收斂、導讀清晰,完全一幅都市做派;而《金華日報·永康金報》則對開大版,標題粗黑、義正辭嚴,儼然一派黨報風格。
并入省報集團的《永康日報》換了“娘家”,管理模式和考核方式自然隨之而變,“民生”成為報道第一要素,除重大時政新聞外,其余領導活動報道紛紛轉至二版。而在金華報業決策者看來,永康反而出現了傳統黨報發展的空間,基于《金華日報》闖蕩市場的歷史經驗,自然,這一空間同時意味著廣告和利潤。
《蘭江導報》前身是側重于農業科技的《浙中科技報》,但現實辦報的則是早年來自《蘭溪報》的老報人。與《浙中新報》幾乎全班人馬從金華移師義烏不同,金華日報社并未向《蘭江導報》新派兵丁將帥。導報的新定位是一份“蘭江流域,面向農村的綜合類報紙”。
這些“異地”的子報,正是金華日報社未來主業發展的寄望。在金華日報社“十二五”時期發展規劃中,從2010年到2015年的五年間,金華日報社對《金華日報》和《金華晚報》廣告經營額的年均增長指標設定為8%,而《浙中新報》《蘭江導報》為14%-15%上下;在發行上,金華的日報晚報同為5%,而《蘭江導報》《浙中新報》則分別為11%和12%。
多元之道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清晰看到,面對內外競爭,金華報業強調的是“競爭與補位”的關系——應對外來競爭,從對手中發現自身盲點;應對“異地”市場,從“主人”中找出剩余空間。
這些努力或許不足以解決“外地媒體大舉進入、延展空間先天不足、主營業務潛力長期釋放”所帶來的全部問題,但畢竟打開了局面,開創了某些新的可能。
然而,相較于此,“多元發展”的問題就顯得更加棘手。
首先,房地產之外,究竟如何拓展,金華報人并沒有現成答案。
金華日報社社長、總編輯陳東設想了未來幾個可能的發展方向:其一,當地政府正在籌劃建設金(金華)義(義烏)核心區,核心區如若成型,可以擇機進入,考慮傳媒產業園等新興項目;其二,橫店影視城就位于金華的東陽,可嘗試與之合作,洽談影視項目,尤其是電視劇,數家電視臺購買即可收回成本;其三,物流與民生類項目。如呼叫中心,利潤不高,起步艱難,但做到一定規模可能會有巨變。
凡此種種,畢竟囿于設想。
好在“船到橋頭自然直”,很多事情的演變往往水到渠成。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看看過去的發展脈絡也給能我們未來的選擇提供若干參考和借鑒。
金華日報社副社長黃健介紹了多元經營的金華故事:
“我們多元經營起步比較早,大概從1984年我們就和義烏的一個老板合作過,成立一個經濟服務部;我們還租賃過下面一個縣的造紙廠,生產再生新聞紙;搞過燈具市場,但這些基本上都是微利或者虧本。所以,后來我們的項目在體制上全部搞股份制。
做房地產項目的契機是當時我們從江北搬到江南(注:婺江橫貫金華南北城區),報社領導考慮到職工工作便利,就在單位附近買了一塊土地。因為不允許集資建房,所以必須要有一個開發主體。我們于是成立一家房地產公司,負責幾個項目,包括小區的建設、(報社)大樓的建設、印務中心的建設。

1 《金華日報》集體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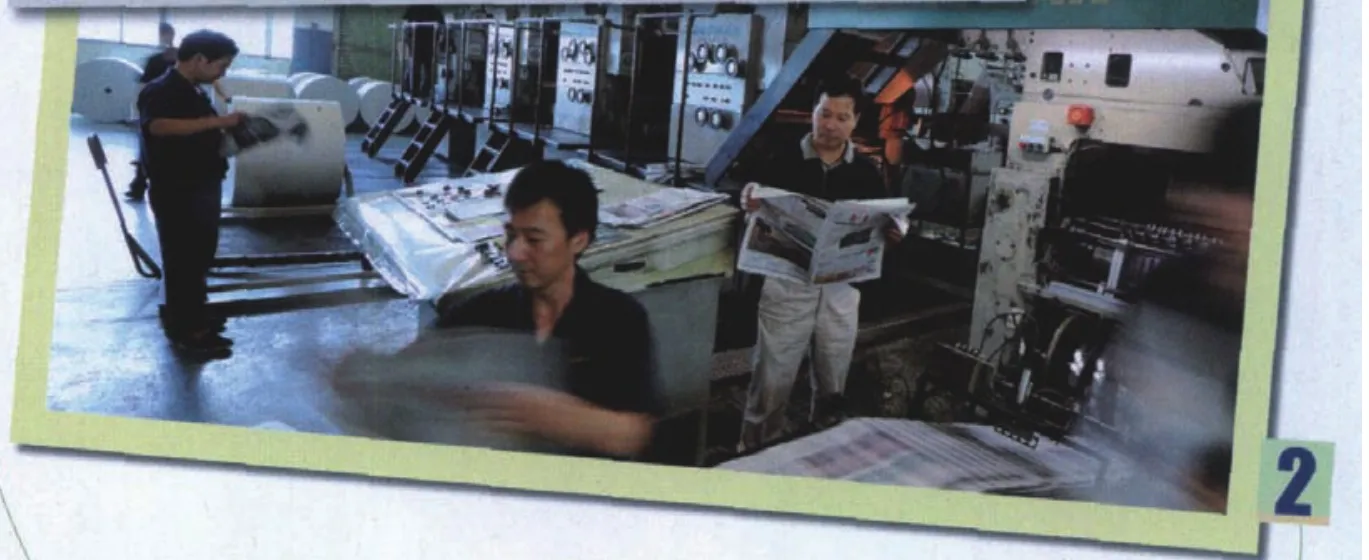
2 《金華日報》印刷廠。
項目2011年結束后,這個公司如果不開發就要注銷。所以性質變更為新聞發展總公司控股51%,另外的49%由職工自愿認購。
我們這幾年主要是節點把握比較好。別人恐懼的時候我們去拿地,地拿到以后高潮的時候也基本上出光了。另外風險控制得好。我們第一個項目是和別人合作的,拿固定回報。積累了一點兒資金。第二個項目就自己搞了,剛開始兩年正好碰到低潮,銷售壓力很大。但第二個項目大概有6000萬利潤。有一定經驗了,接下來的兩個項目就搞得就比較順。后兩個項目估計有3個多億的利潤。”
觀察金華多元經營的發展史,可以發現,金華的多元經營是“無心插柳”與“苦心經營”相互交織的結果。在市場意識引導下(公司面臨如果不開發就要注銷,其實正說明保留公司,以此作為發展的抓手是當時決策者的共識),多元經營往往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在這種自然發展過程中,相關人才團隊不斷成熟、報業獨具的品牌效應漸次顯現,走得多了,多元之路自然踩踏出來。
金華報業的體制與眾不同。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金華日報社就進行了股份制改革,成立了新聞發展總公司。新聞發展總公司中集體股占全體股份的三分之二,財政投入和個人入股加起來占其余的三分之一。這種體制使同時作為金華新聞發展總公司的金華日報社獲得了較完整的市場經營主體身份。因此,相比其它媒體單位,小到千萬,大近億元的投資項目,由于只需要通過公司董事會,其決策和審批的過程要簡單得多。
特定地區、特殊時代。金華獨特的報業體制無可復制,但即使如此,進入一個報業之外的行業,金華同樣存在尋找核心優勢的問題。正是在此刻,“文化”成了金華的“硬核”。金華日報社推出的幾個樓盤都是“金報系列”,打的是金報文化品牌,舉辦的各種活動也充滿了文化味。正是因為“嘗到了甜頭”,因此,對“金報”來說,“怎么把地產業做得更好”這個問題就顯得過于寬泛,而更準確的問題則應該是:怎么把“文化房產”做得更好?
未來之謀
媒體人討論媒體難免從自身看問題:比如“新媒體”與“舊媒體”的區分;報紙消亡還是得救的計較。恰恰在此,如果換位思考,該問的問題也許是:今天的“讀者”還是過去的讀者嗎?如果我們追求的“讀者”早已變幻,那么,報人應該如何滿足新的讀者和新的需要?
如此,那么,對當前報人——尤其是基層報人來說,最現實的考量則是:深入分析讀者需求的脈動,用新手段滿足新需要,而不是陷入對報業未來的不可知。
做好重大主題
金華日報社社長陳東認為,報紙當前最重要的是把傳統媒體的優勢延續下來。然而,判斷哪些是傳統媒體的優勢,又如何挖掘、延續、做強,并不是一件輕松之事。對一些地方媒體花大力氣投入到全國兩會等重大報道中,陳東一度很不理解。這類報道往往耗資費力,且是與其它媒體同題競爭,并不容易做出新意。但現在,陳東對之的評價則是“非常正確”:正是要把那些新媒體疏于“報道”,讀者對信息來源的權威性又極為看重的重大主題做足、做好,才能真正彰顯傳統紙媒的優勢。
一片喧囂之中,地方報紙就是要屹立不動。以推動地方發展的建設性態度審視滾滾拍岸的信息之濤。無昭昭之明,何以立赫赫之功?
增插時尚之翅
金華日報社的采編人員人手一部iPhone。在媒體圈,這不是什么新鮮事,甚至難免有附庸風雅之嫌:這究竟是為了顯示實力、擺擺全媒體的樣子,還是一種變相的“福利”?
指望幾部手機,全盤改變傳統媒體的運作流程,顯然近于夢囈,但是,iPhone也許還有另外一種作用——給報紙“插上時尚的翅膀”。陳東堅持,媒體人“要跟得上時代的步伐。”
配備新的“媒介融合”裝備,采編人員可更加方便地獲取有效信息。從采編實踐上說,網上博客,手機微博,這些新興的傳播渠道具備極強的“勾連”功能,博主們在評論某件事的同時,往往會“泄漏”一些其它有意思,甚至有報道價值的事件,從而帶進來新線索、新信息。從理念變化上看,對那些不直接與“網絡”“微博”打交道的采編人員來說,這么一個“好玩”的東西,也能給人以新鮮刺激,從而對讀者和媒體生態的變化有更感性的認識。
顛覆互動傳統
《金華日報》微博小組組長、社文部的胡國洪對此體會頗深:2011年8月,報紙剛開微博,報社不少采編人員,包括一些報社領導都對微博抱持“無所謂”的淡然態度。然而,去年10月,發生了一場事關金華形象的“狗肉節”大論戰。其中,報紙微博的獨特作用,讓不少人對手機和微博這種“時髦”玩藝兒另眼相看。論戰起于金華郊區某地。該地一直有賣狗肉的傳統,為擴大影響,有關方面舉辦了“狗肉節”,借活動為自身發展造勢。“節日”早已有之,先前并不惹人注目。但這次,主辦方為了避免“死狗、病狗”的責難,當場宰殺活狗。現場被網友在微博上公開,立即引起動物保護組織以及一些名人的關注轉發。隨著負面輿論的擴大,事件演變成對金華的抵制和攻擊。
事件期間,《金華日報》微博第一時間發布信息,24小時轉發評論。“我們在微博上第一時間發布了活動停辦的消息。但網友馬上質疑:5000多條狗哪里去了?還有人甚至言之鑿鑿地說,活動還要辦,官方發布的消息是想暗度陳倉。”胡國洪說,“于是,我們的記者馬上到現場,直接采訪。信息發在報紙的微博上,并轉發關注此事的動物保護組織和明星們。后來,甚至陪同他們一起到金華實地考察。”在《金華日報》微博積極參與下,一些事實很快澄清,先前質疑的博主們也開始幫助金華辟謠。
整個事件,報紙微博展現的力量之大,應對能力之強,讓人贊嘆。
除了全新的互動形態,在傳統“編讀互動”方面,“新武器”的運用也十分有效。如,記者常會把報道放在微博上,聽聽網友們的評論和留言,借此更好地把握讀者需求。有記者曾在微博上放了一條很短的報道,介紹池塘里種稻谷的新技術。結果微博上的各種討論極為熱烈。有意思的是,大家討論最多的不是這種技術好壞,可行與否,而是:稻子熟了該怎么收割?
影響基層社區
新媒體是個“燒錢”的行當。買設備、建隊伍,如果換不回持續穩定的收入,很可能給地方報紙帶來沉重壓力。陳東對耗資巨大的“戶外屏”心存疑慮,但對種種“進社區”的想法卻極為積極。對地方報紙來說,借助新媒體的機會,建立貼近基層的新渠道,是一條清晰明確的康莊大道。借用新的形式,擴大傳統影響,誰說新媒體不能延伸報紙的生命力?
總之,對地市報來說,樹立“新媒體觀”的同時,千萬別忘了建立“新讀者觀”。主動采取各種方式,以滿足現代讀者的新需求,是大家面對新媒體挑戰的一條務實、積極,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應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