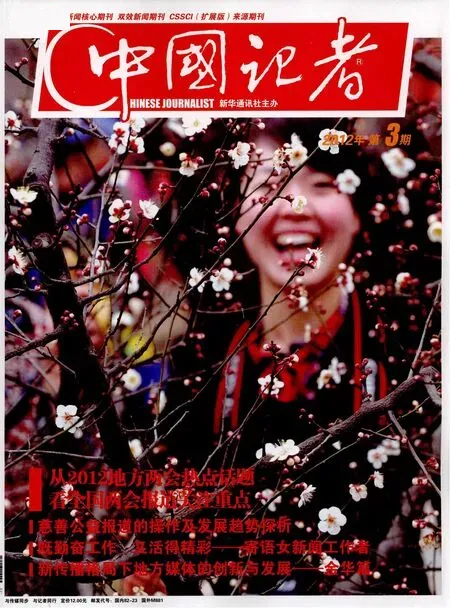媒體如何在慈善制度構建中積極作為
□ 文/王亦君
本欄編輯 陳國權 24687113@sina.com
我國公益慈善事業已經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推動慈善事業制度構建媒體義不容辭,但是,我國媒體當下在公益慈善報道中的報道理念、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少困惑甚至誤區,有著諸多不足,有時甚至傷害了整個公益慈善行業。
如果說2008年是中國慈善元年,來自民間與社會的慈善熱情在隨后的時間里持續升溫,而媒體從那一年開始對慈善的報道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對于慈善的參與和報道,也不再局限于簡單報道某個企業家、某位明星捐了多少錢;某個基金會在哪個貧困地區做了哪個援助項目,而是更主動介入,既報道單一事件,又通過質疑、監督、反思、建議,推動慈善事業制度的發展,媒體在慈善新聞中的角色已從單純的報道者向組織者、推動者轉變。
公益慈善行業與媒體行業氣質相近,精神契合,其最顯著的相似點是:都是為了公眾利益,都需要很高的公信力,公益報道不是僅僅報道公益慈善事業的進展,媒體應該利用自身的特殊職能關注和守護大眾利益。
當前公益慈善報道存在的誤區
公益慈善報道方式單一。不少都市報、商業網站的公益慈善報道多以消息的形式出現,且報道主題相對單一。如“賣身救母”“為救親人賣器官”等經常存在于報紙的社會新聞欄目、一些網站的公益頻道,這些報道的重心多是宣揚當事人的種種不幸、悲慘遭遇,而不是關注造成這一悲劇的社會意義及社會救助、公益慈善事業在機制、制度等方面的漏洞,從而使報道僅具有個案意義。這類報道的泛濫,已引起受眾審美疲勞,出現了公眾自愿捐款的乏力。
公益慈善報道過于注重富人、名人、明星、企業等群體的行為,忽視普通民眾的公益慈善之舉。
公益慈善監督報道有失客觀平衡,有“妖魔化”公益事業的傾向。公益監督報道是指媒體運用其輿論監督力量抨擊公益慈善事業運行過程中不規范行為,這表現為媒體批評、監督各類民辦或公辦的慈善會、基金會善款運作不透明行為,公益項目暗箱操作,借助公益非法牟利的違法亂紀行為,及企業家、富人、名人借助慈善的“投機”行為。媒體監督公益慈善事業,有助于我國慈善公益事業的完善與成熟,然而一些媒體在報道時,片面追求轟動效應,沒有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損害了慈善公益事業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公民自愿捐款的社會誠信文化,在民間慈善新組織新渠道還很薄弱,官辦慈善組織信譽岌岌可危的情況下,不少救助渠道被迫中斷,最初傷害的是公眾慈善熱情,最終傷害的則是弱勢群體,是普通民眾和還在蹣跚行走的中國公益慈善事業。
記者進行公益慈善報道的短板
出現以上這些誤區,原因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專業素養不足。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多年來由政府主導,因而,慈善事業在向民間公益勃興轉化的過程中,一旦深入下去,面對公益活動中出現的種種現象,媒體常常無法做出專業判斷,更不用說以先進的公益理念對讀者予以引導了。
2010年,曹德旺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向西南五省旱區貧困農戶捐款2億元,要求基金會在半年內將善款按照每戶2000元發到10萬農戶手中,要求管理費不超過3%,差錯率不超過1%,這也開創了我國捐贈者對受捐公益慈善機構問責的先河。當時網絡上出現了一些幾乎是一邊倒的聲音,罵基金會收3%的管理費太黑了,不少中央級媒體也在其中,其實,早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中國紅十字會也曾經因為從善款中提取管理費,而遭到鋪天蓋地的質疑,當時就有行政主管部門和專家學者解釋過,根據國家相關規定,提取管理費的上限是10%,因為做公益需要成本,募集善款需要成本,把救災物資運到災區也需要成本,普通民眾缺乏明確認知可以理解,媒體應該具備基本的公益慈善專業素養,理性發聲,正確引導公眾和大眾輿論。
做公益報道缺少建設性心態和大局眼光。建設性的心態不是不批評,而是在批評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從“發現問題”到“發現問題的原因”再到“促進問題解決”。媒體對于推動慈善事業發展具有責任,那么應該怎樣來履行這個職責呢?
首先應該把焦點對準公益慈善發展的社會環境,尤其是政府部門和慈善機構的關系,值得媒體深入探討。
其次,媒體不應該只對誰出錢感興趣,更要關心公益慈善機構如何用錢。一個完整的公益慈善活動,本身就包含了“捐”和“助”兩個部分。“捐”了不等于“助”了,“助”了不等于“善”了,公益慈善機構如何使用善款,往往對捐助者缺少最起碼的交代。
努力形成“人人都做慈善”的氛圍
2011年4月,許多媒體都關注了這樣一條新聞:多年來有著“中國首善”之稱的陳光標落選“中國慈善排行榜”,當時不少媒體作的解讀都是,陳光標的“高調行善”“暴力慈善”不被大眾認可了,這種現象其實反映了目前在一些媒體在慈善報道中,或多或少存在著誤區:過分關注捐贈者的行為,不能容忍捐贈者一點點瑕疵。實際上,媒體在進行公益慈善報道中,應堅持并倡導寬容而不是苛責的慈善理念、倡導慈善主體平等、人人皆可慈善、引導公眾關注慈善信息公開、著力打造透明慈善。
媒體視線并非都放在慈善精神的傳播、慈善意識的培養上,不少慈善報道是對商家做秀的展示,更多集中在對少數企業家、明星等社會公眾人物慈善行為的過分渲染和炒作上,呈示給公眾的慈善事實通常是一個個由企業、社會團體或明星們為提高自己的美譽度而舉辦的“活動”,使人們認為慈善僅是那些“有錢人”干的事,和自己無關,在社會中造成人們對慈善價值的錯誤理解,從而導致慈善精神被扭曲,違背了慈善的人文精神。媒體慈善報道的主旨是憑借其強大的社會動員功能,通過慈善事實的報道,在全社會倡導一種扶危濟困、樂善好施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的弘揚不僅是企業家、明星的社會責任,更需要全社會所有人的參與。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一些媒體報道了萬科集團捐款200萬元及王石的“十元論”,甚至提出“作人不能太王石”,從而引發無數網民對萬科及王石的圍攻和謾罵。慈善的本質是“行善者”出于愛心基礎上的主動、自愿奉獻,他們的捐助行為原本不應該受到絲毫脅迫,否則就失去了慈善的意義,但在媒體強力介入、公開點名的道德綁架下,不僅扭曲了慈善自愿的本意,變成了在輿論壓力之下,捐助者為維護自己形象和名譽的被動應對,同時在無形中也貶低了其捐助的慈善感召效應,在這種輿論氛圍下,大多數公眾只是抱著“看客”的心態看富人們到底會不會捐錢而已,把自己置身事外,真正的道義反而成了缺席者,媒體的這種不當行為不僅會損害富人對慈善的熱情,就是一般人也會對慈善心生冷漠,這無異于挖掉了社會慈善的道德根基,有悖于慈善的人本理念。
選擇捐還是不捐,捐多少,通過什么渠道捐,都是非常私密的個人選擇,媒體不征求當事人的意見即公布姓名、捐款數額是對人的財產自由處分權、隱私權、名譽權的侵害,是對人文精神的誤讀。
近年來,媒體開始選擇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平凡人的慈善行為進行報道,引導人們自發自覺地參與慈善,讓受眾逐漸接受這樣一種觀念——慈善永遠是人類所需要的,慈善體現在人們的各種行為中,善舉不僅是富人才能參與的“游戲”,社會更需要千千萬萬普通人的點滴善舉。2011年7月,第六屆中華慈善獎在京頒獎,筆者采寫了《賣羊肉串助學大叔和陳光標同獲中華慈善獎》,報道了草根慈善者阿里木用自己一根一根賣烤羊肉串賺得的錢捐資助學,事跡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阿里木是個普通人,卻做出了不普通的事,他的善舉和捐款上千萬、上億的企業家一樣打動人心,為更多普通人提供了學習的榜樣。
2010年9月30日,“股神”巴菲特在北京表示“平民慈善更值得尊敬”“每個個體對慈善的態度將推動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當更多人投身到一個社區的微小慈善事業中時,這個進程所蘊含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精神力量也將改變整個社會的行為風尚。”慈善不單是有錢人的事業,而是全社會每個人的共同事業。平等是現代慈善的基礎,因為平等,慈善的最高原則才能得以實現。任何人都沒有特權,沒有特殊待遇;任何組織都沒有強制權利,沒有強制規定。慈善不存在愛心多少之分,也不會有道德高低之分,平等慈善理念是實現人人可善、人人能善的前提和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