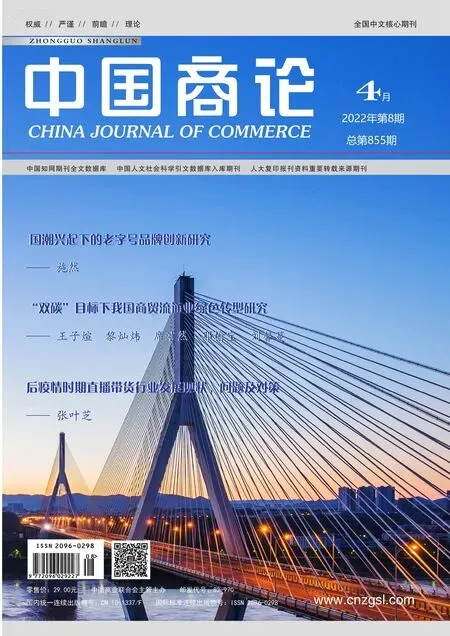企業經營從“計算的誠信”到真正的誠信
石家莊經濟學院 李春播
“瘦肉精”事件余波未了,央視《每周質量報告》又爆出某高檔家具代理公司通過保稅區“一日游”的方式用國產家具冒充洋品牌而賣出高價事件,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企業的不誠信行為再次令消費者失望。誠信作為一種婦孺皆知的社會美德,本應是我們做人做事的一種基本準則和道德底線,然而卻在企業的經營實踐中不能一貫被遵守,其緣由確實值得我們思考和分析。
導致企業經營者不誠信的原因有許多,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市場競爭以及企業和企業經營者自身的,但是歸根結底,我認為在企業經營者選擇博弈中,企業選擇誠信還是選擇欺騙不誠信決定因素是誠信的收益預期與成本預期問題,誠信的凈收益是企業最主要的考量因素。在經營實踐中,企業根據行業、市場環境、競爭和企業自身情況,對誠信收益和成本作出判斷,只有當收益預期大于成本預期,企業才有建立誠信的動機;反之,當收益預期小于成本預期,企業在不會有建立誠信的動機。
在企業經營管理中,不但有我們通常道德意義上的誠信,即“道德的誠信”,也有經過成本與收益核算后的誠信,我們把它稱為“計算的誠信”。計算的誠信與道德的誠信有著明顯的不同,道德的誠信是我們每一個人做人做事的基本準則,計算的誠信則是企業經營者面對現實的一種誠信折衷,是具有“經濟人”特征的企業“理性”選擇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企業真正做到誠信的初級階段,如果收益預期大于成本預期企業將是誠實而守信的,如果收益預期小于成本預期企業的經營將是失信,比如通過以次充好來降低成本。
我們通過計算,來說明“計算的誠信”。先以一次交易為例,一次交易亦即“一錘子”買賣,企業的選擇是恪守誠信或者欺騙不誠信,消費者的選擇是購買或者不購買,企業選擇欺騙不誠信的預期收益為:

企業選擇誠信的預期收益為:

其R1、R2為消費者購買后企業的收益,由于是一次交易,信息存在較嚴重的不對稱,我們認為消費者購買與不購買的可能性相同。很顯然,企業選擇欺騙不誠信的E1要大于E2,原因是企業不誠信行為比如偷工減料、比如以次充好、比如添加違法添加劑而帶來的企業成本的減少或者收益的增加,即R1>R2,所以從企業角度來考慮,企業的最佳選擇是不誠信。
重復多次的交易。企業的不誠信行為的結果只能是短期交易,一旦消費者知道企業不誠信他們會選擇不再購買,所以重復交易一定是企業誠信經營的結果或者是至少一個階段誠信經營的結果。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證明,只要重復交易時每次的收益率i>0,那么從長遠看,重復交易的總收益一定是大于“一錘子”買賣的收益。一般地說,重復交易的次數越多,企業誠信的收益越大。博弈論聲譽模型證明,只有在無限重復博弈中,企業才有通過守信行為建立信譽的動機。
所以,如果企業經營者是一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機會主義者,那么,他會“理性”地選擇欺騙不誠信,通過一次交易或短期交易來獲取利益,然后或者關門歇業或者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長期的重復交易雖然可以為企業帶來長期利益,但這只是理想情況下計算的結果,激勵的市場競爭和市場的不確定性都可能會使這種重復交易的利益不能夠維持長久。另外,由于我們的法律、制度對失信企業的懲罰還缺乏足夠的置信度,我們的信用體系還不夠完善,我們對失信的經濟處罰畸輕,在法律和制度處罰的能夠變通、失信的不良行為不能被記錄并傳播、失信的經濟處罰不痛不癢等情況下,企業的經營者便失去了長期誠信的耐心。再者,在我國當前階段企業收益的變化對誠信度變化不敏感,也就是說企業因為誠信而帶來的收益不大,企業因失信帶來的成本增加也不大,以至于許多企業經營者沒有長期誠信經營的動力,他們在企業初創時表現的足夠誠信,待企業建立聲譽之后,會表現出某些機會主義特征,開始試著不誠信,如果這種不誠信確實能夠給企業帶來更大的利益而沒有得到相應的懲罰,那么計算之后的不誠信將成為習慣。
如何使企業誠信,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增大企業的失信成本,使企業經營者在計算得失之后選擇誠信經營。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加大法律、制度對不誠信行為懲處的可置信度,加大失信行為的法律成本。雖然我們更多的是將失信行為歸于道德,我們多數人的多數行為應該約束于道德,但道德畢竟是一種軟約束,對那些懷有暴富心態的機會主義者來說懲治的力度有些不給力,他們往往至道德于不顧。我國現有的多部法律、制度如《合同法》、《民法通則》等都有誠信守信的法律原則,但是由于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等腐敗的產生,導致許多法律、制度等固有的神圣性、正義性、公平性和強制性被弱化、被軟化,從而導致法律、制度對失信行為懲處的可置信度降低,那些機會主義者會理性地選擇用少量的租金來換取法律懲處減小或消失,從而獲得極高的收益。相反,如果失信行為必將受到法律、制度的懲處,企業不誠信的法律、制度成本極高,那么失信行為就顯然得不償失,在衡量失信的收益與法律的制裁之后,一部分即使嚴重的機會主義者也不得不攝于法律、制度的懲處而至少會“計算的誠信”。要提升法律、制度懲處的可置信度,就要求掌握這種法律、制度裁定權和行使權的政府和政府相關官員首先要做到誠實守信、依法行政。要依法依規對那些行政不作為、慢作為、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尋租設租、收受賄賂等不誠信行為的法律裁定者、執行者進行懲處,并對這些人的不誠信行為做到零容忍,要從制度和法律層面對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加以規范,要從權力制衡角度對他們進行監督,使權力行使者在面對企業違反法律、制度等不誠信行為時能夠做到違法(或違反相關制度)必究、執法必嚴,從而提高法律、制度對不誠信行為懲處的可置信度,加大企業違約等失信成本。
(2)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強化社會信用體系對失信者社會約束和懲罰機制,加大失信行為的社會成本。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可以使不守信企業無立足之地,一旦失信處處受制,使失信者面臨極高的社會成本。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是建設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必要條件,也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以來,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已經初步形成,但其對失信者的約束和懲戒功能還非常有限,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任重而道遠。我們應該在科學認知社會信用體系功能的基礎上,用科學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重要性。當然,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在當前,我們首先要完善的社會征信體系,即央行正在完善的誠信系統,通過完善誠信體系,使企業失信行為一經核實就將其記錄在案,并且讓銀行、工商、稅務、海關、質檢等相關機構和相關企業能夠查詢的到,還要通過合法的傳播讓做到眾人皆知,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良后果,使失信企業對某個企業或消費者的失信轉為對全社會的失信,使其一處失信,處處受制,甚至無安身之地,從而大大提高其失信社會成本。
(3)增加經濟懲戒力度,加大失信行為的經濟成本。無論是法律、制度可置信度的加大還是社會信用體系對失信行為的約束和懲罰機制的加強,歸根結底要落實到經濟處罰上,沒有經濟的處罰恰恰是機會主義者們喜歡看到的。企業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獲取利潤,利潤左右著企業經營者是否誠信經營的選擇博弈,通過對失信行為的經濟懲罰使失信者不能因失信而獲得利潤,從而減少失信行為。當前我們的各種法律、法規和制度對失信行為處罰過輕,即使是按照處罰的上限也不能使失信企業感到“疼”。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總量的增大,CPI的高啟和誠信缺失的現實,我們各種法律、法規和制度規定的處罰力度也應與時俱進,提高處罰上限直至罰到失信者傾家蕩產,讓失信者感到切膚之痛。經濟懲罰的增大必然會加大企業失信成本,減少失信的可能,從而達到“計算的誠信”。
本性難移,是說一個人的個性一旦形成,我們很難改變,也就是說要使一個企業做到道德的誠信是不易的,企業經營者的個性早已形成,但是其“理性經濟人”特征,又決定其能夠在計算之后理性地選擇“計算的誠信”,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加大其失信的成本,增加守信的收益,讓其作出理性的選擇。從長遠來看,企業誠信的預期長期收益的增大或失信成本的增大可以使企業經營者“計算的誠信”,并逐漸成為他們的習慣或自覺,最終轉化為企業經營內在的“道德的誠信”,也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真正的誠信。
[1]程民選.信用的經濟學分析[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2]張維迎.產權、激勵與公司治理[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3]王地寧.企業信用管理制度缺失問題研究[D].中國優秀博士論文,2010.
[4]劉光明等.企業信用——倫理、文化、業績等多重視角的研究[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