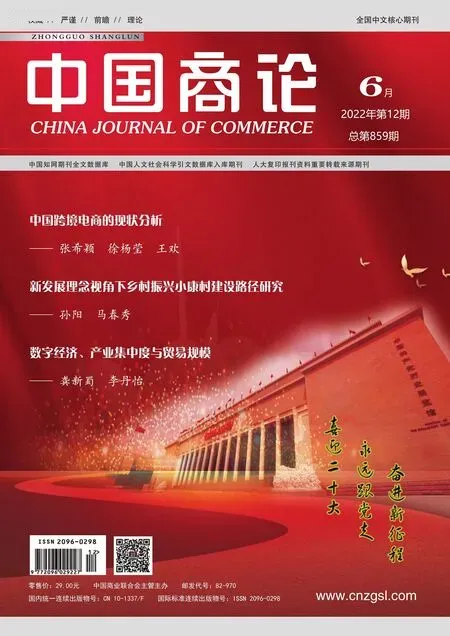交易成本、權力距離與經濟成就
北華航天工業學院 咸守衛 白桂榮 薛寧
現代的商事主體,主要為企業。現代企業,尤其是公司,是產權社會化、交易集合化和財產人格化的產物。在現代社會的經濟活動中,企業是最重要的資源擁有者和交易主體。企業具有前所未有的經營規模和財富創造能力,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本質上講,企業是文化模式的載體。不同文化類型化下的企業以其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文化理念在不同的經濟形態中謀求立足、發展和繁榮。因此,不同的權力距離能極大地改變交易成本,最終實現文化模式與經濟成就的相互促進,從而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和健康的發展。
1 交易成本理論
西方經濟學起源于15世紀的重商主義,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幾次重大的變革。以亞當·斯密為代表,在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了西方第一個經濟學理論體系,即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論證了市場經濟的必然性和高效性。但是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后,古典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壟斷進行解釋。20世紀30年代中期,張伯倫和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宣告了“斯密傳統”的結束。他們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市場的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并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學的革命。1929~1933年大危機使人們又開始重新考慮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凱恩斯區分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否定了自古典學派以來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的基本假設,認為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市場失靈”,主張政府積極地干預經濟,采取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宏觀經濟學使西方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但是凱恩斯革命本質上只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20世紀70年代出現又出現了“政府失靈”問題。由于正統經濟學提不出合適的政策主張,其地位開始動搖,新的自由主義傾向重新卷土重來,經濟學界分化出來許多新的學派。在眾多新興的經濟學流派中,其中一個重要的流派就是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使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得到了復興。
在主流經濟學中,制度(包括法律制度)都被假定為不變的因素,即常量,而不是變量。因此在進行分析時往往被排除在外的,制度(包括法律)對經濟行為的影響往往被或略掉。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出現了一個以制度為研究對象的非主流經濟學流派,即制度經濟學,后人為了將其與新制度經濟學派區分,將其稱為舊制度經濟學。其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和康芒斯。他們強調制度的功能,主張把制度當作一個變量而不是常量來加以考慮。尤其是康芒斯,他認為傳統經濟學把商品作為經濟學的基本范疇,把交易看成是物質產品的轉移是錯誤的,應當把交易關系看成是法律上權利轉移,這才有制度上的意義。
新制度主義從本質上講并不反對作為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理論,而是對新古典理論的補充和發展。這種補充和發展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密切相關的。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與物的經濟關系,即如何配置稀缺資源的技術性問題,二是人與人的經濟關系,即如何處理人們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激勵與協調、剝削與被剝削等一系列制度性問題。新制度經濟學就是要探尋資源配置的制度結構。因為,新古典理論將制度和結構假定為既定,而探究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新制度經濟學則將注意力集中于制度和結構本身,分析制度結構與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新制度經濟學所運用的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與新古典理論并無二異,如理性人、穩定偏好、最大化均衡等。新制度經濟學由四部分內容組成: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代理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
科斯認為,交易成本是獲得準確市場信息所需要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也就是說,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尋成本、談判成本、締約成本、監督履約情況的成本、可能發生的處理違約行為的成本所構成。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的根本論點在于對廠商的本質加以解釋。由于經濟體系中廠商的專業分工與市場價格機能之運作,產生了專業分工的現象;但是使用市場的價格機能的成本相對偏高,而形成廠商機制,它是人類追求經濟效率所形成的組織體。
交易成本泛指所有為促成交易發生而形成的成本。總體而言,簡單的分類可將交易成本區分為搜尋成本、信息成本、議價成本、決策成本、監督交易進行的成本和違約成本。
交易成本理論是低權力距離國家中的經濟學理論,它依據低權力距離國家的經濟制度和文化土壤。在解釋高權力距離國家的經濟現象時面臨很大的困難。單就交易成本構成來說,高權力距離模式下的企業面臨更多的隱性的交易成本。結合不同的文化結構模式,我們可以看到:“與中國等東方封建制度的單向金字塔式的結構不同,西歐封建制呈網絡金字塔型結構。國家或政府權力分散到各級封臣手中,中央集權的形成障礙重重。不僅如此,這種封建結構還深刻地影響到日后歐洲政治與制度的構建。”

圖1 東方封建結構

圖2 西方封建結構
2 權力距離
20世紀60年代,跨文化交際學最先在美國開始興起。美國人類學家霍爾的著作《無聲的語言》被認為是跨文化交際學的奠基之作。霍爾提出了“文化就是交際,交際就是文化”的觀點。此后有關跨文化交際的著述開始不斷涌現。到了1970年,國際傳播學會已經承認跨文化交際學是傳播學的一個分支。近幾十年來,跨文化交際學得到了持續的縱深發展,今天已經成為十分重要的跨學科研究領域。
相比于美國,歐洲的跨文化研究起步較晚。但是因為歐洲悠久深厚的學術傳統,研究成就依然不菲。出生于荷蘭的吉爾特霍夫斯泰德就是一個杰出的代表。在《文化之重》這部經典的著作里,他提出了文化維度的問題。與許多跨文化研究專著有所不同,霍夫斯泰德提出的理論框架及其論述都有具體的調查數據做支撐。
《文化之重》第三至第七章分別描述了五種不同的文化維度。權力距離是第三章論述的問題。“權力距離”指的是組織機構中處于弱勢地位的成員對于權力分布不平等的接受度和預期度。不同國家的文化在這個維度上有高低之分。高權力距離通常意味著在該社會對于由權利與財富引起的層級差異有較高的認同度,這些社會一般傾向于維持層級制度體系,自下而上的交流受到限制。而低權力距離則指一個社會不看重人與人之間由財富或權力引起的層級差異,而更強調地位和機會的平等。
3 經濟成就
“制度與經濟成就之間的關鍵問題是什么形式的制度組合最能促進交換利益。而且,長期經濟體制的成就是取決于制度變動的調適效率。對于制度變動的產生,諾斯在本書中強調制度與組織之間的互動。制度是行為的限制;組織則是設立來利用制度帶來的機會,并由此造成經濟體系的發展。”實際上,從文化模式來看,文化是一種更為持久穩定隱性的制度模式。不同的文化與相同的經濟形態將產生不同的互動模式。就東方封建制和西方封建制的對比來看,網絡型的相對獨立模式與市場經濟結合無疑更具有優勢。在此看來,新制度經濟學是西方學者首創的經濟學理論,在面臨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時,存在著一個基礎差別問題。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單向型金字塔模式下,存在著諸多的外部因素影響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在更宏觀的層面會影響經濟成就。首先,是經濟成就的總量問題。第二是經濟成就的分配問題。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在短期的考察來看,或者在經濟轉型來看,文化模式對于經濟發展抑制或者抵消作用更大。歷史的積淀就構成了一種路徑選擇和文化模式,進而影響了經濟成就。
4 結語
新制度經濟學作為西方正統經濟學的補充,為西方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也推動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新制度經濟學主張看待和分析經濟問題,不能就經濟論經濟,必須要結合制度環境。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不再局限于資源配置,而觸及到人與人的關系。新制度經濟學看到了制度對經濟行為的影響,將制度作為分析的變量來對待,把人的因素結合制度來考察。本文試圖從人的文化屬性來結合制度因素探討交易成本理論和經濟成就的關系。市場經濟的本質在于自由、公平、效率和法治的有機結合。競爭是市場經濟有效性的最根本保證。市場機制正是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迫使企業降低成本、提高質量、改善管理、積極創新,從而達到提高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的結果。而所有的環節的根本在于人。人的文化屬性包含了政治、宗教、哲學等一系列方面。不同的權力距離塑造了不同的企業文化、組織模式進而產生了經濟成就的差別。低權力距離的民主、自由、扁平式的模式更能降低交易成本,從而適應和推動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影響經濟成就。
[1]羅納德·哈里·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董曉燕.西方文明:精神與制度變遷[M].學林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