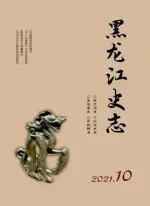鐵弗匈奴與拓跋鮮卑關系考略
胡玉春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鐵弗匈奴和拓拔鮮卑是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活動于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兩個重要民族。在他們的早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都融合了當時草原上的其他民族,其中主要是匈奴和鮮卑的融合,兩族之間本身亦具有通婚的血緣關系。鐵弗匈奴和拓拔鮮卑在十六國后期,先后在中國北方地區建立割據政權,其民族發展歷史具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為了適應環境,鐵弗匈奴和拓拔鮮卑較十六國的其他民族更加熱衷于崇尚裝扮正統。兩個民族在建立政權后,都改變了祖先譜系的記憶,分別以大禹之后和黃帝之后自詡,以此來脫離原來的群體,或接納新的成員。并且鐵弗匈奴人和拓拔鮮卑都改變了原來的姓氏,按照中原宗法制度嚴格劃分出大宗和小宗,使得政權與中原政權在皇室地位、姓氏繼承方面達成一致。這種與文化和風俗習慣相關的變革,滲透著十分強烈的政治意義,是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背景下的一個有趣圖像。然而鐵弗匈奴和拓拔鮮卑雖然在血緣上有共通、共生關系,但在雙方長達近一百五十余年的交往中,只建立過短暫的通婚,朝貢、質子等關系。敵對是兩個民族在外交上對待彼此的主要態度,這與當時的時代大背景和兩個民族自身的經營策略有重要關系。本文作者希望通過考述二者的關系,探究兩個民族敵視背后的因果。
一、鐵弗匈奴和拓拔鮮卑
鐵弗匈奴在劉虎時期,與拓跋鮮卑的外交關系有了相對明確的記載。公元272年,劉虎的叔父劉猛叛晉被殺,子副侖投奔了拓拔鮮卑,劉虎父誥升爰代領部眾,后傳劉虎,當時劉虎仍是晉所統轄下的匈奴五部帥之一,鐵弗匈奴亦依附于西晉。《資治通鑒》卷八十七西晉懷帝永嘉三年條注:“當聰、彌之末走烏丸,劉虎勾為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稱臣于淵……”。[1]由此可知公元309年,劉虎叛晉,轉而依附于劉淵。從這個時候開始,以劉虎為首領的部分南匈奴部眾開始被稱為“鐵弗匈奴”,其作為一個族群整體歷史的展開正是以背叛西晉為起點的。需要注意的是,拓拔鮮卑在發展過程中恰恰走了一條與鐵弗匈奴相反的道路。支持、依附西晉是拓拔鮮卑在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外交策略,因此拓跋鮮卑與西晉在軍事上形成了較為可靠地聯盟,拓跋鮮卑通過輔助西晉,擴張了領土。顯然,在鐵弗匈奴和拓跋鮮卑開始接觸時,他們的政治策略立場就是相背的。
公元310年,白部鮮卑在西河起兵攻襲晉并州刺史劉琨控制下的新興、雁門二郡。鐵弗劉虎舉眾于雁門以應之。在劉虎和白部攻下雁門、新興二郡后,拓跋猗盧立刻派遣猗盧出兵二萬幫助劉琨,大破白部和劉虎,并且屠鐵弗營落。這是有記載的鐵弗匈奴和拓拔鮮卑的首次沖突,二者分別站在了反晉和助晉兩個不同的陣營。此戰以后,鐵弗匈奴居住地發生遷移,被迫從新興、雁門一代西走朔方。漢滅西晉后,劉聰又以劉虎為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從漢對劉虎任命的官職可以很明顯看出所謂“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主要是針對北方勢力不斷擴大的拓拔代政權的。鐵弗匈奴和拓拔鮮卑的敵對陣營愈漸清晰。
318年,鐵弗劉虎在朔方站住腳后,兩次出兵拓跋鮮卑的西境,都遭到了拓拔鮮卑的有力回擊。劉虎死后,兒子務桓試圖改變與拓拔鮮卑的敵對關系。當時鐵弗匈奴依附的漢—前趙政權滅亡。為了保存實力,務桓在繼起的后趙政權和拓拔鮮卑之間左右逢源,與雙方都保持了緩和的外交。在此期間,務桓與拓拔鮮卑建立了通婚關系,并派子十二人為質于拓拔鮮卑。此后直到357年務桓去世,鐵弗部實際上從屬于拓跋部。務桓死后,弟閼陋頭再次挑起與拓拔鮮卑的爭端。在閼陋頭有叛跡的情況下,務桓子十二人被遣返回部落。很明顯拓跋鮮卑的意圖是“欲其自相猜離”,通過激化鐵弗匈奴內部的權利之爭來瓦解閼陋頭的勢力,并有意扶持務桓子悉勿祈爭奪權利。公元359年,衛辰繼其兄悉勿祈成為鐵弗首領后,開始有計劃的擺脫鐵弗匈奴受制于拓拔鮮卑的現狀。衛辰首先示好拓拔鮮卑,其在位時,三次遣使朝貢拓跋鮮卑,并通婚于拓拔鮮卑。可以說其時,是鐵弗匈奴人和拓跋鮮卑關系最為緩和的階段,但是這種關系僅維持了六年。365年鐵弗匈奴再次挑起與拓跋鮮卑的戰事,并最終不敵對手更向南遷移。此后,迫于拓拔鮮卑的軍事壓力,鐵弗匈奴求告前秦。376年鐵弗匈奴充當向導,引前秦兵二十萬滅亡了拓拔鮮卑的代國,鐵弗匈奴如愿以償獲得了代國西部的領地。十年之后,拓跋珪又重新建立政權,即對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北魏。北魏初期,拓跋珪積極征討周邊各部,但是并沒有主動出擊鐵弗匈奴。此期間,恰恰又是鐵弗先后三次主動出兵拓拔鮮卑,最終引火焚身。在391年鐵弗出兵北魏南部時,被拓跋反擊大敗于鐵歧山南,鐵弗部落崩潰逃散,衛辰被部下所殺,宗族五千人被殺,衛辰子勃勃逃亡后秦。鐵弗部和拓跋部第一階段的角逐告一段落。
從以上這些事件看來鐵弗部在和拓跋鮮卑的關系上有些滑稽的表現。鐵弗首領前赴后繼挑釁拓拔鮮卑,一再主動出擊,一再的敗北,直至自取滅亡。鐵弗匈奴的反復無常引發了拓跋鮮卑人極大地怒火。拓跋珪是一位有才略的君主,其自稱“歷觀古今,不義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鋸之誅。”[2](卷2,《太祖紀》)所以在其處理敵對部落的態度上多采取了溫和的手段。但是,拓拔鮮卑在對待鐵弗部的問題上顯然不同。在其誅殺了鐵弗宗族五千余人后,得知勃勃逃亡薛干部,進一步索要勃勃,遭到拒絕后,進攻薛干部所在的三城,并在城破后實施了屠城。
二、大夏國和北魏
鐵弗匈奴和拓跋鮮卑關系的第二個階段從407年到431年。這段期間鐵弗匈奴人勃勃建立了大夏國,與拓拔鮮卑建立的北魏毗鄰而居。文獻中對于大夏國建立之前的鐵弗匈奴以及勃勃繼承者赫連昌、赫連定時期,鐵弗匈奴和拓跋鮮卑的交往有較詳細的記載,但是唯獨在大夏國赫連勃勃時期,除了永興五年(413年)和神瑞元年(414年),大夏國三次小范圍掠奪北魏吏民外,雙方基本保持了相對的和平。為什么在鐵弗匈奴人最強盛的時期,兩個民族反而沒有大的戰事發生呢?考慮到鐵弗匈奴先前的表現,這種平靜表面看來確令人費解。但是我們通過分析當時兩個民族政權所處的歷史環境,兩個民族短暫的和平亦在情理之中。
赫連勃勃是鐵弗匈奴歷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他在建立大夏國后,在對待北魏的態度上,采取了較為謹慎的態度。414年,勃勃曾經派人小范圍的入寇河東蒲子,被擊退。這次是有記載的大夏國建立后首次與北魏發生沖突,可以看作是勃勃的一次試探性的進攻。不久之后北魏西河胡曹成和吐京民劉初元攻殺了大夏吐京護軍及其守士300余人。這是北魏給大夏的一個有力的警告。在整個國家的戰略上,終勃勃時期的各種策略、政策,并沒有針對北魏的,可見勃勃本身也無意進攻北魏。這可能與其先祖屢戰屢敗的歷史事實有關。但是主要還是基于大夏國整體的外交策略考慮。赫連勃勃本人具有卓越的軍事謀略。他統治時期。大夏國一個很明確的策略重心是向西南擴張,蠶食后秦領土,占據嶺北、關中之地。在外交策略上,赫連勃勃目標明確,集中力量針對后秦,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大夏國與北涼結盟、聯合北燕,除后秦外很少發動對它國的戰爭。崔浩曾經感嘆赫連勃勃在建立大夏國后不思報仇雪恥,根據鐵弗匈奴的歷史,其雪恥的對象應該是曾經滅鐵弗宗族的拓拔鮮卑,從崔浩言也可以看出,大夏國時期確實沒有發動大規模的對北魏的戰爭。
而北魏其時面臨的局勢是,西邊是宿敵大夏國,南邊是劉裕控制的東晉,北面和東北面是柔然和北燕聯盟,處于四面受困境地。413年,大夏與后秦戰事激烈的時候,姚興多次向北魏請求通婚,并且遣使朝貢,求請進女。414年姚興再次遣使求聘,415年,姚興獻女。這種跡象反映出后秦在與大夏的較量中已經有些力不可支,急需要外部力量施以援手,而與鐵弗匈奴有宿怨的拓跋正是最好的幫手,這也是拓拔鮮卑出兵大夏的一個很好的機會。可是北魏并沒有出兵助秦,此舉一為隔岸觀火,二則北魏自身亦無暇西顧。當時北魏正是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時期(409年—423年)。史料中有“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謹”,“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伐,不可發軍”等多處天災記載。[2](卷110,《食貨志》)北魏境內發生了大的災荒造成糧食短缺,人民饑困。在這種情況下,北魏沒有對勢頭正勁的赫連夏用兵是合乎常理的。同時北魏在明元帝即位后,勢力南已達黃河北岸,與東晉隔河對峙,北方尚存多個政權。明元帝開始實行收斂政策,在他統治期間,沒有發動兼并其他政權的大規模戰爭,這個政策的實施為北魏帶來了坐收漁利的實際利益,各政權之間互相吞并,至太武即位后,北方僅存西秦、北涼、北燕和夏。另外402年,柔然汗國控制蒙古草原,威脅北魏北部邊境。拓跋燾即位以后,對外政策轉變為主動出擊。其決策上主要的敵人是柔然。北魏多次進攻柔然都沒能遏制柔然的強大和南下進攻。為了防御柔然,423年北魏修筑了長城,并先后在北部軍事要地設置六鎮,派重兵把守。可以說,這段時期北魏的主要軍事策略都是針對柔然的。424年拓拔燾即位后,七次北上擊柔然,柔然勢力一度衰弱。此時恰逢赫連勃勃去世,關中大亂,于是426年在崔浩的支持下,北魏才決定發動滅亡大夏國的戰爭。從以上大夏國和北魏各自的國內形勢和外交策略來看,雙方在公元407年到公元425年沒有發生大的正面沖突是合乎情理的。
赫連勃勃晚期,大夏國諸子為爭奪皇位自相殘殺,力量大為削弱。425年赫連勃勃在大夏國政治動蕩中死去,赫連昌繼承皇位,大夏國開始走向衰落。426年,北魏乘大夏國亂主動出擊。在發動全面戰爭之前,北魏做了全面的戰爭部署,大造攻具,命專人負責君子津上造橋,講習武備,并遣使劉宋,防止了夏宋聯合出兵。在軍隊部署上,北魏以三萬騎兵為前驅,三萬步兵為后繼,步兵三萬攻城器械,另有三千騎兵做前侯。427年北魏西征大夏,大夏國都統萬城破。431年,北魏又進一步消滅了西走平涼的赫連定的勢力,大夏國正式滅亡。拓拔鮮卑最終將鐵弗匈奴人納入自己的統治范圍內,根據已有的文獻,鐵弗匈奴人甚至沒有留下較為完整的部族組織。
游牧民族之間的融合是民族融合過程中的一種重要方式。我們在討論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問題上,一般認為盡管民族之間存在矛盾沖突,但是友好交往仍然是民族關系的主流,這當然與政治背景有關。“然而歷史并不照顧我們的需要或感情,它總是矛盾的、復雜的,撲朔迷離的”。[3](P126)鐵弗匈奴和拓跋鮮卑兩個民族的交往過程中,實事求是的講雙方之間存在政治上的友好往來,但是戰爭、沖突的確是二者之間發生關系的主要方式。當然不能說他們是歷史的叛逆者。通過戰爭的交往本身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種重要途徑。在大夏國滅亡后,鐵弗匈奴人以完全瓦解分散的形式扇形被納入了北魏的統治下,并主要與拓拔鮮卑混合為一體。由于兩個民族本身在血緣上的共通和共生以及相同的經濟形態,鐵弗匈奴并未經歷民族強制同化的過程,自然融合成為其中一員,并隨著拓拔鮮卑的融合,加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二族先后成為中國歷史上消失的民族。
三、因果
在鐵弗與拓跋之間的力量對比上,鐵弗匈奴根本不具備對抗拓拔鮮卑的能力,無論是主動出擊還是被迫防御,文獻中沒有一次成功的戰例。那么為什么鐵弗匈奴還要一再挑釁拓拔鮮卑。而且據現有記載,鐵弗部在建國前沒有和周圍的其他部落發生大的戰爭,只把苗頭指向拓跋。其中到底有什么樣的原因。我認為,鐵弗匈奴的這種舉動,主要與其想要爭奪回其原來的居住地有關。鐵弗匈奴和拓跋鮮卑在經濟形態上,都并非純粹的游牧民族,他們共享北方農牧交錯帶的資源,地域文化、經濟模式趨同,甚至于發展歷史非常依賴于有限的環境資源,因此將對手吞并或者驅逐,爭奪生存資源是他們首要的戰爭任務。
鐵弗匈奴是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的后裔。建安中,曹操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公元216年,呼廚泉入朝于魏,被曹操留在了鄴城,曹操將南匈奴分為五部,并派右賢王去卑回平陽管理監督各部。后因左賢王劉豹的勢力膨脹,為削弱其勢,鄧艾上言:“聞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4](卷28,《鄧艾傳》)曹魏嘉平三年(251 年),景王司馬師聽從鄧艾建議,遂扶植去卑之后使居雁門(治今山西代縣西南古城)。拓跋猗盧居定襄盛樂后,295年出并州,遷雜胡于云中、五原,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之諸部。其勢力已經威脅到了鐵弗匈奴的生存環境。310年白部鮮卑在西河起兵時,鐵弗劉虎舉眾于雁門以應之。可見當時鐵弗劉虎仍然居住在雁門附近一帶,其攻擊的目標正是西晉雁門、新興二郡。戰爭失敗后,鐵弗匈奴居住地發生遷移,被迫從新興、雁門一代西走。其原來的活動區域被西晉轉讓給了拓跋鮮卑人。因此可以認為,劉虎一直主動出擊拓拔鮮卑,雖屢遭挫折而不放棄,還是出于對其先生存地帶資源爭奪的考慮。劉衛辰占據朔方以后,有感于前秦的和戎,入居塞內,大力發展農業和畜牧業。這個時期,劉衛辰基本保持了與拓跋鮮卑的友好關系。我們可以推測,這一時期的鐵弗匈奴因為對于朔方的經營已見成效,已經不再執著于對早期生存土地的爭奪。但是朔方地區經濟的發展,對于拓跋鮮卑來說既是威脅也是一塊肥肉。于是拓跋鮮卑主動連續出擊鐵弗部,367年,北魏掠得鐵弗匈奴“馬牛羊數十萬頭”391年“獲牛羊二十余萬”;同年攻破衛辰時“收其積谷”,收其名馬三十余萬,牛羊四百余萬,漸增國用。可見,對生存資源的掠奪仍然是鐵弗匈奴和拓跋鮮卑之間戰爭的首要任務。
就戰爭策略而言,拓跋鮮卑在對待鐵弗匈奴的問題上有軸向的計劃,即有通婚以誘其好,又有離間以分其勢,同時質子以脅其危。北魏建立后,在戰略上對鐵弗匈奴也非常重視。在首先出兵討伐鐵弗還是柔然的問題上,拓跋燾曾經多次問策群臣,如文獻載“蠕蠕陸梁于漠北,鐵弗肆虐于三秦。”二者被稱為“二寇”。北魏國內在面臨災荒時,也擔心“屈丐、蠕蠕提挈而來”威脅到北魏云中和平城的安全。大夏國被滅亡后,蠕蠕遣使朝貢。世祖特別下詔:“今二寇摧殄,士馬無為,方將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2](卷4,《世祖紀》)由此可見北魏初年,很重視對鐵弗匈奴的戰略決策。而鐵弗匈奴則一直圍繞著家族仇恨,盲目的頻繁的發動戰爭,屢戰屢受制于拓拔鮮卑。即使其后期暫時放棄了這種仇恨的角逐,但是其本身已經成為北魏地緣政治里有阻統一的因素,仍需要有軍事行為來克服。北魏發動討伐鐵弗大夏的戰爭已經是大勢所趨。
從社會發展來看,當時社會觀念的主流在思想領域表現于漢文化的學習和效仿。在這個主流中,各民族表現出了具有差異的漢化行動。鐵弗匈奴在南匈奴的基礎書并沒有大的跨進,拋開客觀的因素不說,只是在大夏國建立后,主觀上進行過短期的、間斷性的漢化措施。而在此之前的鐵弗匈奴較之南匈奴而言實際上經歷了匈奴民族主義的復興。這是西晉末年內遷匈奴民族的普遍聲音,建立民族政權是其最終目的,尋求政權被認可是其在主觀上主導漢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拓跋鮮卑在與中原王朝開始交往以后,就經歷了連續的長期的漢化行為。其民族主義復興發生在更晚的北魏末年。在其前期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他們較大的依附了傳統眼光中的正統晉朝。其生存機遇和環境都比鐵弗匈奴有利。拓跋鮮卑在漢化上有實質性的措施,一直向較深層次發展。拓拔鮮卑的在解決民生問題上做了很多的嘗試,并且在某些階段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其統治被境內的大多數漢族和其他游牧民族所接受。而鐵弗匈奴的政策則以殘暴著稱,主要的戰斗往往涉及數十萬兵員,通過大肆的掠奪人員來補給,境內民族成分復雜,又缺少民生經營,致使“夷夏囂然,人無生賴”,[5](卷130,《赫連勃勃載記》)強制性遷徙的人口并不滿意大夏的統治。大夏國表面的平靜,全靠著強有力創業之主勃勃的暫時壓制,方能維持表面的平靜,一旦他死去,宮廷里諸子稍有紛爭,就會引起地方上無從管制的因素乘機蠢動,各地叛亂紛紛遣使依附北魏。因此鐵弗匈奴和拓拔鮮卑的較量中最終敗北并不出乎意料。從整個歷史看來拓拔鮮卑的目標性很明確,統一南下是其發展的過程中的主要目標,其戰略決策從大局著眼更具有長遠性。這決定了拓拔鮮卑最終的勝利。
[1][宋]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北齊]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李振宏、劉克輝.民族歷史與現代觀念—中國古代民族關系史研究[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4][晉]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2.
[5]][唐]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