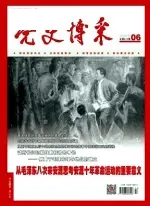中共四大前后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
潘秦保
(上海市虹口區委黨校 中國上海 200081)
中共四大前后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
潘秦保
(上海市虹口區委黨校 中國上海 200081)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民主革命時期在上海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立足于當時的革命形勢,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中共四大首次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與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是分不開的。
中共四大;陳獨秀;領導權
一、中共四大召開前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
1、從五四運動到中共一大:“勞工神圣”
從五四運動到中共一大,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初步形成。早在五四運動以前,陳獨秀就已經認識到由無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領導的“俄羅斯社會革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1]五四運動以后,陳獨秀同情工農大眾,贊同“勞工神圣”的口號,一方面,陳獨秀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從理論上認識到無產階級的地位和使命;另一方面陳獨秀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并使之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中看到了工人階級的力量。陳獨秀認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將工人階級看成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看成社會的“臺柱子”[2],并基于對無產階級的這一根本認識,積極投入了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創建工作。
2、從中共一大到中共三大:矛盾與轉變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了。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執筆的大會《宣言》指出香港海員罷工等運動,“足夠證明工人們的偉大勢力”,工人運動“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軍。”大會還強調了在同全國革命黨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聯合戰線時,必須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應集合在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旗幟下,獨立做自己階級的運動。”[3]中共二大掀起起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充分顯示了無產階級的強大力量和堅強的戰斗力。但是,“二七”慘案后,陳獨秀對工人運動的發展及其前途作了悲觀的估計,使黨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認識出現了曲折。陳獨秀在1923年4月發表的《資產階級革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中提出:民主革命的領導者是資產階級,它的勝利是資產階級的勝利,無產階級只能“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這就是“二次革命論”的由來。在此基礎上,陳提出“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其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4]在陳獨秀和共產國際錯誤估計的影響下,黨的“三大”未能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1923年11月,陳獨秀主持召開的中共三屆一次會議關于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的決議,提出共產黨“必須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5]直到國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以后,陳獨秀的這一認識才基本上被糾正過來。
3、從國民黨一大到中共四大聯合與斗爭
: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孫中山的主持下在廣州召開,這次會議的形式和規程仿照了蘇共。大會通過的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國共黨內合作的正式建立。國共合作建立以后,一方面,國民黨依靠共產黨員在工農群眾中的組織和領導作用,壯大了國民革命運動的力量;另一方面,兩黨在合作的過程中也存在著矛盾與斗爭。比如陳獨秀對國民黨依靠一派軍閥反對另外一派軍閥、組建“三角聯盟”,而不是依靠工農開展革命運動的做法提出批評,他致函國民黨領袖,并在《向導》等報刊上發文建議國民黨走工農革命的道路,指出“只有全國工人、農民、兵士之聯合的大暴動,才可以破壞全軍閥階級的軍事實力,才可以驚醒帝國主義者條約神圣的迷夢......”并建議國民黨“回到革命同盟會的時代,毅然決然下全黨動員令‘到民間去’......組織工人、農民、兵士的大民眾,不斷的為這些大民眾自身利益而奮斗......”[6]
二、中共四大期間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今虹口區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一幢石庫門建筑內召開。陳獨秀主持大會,并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做了工作報告。
1、對無產階級革命徹底性的認識
中共四大期間,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逐漸成熟。成熟的標志是陳獨秀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徹底性做了最充分的肯定。陳獨秀認為越是上層階級越具有革命妥協性,而越是下層階級越具有革命的徹底性。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往往是“急進的先鋒”、決定革命成敗的“重要分子”,國民革命的“督戰者”。這種認識貫穿于中共四大通過的一系列文件和議決案。中共四大通過的《對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之議決案》中,明確指出:“大會對于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本黨在國民黨及國民運動中的活動,使本黨日漸與實際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領導中國國民運動之趨勢,大致認為滿意。”[7]可見,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是把無產階級領導權作為黨的奮斗目標的。更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是中共四大通過的《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有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參加,并取得領導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8]
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是中共四大會議確定的一項中心議題,是中共四大的靈魂所在。中共四大不僅正確指出了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而且也提出了許多關于如何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方針與政策。陳獨秀作為當時黨的主要負責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在中共四大上的提出與陳對此問題的認識有直接的關系。
2、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與“二次革命論”
陳獨秀1923年基本形成的“二次革命論”思想其本質并非是放棄民主革命的領導權,把領導權規定給了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插入了一個資產階級專政階段。陳獨秀在中共四大之前關于資產階級基礎地位的論述并不能被理解為民主革命就是由資產階級來領導,因為他同時還說無產階級處于“督戰地位”。到了中共四大上,則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糾正和彌補了所謂“二次革命論”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地位和作用的忽視。也有學者認為,“陳獨秀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是寫給國民黨人看的。陳獨秀寫此文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孫中山,說服那些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人;而《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是寫給共產黨人看的。陳獨秀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沒有錯,當時無產階級的力量確實很弱。”[9]因此,陳獨秀從來沒有把革命局限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圍,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以建設資本主義社會。
三、中共四大以后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
中共四大之后,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對民主革命運動的領導、致力于群眾性政黨的建設、積極擴大黨員隊伍。陳獨秀等黨的領導人積極投身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尤其是投身于對震驚全世界的“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等運動的領導中。通過領導工人運動的實踐,工人階級表現出最堅決、最徹底的革命性,陳獨秀很快改變了“二七”罷工失敗后過份看重資產階級的認識,對工人階級本質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和更趨正確,甚至還得出過整個中國資產階級都“不革命”的看法。他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工人的力量》、《我們如何繼續反對帝國主義的爭斗?》等大量文章報告中,贊揚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強調中國革命必須有無產階級來領導才能勝利。
[1]《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原載《每周評論》第十八號,1919年4月20日。
[2]《新青年》第七卷6號,1920年5月1日。
[3]中共二大《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1922年7月。
[4]《向導》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第747頁。
[6]《國民黨的一個根本問題》,載《向導》第八十五期,1924年10月1日。
[7]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328頁。
[8]中共四大《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
[9]姚金果: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于《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注:本文是上海市黨校系統青年課題。
潘秦保,(1985—),男,安徽淮南人,中共上海市虹口區委黨校教師,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