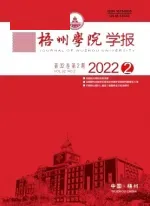論張九齡詩歌的藝術(shù)特征
李 軍
(鹽城工學(xué)院學(xué)報 編輯部,江蘇 鹽城 224051)
論張九齡詩歌的藝術(shù)特征
李 軍
(鹽城工學(xué)院學(xué)報 編輯部,江蘇 鹽城 224051)
張九齡是盛唐詩壇上一位著名詩人,其詩歌創(chuàng)作豐富多彩、精妙絕倫,有鮮明的藝術(shù)特征,如富于風(fēng)骨、勇于諫諍的美刺傳統(tǒng),多采用比興、寄托的藝術(shù)手法,情景交融、雄渾闊大的詩歌意境,清新自然、沖淡悠遠(yuǎn)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其為唐詩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xiàn)。
張九齡;詩歌;藝術(shù);特征;研究
張九齡(678-740),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guān))人,既是唐代政壇上一位賢明正直、敢于諫諍,富有才華、輔佐玄宗實(shí)現(xiàn)“開元之治”的政治家,也是詩壇上一位善于繼承創(chuàng)新、獨(dú)樹一幟、開宗立派的詩家盟主,其不僅獎挹文士,而且詩歌創(chuàng)作有鮮明的藝術(shù)個性和特色,嚴(yán)羽《滄浪詩話》曾譽(yù)其詩為“曲江體”[1],其為唐詩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xiàn)。本文擬就“曲江體”的藝術(shù)特征作一粗淺的研究。
一、富于風(fēng)骨、勇于諫諍的美刺精神
張九齡為官,素以賢明正直、極具膽識、敢于諫諍而著稱于世。故唐玄宗曾贊張九齡為“儒學(xué)之士”、“王佐之才”。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張九齡大力贊同陳子昂提倡的“風(fēng)骨”、“興寄”的漢魏傳統(tǒng),發(fā)揚(yáng)詩歌批判現(xiàn)實(shí)與干預(yù)政治的“美刺”精神,使詩歌具有豐富而充實(shí)的社會內(nèi)容,為人所稱道。胡應(yīng)麟《詩藪》云:“曲江……有漢魏之風(fēng),而唐人本色時露。”[2]35試讀其《和黃門盧監(jiān)望秦始皇陵》:“秦帝始求仙,驪山何遽卜。中年既無效,茲地所宜復(fù)。徒役如雷奔,珍怪亦云蓄。黔首無寄命,赭衣相追逐。人怨神亦怒,身死宗遂覆。土崩失天下,龍斗入函谷。國為項(xiàng)籍屠,君同華元戮。始掘既由楚,終焚乃因牧。上宰議揚(yáng)賢,中阿感桓速。一聞過秦論,載懷空杼軸。”這首詩中的以秦代唐,是詩人們經(jīng)常采用的一種藝術(shù)手法。表面上這是首懷古詠史詩,實(shí)際上卻是詩人對唐代君王發(fā)出的歷史忠告爾。曾經(jīng)在歷史上率先改革并以其強(qiáng)大的經(jīng)濟(jì)軍事實(shí)力,先后平定六國、統(tǒng)一中原而立下赫赫戰(zhàn)功、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在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以后,一方面,自己從此不思進(jìn)取,過起聲色犬馬、搜奇獵怪、驕奢淫逸、醉生夢死、求仙占卜、妄圖長生不老的荒唐腐朽生活,另一方面則敲骨吸髓般地大肆搜刮、剝削黎民百姓,大興土木興建宮室廟宇,以供自己享樂;同時又奉行高壓政策,嚴(yán)酷鎮(zhèn)壓民眾的反抗,把自己的享樂生活建立在黎民百姓的痛苦之上,“黔首無寄命,赭衣相追逐。人怨神亦怒,身死宗遂覆”。物極必反,其終于激起陳勝、吳廣領(lǐng)導(dǎo)大澤鄉(xiāng)農(nóng)民起義,一時天下人云集而響應(yīng),項(xiàng)羽繼而發(fā)難,一把大火,將秦始皇苦心經(jīng)營的阿房宮燒成灰燼,秦王朝也在頃刻間土崩瓦解。詩人借秦始皇因聲色犬馬、窮奢極欲而遭致民眾群起而討之,最后落得個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的歷史事件,向唐朝統(tǒng)治者敲起歷史的警鐘,須知“成由勤儉敗由奢”、“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絕不可輕視民眾的力量,任何的倒行逆施或微小差錯都會使自己陷入無可救贖的境地。可以說,這首詩的主旨、立意與賈誼的《過秦論》是高度一致的,其根本目的就是為唐朝統(tǒng)治者由秦王朝的滅亡中吸取歷史教訓(xùn),居安思危,以防重蹈歷史之覆轍爾。顯然,詩人已深刻地認(rèn)識到當(dāng)時唐王朝中已出現(xiàn)驕奢淫逸、追求聲色犬馬、求仙占卜以圖長生等荒唐享樂的苗頭和傾向,而且其已危及到唐王朝社稷的安危與鞏固,于是煞費(fèi)苦心地借對秦始皇歌詠與感嘆,表明自己鮮明的政治態(tài)度和立場,既反映出一個成熟政治家在政治上的高瞻遠(yuǎn)矚和敏銳,也表現(xiàn)出詩人積極干預(yù)社會政治而又能大膽、委婉地提出批評的勇氣、膽識與良苦用心,更體現(xiàn)出此詩借古諷今之善于諷諫的美刺精神傳統(tǒng)與風(fēng)格特征。
再看《自始興溪夜上赴嶺》:“嘗蓄名山意,茲為世網(wǎng)牽。征途屢及此,初服已非然。日落青巖際,溪行綠筱邊。去舟乘月后,歸鳥息人前。數(shù)曲迷幽嶂,連圻觸暗泉。深林風(fēng)緒結(jié),遙夜客情懸。非梗胡為泛,無膏亦自煎。不知于役者,相樂在何年。”此詩頗有陶淵明厭惡官場爾虞我詐、拍馬奉承的惡劣風(fēng)氣及追求田園躬耕之樂的精神與風(fēng)格,如其“嘗蓄名山意,茲為世網(wǎng)牽。征途屢及此,初服已非然”,簡直就是對陶淵明《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一去三十年,誤落塵網(wǎng)中。羈鳥戀故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的繼承和化用,其思想觀念、行文脈絡(luò),甚至連詞語都是如此驚人的一致。詩人原曾有著遠(yuǎn)大的志向與抱負(fù),也有著杰出的經(jīng)緯治世之才,然其卻時常遭受到官場上一些人的無端猜疑、誹謗、污蔑與排擠,經(jīng)常為一些莫須有的原因而遭到貶官或外放,這使得詩人為此而感到十分的痛心,故而有時不得不借山水之樂來排遣與化解自己心底的愁思和苦悶之情。其《南還湘水言懷》:“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別悔前行。歸去田園老,倘來軒冕輕。江間稻正熟,林里桂初榮。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蘋。時哉茍不達(dá),取樂遂吾情。”此詩與《自始興溪夜上赴嶺》,可謂是同一意旨與風(fēng)格特征。顯然,這既是詩人對當(dāng)時社會現(xiàn)實(shí)的一種藝術(shù)反映,也是其對社會丑惡風(fēng)氣的大膽揭露、無情批判與強(qiáng)烈譴責(zé),更體現(xiàn)出其詩歌干預(yù)社會現(xiàn)實(shí)的美刺精神和傳統(tǒng)。
張九齡詩歌富于風(fēng)骨,是指其詩歌極具現(xiàn)實(shí)主義內(nèi)容和精神,如其《奉和圣制喜雨》詩,開篇即以“艱我稼穡”為百姓之憂而憂,再為當(dāng)時“黍稷黯黯”、“無卉無木”的旱情而焦慮,進(jìn)而感慨天隨人愿、普降甘霖,使得“人和年豐,皇心則怡”。雖為應(yīng)制詩,然卻反映其深沉的憂國憂民之情懷,頗為難得。《奉和圣制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臺座,人當(dāng)萬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暫揚(yáng)旌……為奏薰琴唱,仍題寶劍名。聞風(fēng)六郡伏,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yīng)疾,留侯功復(fù)成。”詩篇贊頌恩師、友人張說,奉命出使朔方,贊揚(yáng)其有運(yùn)籌帷幄、成竹在胸,英姿勃發(fā)、決勝千里的非凡文韜武略,此行當(dāng)一舉破敵安邊、勒石銘功、凱旋而還,堪稱護(hù)國安邊的“萬里城”。雖為應(yīng)制詩,卻顯得氣勢奔放,風(fēng)格豪邁,頗具盛唐邊塞詩氣象。其《餞王尚書出邊》:“漢相推人杰,殷宗伐鬼方……感恩身既許,激節(jié)膽?yīng)q嘗。祖帳傾朝列,軍麾駐道傍。詩人何所詠,尚父欲鷹揚(yáng)。”《送趙都護(hù)赴安西》:“自然來月窟,何用刺樓蘭。南至三冬晚,西馳萬里寒。封侯自有處,征馬去啴啴。”詩人大筆如椽,氣勢奔放,境界壯闊。用詞擲地有聲,聲韻鏗鏘。詩人雖是贊頌他人,亦是自勉,表現(xiàn)出一種積極進(jìn)取、奮勇殺敵、建功報國的壯志豪情,使人讀來頗受鼓舞。
張九齡詩歌的美刺精神在當(dāng)時的詩人中是極其出類拔萃的。因詩人心情耿介、守正不阿、直言敢諫常得罪于朝廷權(quán)貴和小人而遭受讒言被貶,使得其逐漸認(rèn)識到開元后期的政治漸趨黑暗與腐敗,尤其是玄宗已沉迷于享樂,喜歡聽信奸臣與小人的阿諛奉承的虛美夸飾之詞,卻聽不得貞臣的逆耳忠貞之言,故為此而深感憂慮。其《感遇》之四:“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cè)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像詩人這樣由科舉而躋身朝廷的庶族士子,自然會遭到像李林甫這樣出身于李姓皇族等官僚家庭背景的世襲士子們的抵觸與反對,后者常因皇室的庇護(hù)以及強(qiáng)大的官僚勢力的后盾而飛揚(yáng)跋扈,前者則因勢力的單薄或缺乏家庭背景而往往成為斗爭的犧牲品。“孤鴻”是詩人自比;“雙翠鳥”則喻其政敵李林甫、牛仙客耳;“池潢”比朝廷,“三珠樹”則喻高位耳;“金丸”喻讒言,更比仕途之風(fēng)險爾。詩篇通過一連串的喻象的疊加、組合,形成了一個純粹的象征藝術(shù)世界,含蓄婉轉(zhuǎn)地表達(dá)了詩人對李林甫、牛仙客等政客的諷諫之意,同時又反映了對自己能因遭讒言而潔身自好、遠(yuǎn)禍而退、躲離朝廷這個是非之地的既頗感沉重、又略顯慶幸的復(fù)雜思想感情。《感遇》之六:“西日下山隱,北風(fēng)乘夕流。燕雀感昏旦,檐楹呼匹儔。鴻鵠雖自遠(yuǎn),哀音非所求。貴人棄疵賤,下士嘗殷憂。眾情累外物,恕己忘內(nèi)修。感嘆長如此,使我心悠悠。”顯然,西沉的落日、呼嘯的北風(fēng)、慘淡的黃昏……這正象征著當(dāng)時已趨于腐敗和黑暗的社會現(xiàn)實(shí)狀況。那些只能在屋檐下、屋梁上飛來飛去、嘰嘰喳喳的燕雀,正呼朋喚友,好不得意,其不正象征著那些自鳴得意的無恥小人;而那些有著遠(yuǎn)大志向卻在恐怖情勢威逼下哀叫著飛向遠(yuǎn)方的鴻鵠,則是忠臣良將的象征,也是詩人自比。之所以會造成這樣一種“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小人得意、直臣遭罪”的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社會狀態(tài)的根源,不正是源于高高在上的那位“貴人”之所作所為嗎?由此也反映出詩人強(qiáng)烈的憂國憂民之思想情懷。像這類托物言志抒懷的詩篇很多,表現(xiàn)出詩人意在繼承和發(fā)揚(yáng)漢魏詩歌“風(fēng)骨”與“美刺”的優(yōu)良創(chuàng)作傳統(tǒng)與精神。
二、多比興、寄托的藝術(shù)手法
陳子昂提出詩歌應(yīng)繼承風(fēng)騷之比興、寄托的藝術(shù)傳統(tǒng),目的在使詩歌既形象鮮明、避免直白的議論抒情,又使詩歌蘊(yùn)藉含蓄、富有韻味。張九齡在其《鷹鶻圖贊序》中也談了風(fēng)骨、以形傳神、因象見意等問題,其《題畫山水障》:“偶因耳目好,復(fù)假丹青妍……良工適我愿,妙墨揮巖泉。變化合群有,高深侔自然……所因本微物,況乃憑幽筌。言象會自泯,意色聊自宣。對玩有佳趣,使我心渺綿”。詩人借稱贊畫家所繪之山水畫,不僅鬼斧神工、妙造自然,而且以形見意、生動傳神,還引發(fā)想象、啟迪神思。這就是其在《宋使君寫真圖贊并序》中所云“意得神傳,筆精形似”爾。自古以來,詩畫一體,藝術(shù)相通,因此詩篇若要以形傳神、見意的話,就須采用比興、寄托之手法,此外別無他途。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五云:“張曲江五言以興寄為主,而結(jié)體簡貴,選言清冷,如玉磐含風(fēng),晶盤盛露”[3],在比興、寄托手法的運(yùn)用方面,詩人頗為嫻熟,幾臻得心應(yīng)手、游刃有余、爐火純青的藝術(shù)化境。
首先是以擬人手法托物言志抒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云:“張曲江以風(fēng)雅之道,興寄為上,故一篇一詠,莫非興寄。”試讀其《郡中每晨興輒見群鶴東飛至暮又行列而返……所羨遂賦以詩》:“云間有數(shù)鶴,撫翼意無違。曉日東田去,煙霄北渚歸。歡呼良自適,羅列好相依。遠(yuǎn)集長江靜,高翔眾鳥稀。豈煩仙子馭,何畏野人機(jī)。卻念乘軒者,拘留不得飛。”詩人因久在官場,受困于官場倚強(qiáng)凌弱、爾虞我詐,以及往來送迎、阿諛奉承等清規(guī)戒律的束縛,沒有半點(diǎn)的自由,就像被困于籠中的鳥兒,尤其是還深受官場相互誣陷、攻訐、排擠、傾軋等丑惡現(xiàn)象與風(fēng)氣之害,曾幾次被貶官或外放,因此詩人十分羨慕飛鶴能直沖藍(lán)天,在云霄間自由自在地飛翔。顯然,詩人采用比興手法,借鶴言志抒懷,鶴成了詩人的化身與象征,也使得詩歌人與鶴渾然一體,二者密不可分。借物起興,表白心志,幾乎是張九齡所有詠懷詩里都用到的表現(xiàn)手法。
再如其《和黃門盧侍御詠竹》“清切紫庭垂,葳蕤防露枝。色無玄月變,聲有惠風(fēng)吹。高節(jié)人相重,虛心世所知。鳳凰佳可食,一去一來儀。”詩人以竹自比,寫自己“高節(jié)”“虛心”的美好品質(zhì)。《庭梅詠》“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更憐花蒂弱,不受歲寒移。朝雪那相妒,陰風(fēng)已屢吹。馨香雖尚爾,飄蕩復(fù)誰知”。通過寫梅花雖能經(jīng)風(fēng)雪凌嚴(yán)寒而怒放,卻不免為“朝雪”“陰風(fēng)”等所妒忌而顯得孤單、寂寞。梅花正是受人排擠、打擊的詩人形象的寫照。《詠燕》“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尤袤《全唐詩話》云詩人“為燕詩以遺林甫”[4],當(dāng)有所據(jù)。詩人以將歸的海燕自喻,表白自己既光明正大不會貪戀官位不放,也不會與人爭搶官位而搞什么陰謀詭計,更希望那些像鷹隼一樣兇殘的政敵李林甫、牛仙客等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互相猜疑。此詩妙用比興,寓意深長、耐人尋味。《感遇》之一“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jié)。誰知林棲者,聞風(fēng)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之七“江南有丹橘,經(jīng)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yùn)命唯所遇,循環(huán)不可尋。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詩人遭讒貶謫后,便繼承了屈原《橘頌》、《禮魂》的藝術(shù)手法,借花草樹木而托物言志。顯然,詩人是以比興手法,通過婉曲的方式,表明自己潔身自好的品行與節(jié)操,抒寫對李林甫等人蓄意陷害的揭露與指責(zé)。“《感遇》一二首,抒懷感事,興寄深婉,頗得風(fēng)騷之旨。”[5]
其次是以香草美人自喻,反映自己被貶途中對玄宗于朝廷的懷念之情。《感遇》之十“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冥冥愁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馨香歲欲晚,感嘆情何極。白云在南山,日暮長太息”。詩人以游女自比,言自己雖有美好的情感想向心上人表達(dá),既書信無由傳達(dá),更因?qū)Ψ骄芤姸荒芟鄷灾伦约恒俱病⒏袊@、思念不已。通過比擬的手法,抒寫賢良正直之人反遭小人讒言相害、無由申述,終不為皇上所理解的心靈創(chuàng)痛與愁苦,以及自己因此而不能輔佐皇上、建功報國的深深遺憾之情。賀裳《載酒園詩話》評曰:“初唐人專物鋪敘,讀之常令人悶悶,惟閨闈、戎馬、山川、花鳥之辭,時有善者,求其雅人深致,實(shí)可興觀,惟陳拾遺、張曲江兩公耳。”[6]
最后是以古諷今,即借懷古詠史抒寫自己的感慨。《詠史》:“穰侯或見遲,蘇生得陰揣。輕既長沙傅,重亦邊郡徙……賢哉有小白,仇中有管氏。”詩人感嘆穰侯魏冉得秦昭王賞識與重用,終為秦國建立功業(yè),連管仲也能得到本是仇人的公子小白的重用而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干,而自己遭讒言陷害而被流放就像當(dāng)年的長沙傅賈誼一樣,感慨自己懷才不遇的無盡痛苦與憂愁。顯然,這是詩人借古諷今,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爾。《登襄陽峴山》:“蜀相吟安在,羊公碣已磨。令圖猶寂寞,嘉會亦蹉跎。”詩人再登峴山感嘆物是人非,緬懷諸葛亮曾建功立業(yè)留名不朽,思念羊祜當(dāng)年盛會又是何等風(fēng)光,既感嘆自己生不逢時、未能遇上賢明之君主與風(fēng)云際會的時機(jī),又想到其現(xiàn)今皆煙消云散,諸葛亮人在哪里?羊祜碑上字已模糊不清,即使自己能如此又能怎么樣呢?故詩人不免為此而感到消沉與悲傷。這種思想、觀念在其《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賦懷湘浦吊,碑想漢川沉。曾是陪游日,徒為梁父吟”中亦有反映,屈原也好,諸葛也罷,不是都隨著歲月而遠(yuǎn)去了嗎?詩人先前那種遠(yuǎn)大的政治抱負(fù)經(jīng)過疊遭打擊與被貶流放的折磨變得低沉了許多,也愈發(fā)顯示出詩人此時心頭的巨大創(chuàng)痛。
詩人通過比興、寄托的藝術(shù)手法,既強(qiáng)化了詩歌的形象,創(chuàng)造出深遠(yuǎn)的意境,又使得詩歌風(fēng)格含蓄蘊(yùn)藉,富有韻味,進(jìn)而增強(qiáng)了詩歌的藝術(shù)感染力。
三、情景交融、闊大雄渾的詩歌意境
詩歌發(fā)展到盛唐初期,使得原本由劉希夷、張若虛等所創(chuàng)造的優(yōu)美意境也逐漸為闊大雄渾的意境所取代,盛唐氣象才真正地形成了。在這方面。張九齡的成就明顯地高于陳子昂與張說。張九齡是盛唐初期大量創(chuàng)作山水詩的詩人,并由此形成其詩歌既情景交融、又闊大雄渾的詩歌意境,給世人與后人以極大的影響。
詩人在出守洪州與桂州期間,創(chuàng)作了不少的山水詩佳作,形成其情景交融、充滿詩情畫意的詩歌意境。《臨泛東湖(時任洪州)》:“郡庭日休暇,湖曲邀勝踐。樂職在中和,靈心挹上善。乘流坐清曠,舉目眺悠緬。林與西山重,云因北風(fēng)卷。晶明畫不逮,陰影鏡無辨。晚秀復(fù)芬敷,秋光更遙衍。萬族紛可佳,一游豈能展。”山水之樂使得詩人一時忘記了自己遭貶謫的身份,為眼前的優(yōu)美景色所陶醉,筆走龍蛇,繪就一幅幅精美的山水畫卷。秋高氣爽,藍(lán)天白云;萬頃湖面,煙波浩淼;水天相接,一望無際;風(fēng)平浪靜,碧波蕩漾;點(diǎn)點(diǎn)星帆,銀光閃耀;只只快舟,疾駛而過;參天樹木,遮蔽島岸;繽紛百花,裝點(diǎn)渚嶼;游人如織,喜笑顏開;湖光山色,美不勝收。詩人借景抒情,情寓景中,景中含情,可謂是情景交融,詩情畫意。其歡快、愉悅之情與眼前明麗畫面相融合,構(gòu)成優(yōu)雅、純凈、悠遠(yuǎn)的詩歌意境,令人拍手稱奇。再如《晨坐齋中偶而成詠》“寒露潔秋空,遙山紛在矚。孤頂乍修聳,微云復(fù)相續(xù)。人茲賞地偏,鳥亦愛林旭。結(jié)念憑幽遠(yuǎn),撫躬曷羈束。仰霄謝逸翰,臨路嗟疲足。徂歲方暌攜,歸心亟躑躅。休閑倘有素,豈負(fù)南山曲”。寫景如鬼斧神工,形象生動,美不勝收;情寓于景,借景抒情,則顯得情景交融、詩情畫意,直接令讀者嘆為觀止。
詩人筆下那種境界闊大、意境雄渾的山水詩篇,更是給讀者帶來藝術(shù)美的享受和體驗(yàn)。如《奉和圣制途經(jīng)華山》:“萬乘華山下,千巖云漢中。靈居雖窅密,睿覽忽玄同。日月臨高掌,神仙仰大風(fēng)。攢峰勢岌岌,翊輦氣雄雄。揆物知幽贊,銘勛表圣衷。會應(yīng)陪玉檢,來此告成功。”詩人以夸張的手法,寫華山既聳立云天、與日月相接,使得神仙景仰,又獨(dú)尊天下、使得萬山臣服朝拜,連皇上也由此封山勒石銘功,頗有一種“登山而小天下”的氣概,盡情渲染華山的巍峨險俊、雄奇壯麗的高大形象。此詩筆力遒勁剛健,氣勢豪邁奔放,情感激越高昂,形象鮮明突出,境界宏麗闊大,意境壯觀雄渾,可謂是神來之筆。《江上遇疾風(fēng)》:“疾風(fēng)江上起,鼓怒揚(yáng)煙埃。白晝晦如夕,洪濤聲若雷。投林鳥鎩羽,入浦魚曝鰓。瓦飛屋且發(fā),帆快檣已摧。不知天地氣,何為此喧豗。”詩人揮動如椽巨筆,寫在疾風(fēng)推動下,江上波濤洶涌,勢不可擋,投林之鳥為之傷命,水中游魚被拋上岸邊而死,所到之處,更是屋塌瓦飛、帆毀檣摧;水霧蒸騰、遮蔽了天空,使得白晝?nèi)琰S昏般昏暗;聲若雷鳴,使人不寒而栗、驚恐萬狀。詩人以其神奇之筆,表現(xiàn)出一種“風(fēng)助浪威、浪趁風(fēng)勢”的駭人威勢,創(chuàng)造出一種雄奇而雄渾的詩歌意境。顯然,李白《入廬山仰望瀑布水》之“猛風(fēng)吹倒天門山,白狼高于瓦官閣”,孟浩然《臨洞庭》“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等,都是從此詩化出的,其不僅在寫法、手法方面多有借鑒和啟迪,而且其筆法、詞語、脈絡(luò)等也都有痕跡可尋。由此可見此詩的巨大而深遠(yuǎn)的影響。而《湖口望廬山瀑布泉》“萬丈洪泉落,迢迢半紫氛。奔飛流雜樹,灑落出重云。日照虹蜺似,天清風(fēng)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此詩描繪廬山瀑布,可謂是大筆涂抹,氣勢飛動,形象宏大雄偉,境界高遠(yuǎn)闊大,意境雄渾壯觀,風(fēng)格豪放雄奇,可與李白的《望廬山瀑布》相媲美。
《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明發(fā)臨前渚,寒來凈遠(yuǎn)空。水紋天上碧,日氣海邊紅。景物紛為異,人情賴此同。乘槎自有適,非欲破長風(fēng)。”描繪詩人清晨于津亭遠(yuǎn)眺,碧綠的海水與遠(yuǎn)處的藍(lán)天相接更顯得浩淼無際、渾然一體,漫天紅色的霞光與與蒸騰的紅色云氣相互映襯、烘托更顯得云蒸霞蔚、璀璨壯觀,真可謂是“海水與藍(lán)天一色,旭日同霞光齊暉”。更難得的是這雄偉壯麗的景色與詩人此時的“乘槎”、“破長風(fēng)”而泛海的遠(yuǎn)大志向抱負(fù)以及開朗樂觀的心情極為和諧一致,誠如胡應(yīng)麟《詩藪》云:“獨(dú)曲江諸作,含清拔與綺繪之中,寓神俊于莊嚴(yán)之內(nèi)”[2]77,令人稱道。詩人的另一些詩篇,既表現(xiàn)出大江大湖之風(fēng)平浪靜、煙波浩淼、一望無際的壯闊景象,又營造出一種雄渾、蒼茫、清曠、悠遠(yuǎn)的詩歌意境。如《送竇校書見餞》“江水連天色,天涯凈野氛”;《初發(fā)江陵有懷》“極望涔陽浦,江天渺不分”;《彭蠡湖上》“一水云際飛,數(shù)峰湖心出”;《自彭蠡湖初入江》“江岫殊空闊,云煙處處浮”等等,不僅反映出一種清曠、蒼茫、深邃、悠遠(yuǎn)的詩歌情韻,而且境界極其雄渾闊大,景象十分雄奇壯觀,極具盛唐氣象。
四、首開清新自然、沖淡悠遠(yuǎn)的獨(dú)特詩風(fēng)
胡應(yīng)麟《詩藪》云:“張子壽首創(chuàng)清淡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yīng)物,本曲江之清淡,益之以風(fēng)神也。”[2]35還說:“曲江之清遠(yuǎn),駭然之簡淡,蘇州之閑婉,浪仙之幽奇,雖初、盛、中、晚,調(diào)迥不同,然皆五言獨(dú)造。”[2]59詩人的藝術(shù)成就集中體現(xiàn)在山水詩的創(chuàng)作上,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清新自然、沖淡悠遠(yuǎn)的獨(dú)特詩風(fēng)方面。
試讀其《自湘水南行》“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間。雖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閑。暝色生前浦,清暉發(fā)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夕陽落下,晚霞滿天,詩人乘坐的船兒在兩岸蜿蜒起伏、連綿不斷、如畫一般的山峰中穿行,在碧波蕩漾、波瀾不驚的湘江水中行進(jìn)著,詩人雖然是因公務(wù)在身而不得不趁著黃昏催艄公開船遠(yuǎn)行,但其的心情是極其平靜、安然和閑適的。此詩以寫景為主,抒情為輔,詩人巧妙地將自己的情感融匯在其筆下的景物描寫中,借景抒情、情寓景中、情景交融渾然一體,由此而表現(xiàn)出一種清雅、疏淡、蘊(yùn)藉的詩歌風(fēng)格特征。
再如《使還湘水》“歸舟宛何處,正值楚江平。夕逗煙村宿,朝緣浦樹行。于役已彌歲,言旋今愜情。鄉(xiāng)郊尚千里,流目夏云生”。詩篇直寫詩人因出使外地長達(dá)經(jīng)年之久而歸來再游湘江時的愜意、歡快、愉悅的心情,正是詩人這種主觀上的愉悅心境,使得其眼中的景物和所處的環(huán)境也都充滿著詩情畫意,從首句“歸舟宛何處,正值楚江平”的描寫中就可以看出或發(fā)現(xiàn)。此時,夕陽落山,霞光滿天,炊煙裊裊,遠(yuǎn)處那朦朧顯現(xiàn)的村莊正是自己理想的宿營之所;想明朝,船兒在兩岸參天樹木的遮蔽下,沿著江邊緩緩前行的美妙景色,詩人為此不免有點(diǎn)陶醉其中的感覺。“言旋今愜情”是此詩的“詩眼”所在,是讀者深入、準(zhǔn)確理解此詩的鑰匙。該詩則以抒情為主,寫景為輔,然情寓于景,景中含情,詩人的心境與周圍環(huán)境是那么地和諧、協(xié)調(diào)、一致,更使得詩篇情景交融,意境清新、明朗、雅麗、悠遠(yuǎn)。另如《赴使瀧峽》、《湞陽峽》、《巡按自漓水南行》、《臨泛東湖(時任洪州)》等詩篇,都具有一種既清新、雅致、幽靜、深邃,又明麗、平和、沖淡、悠遠(yuǎn)的意境之美與風(fēng)格特征。
詩人常用一種清淡的筆墨來描繪山水景物,并將自己的主觀情思巧妙地融進(jìn)其筆下的景物意象之中,創(chuàng)造出一種清新雅致、疏淡悠遠(yuǎn)的詩歌意境,給讀者以平和、沖淡、自然之強(qiáng)烈藝術(shù)感染。如其《西江夜行》:“遙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xiāng)情。外物寂無擾,中流澹自清。念歸林葉換,愁坐露華生。猶有汀洲鶴,宵分乍一鳴。”此詩在描繪西江夜晚行舟時所見的景色方面極具特色,一是善于渲染西江夜晚那種清幽而靜謐的氣氛,如尾句“猶有汀洲鶴,宵分乍一鳴”簡直是神來之筆,其采用“以動襯靜”的藝術(shù)手法,用鶴的一聲鳴叫來表現(xiàn)、烘托西江夜晚的寂靜無聲,與王維“鳥鳴春澗中”可謂是同一技法,給讀者留下極其深刻而難忘的印象。二是用字極其準(zhǔn)確形象,如用“遙”字形容“夜”之長、之永;用“澄”來描繪“潭”之清澈、平靜;用“澹”、“清”來形容湘江水波平如鏡、清澈見底的特點(diǎn);用“寂”反映西江夜晚景色的清幽和靜謐;特別是用“悠悠”描繪“天宇”之深邃、空曠、悠遠(yuǎn)、無際,用“切切”表現(xiàn)詩人對故都故土的強(qiáng)烈思念之情,都顯得無一不準(zhǔn)確而形象;三是此詩既有視野開闊、景象宏大的一面,也有境界清麗、幽靜、深邃、悠遠(yuǎn)的一面,給讀者以深刻的藝術(shù)感受與強(qiáng)烈的情感體驗(yàn)。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轉(zhuǎn)逢空闊處,聊洗滯留情。浦樹遙如待,江鷗近若迎。津途別有趣,況乃濯吾纓。”此詩乃詩人因朝廷召還得從貶地豫章回京途中與舟行江上所作,首聯(lián)“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就形象地表現(xiàn)出詩人在歸途中,因自己得以回歸京城而歸欣然地與滾滾南去的江水告別的激動舉止,更因?yàn)樽约旱乃馐艿脑┣靡哉蜒┖推椒炊矏偟男那椋梢哉f此時詩人的心情是極其輕快、放松的。“浦樹遙如待,江鷗近若迎。”詩人巧妙地采用移情、擬人等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遠(yuǎn)處湘江兩岸那高聳云天的樹木,仿佛早就有預(yù)料和準(zhǔn)備似的,正焦急地等待著詩人的歸來;近處江面上那在云天翻飛、跟隨并繞著船兒桅桿盤旋的海鷗,正在高聲鳴叫著歡迎著詩人的回歸。詩人是多么地為此而感動不已啊,其在心頭默默發(fā)誓:愿為國家、為民眾無私奉獻(xiàn)自己的一切。正可謂“一切景語皆情語”也,全詩情寓于景,景中含情,情景交融,使得清幽的自然環(huán)境與清靜的人物心境渾然一體,使得詩歌意境既沖淡、清和,又深邃、悠遠(yuǎn)。
另如其《耒陽溪夜行》:“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zhuǎn)幽。月明看嶺樹,風(fēng)靜聽溪流。”筆調(diào)清新、雅致、自然,意境也清幽、疏淡、悠遠(yuǎn)。《溪行寄王震》:“山氣朝來爽,溪流日向清。遠(yuǎn)心何處愜,閑棹此中行。叢桂林間待,群鷗水上迎。徒然適我愿,幽獨(dú)為誰情。”山氣、晨曦、溪流、藍(lán)天、桂樹、飛鷗……景色空闊而清幽;“爽”、“遠(yuǎn)”、“清”、“閑”、“適”、“幽”,則表現(xiàn)出詩人恬然、明爽、開朗、閑適、平和的心境,更形成一種清新、幽深、沖淡、悠遠(yuǎn)的詩歌風(fēng)格。其《晚霽登王六東閣》:“試上江樓望,初逢山雨晴。連空青嶂合,向晚白云生。彼美要殊觀,蕭條見遠(yuǎn)情。情來不可極,日暮水流清。”刻畫清幽、深邃、曠遠(yuǎn)的大江及兩岸景色,再現(xiàn)詩人灑脫、飄逸的形象與清靜、豁達(dá)的心態(tài),頗為生動形象而傳神。《秋晚登樓望南江入始興郡路》:“潦收沙衍出,霜降天宇晶。伏檻一長眺,津途多遠(yuǎn)情。思來江山外,望盡煙云生。”詩人善于用簡潔的筆觸來描畫山水,繪其形,傳其神,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于言外,創(chuàng)造出一種清新自然、沖淡悠遠(yuǎn)的詩歌意境。胡應(yīng)麟《詩藪》云:“二張……于沈、宋、陳、杜景物藻繪中,少加以情致,劑以清空,學(xué)者間參,則無冗雜之嫌,有雋永之味。”[2]68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贊曰:“曲江蘊(yùn)藉”、“詩品乃醇”[7]8,信然。
劉熙載《藝概·詩概》云:“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dú)能超出一格,為李杜開先。”[8]高度評價其引領(lǐng)盛唐氣象,以及推動、促進(jìn)唐詩發(fā)展的的重要作用。在盛唐詩壇上,張九齡以其豐富多彩、精妙絕倫的詩歌創(chuàng)作,自樹一幟、開宗立派的鮮明風(fēng)格,以及所取得的杰出而重要的藝術(shù)成就,“開一代風(fēng)氣”[9],“樹一代風(fēng)范”[10],為唐詩的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xiàn),由此而奠定了其在唐詩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1]嚴(yán)羽.滄浪詩話:下冊[M]//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689.
[2]胡應(yīng)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6.
[4]尤袤.全唐詩話[M]//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78.
[5]周祖譔.中國歷代文學(xué)家評傳:唐五代卷[M].北京:中華書局,1992:405-406.
[6]賀裳.載酒園詩話[M//]郭紹虞.清詩話續(xù)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05.
[7]沈德潛.唐詩別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8.
[8]劉熙載.藝概·詩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7.
[9]喬象鐘.張九齡[M]//呂慧娟,劉波,盧達(dá).中國歷代著名文學(xué)家評傳.濟(jì)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77.
[10] 楊世明.唐詩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123.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Zhang Jiuling’s Poem s
Li Jun
(The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224051,China)
Zhang Jiuling was a well-known poet in the poetic circle during the glorious age of the Tang Dynasty.His poems are richly colorful and masterly with distinctiv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such as abundant strength of personality,courageous dissuasion of ironic tradition,artistic techniques of Bi-xing and Ji-tuo,integration of scenes and emotions,grand poetic prospect,freshly natural and remotely insipid artistic style.He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of Tang poetry.
Zhang Jiuling;poetry;art;characteristic;research
I206.2
A
1673-8535(2012)02-0057-08
李軍(1952-),江蘇濱海人,鹽城工學(xué)院學(xué)報編輯部教授,研究方向:唐宋文學(xué)。
(責(zé)任編輯:覃華巧)
2012-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