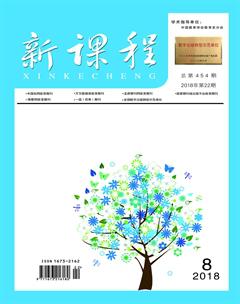關于小學語文教學中書寫教育的探究
劉海容
摘 要:近些年,隨著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電子化的書寫形式取代了手寫,使得很多小學生越來越懶于手寫漢字,導致學生缺乏規范的漢字書寫習慣。很多學生在作業中存在字跡彎彎扭扭、潦草馬虎,字體不規范而且字跡不工整等現象。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和語文課程標準(意見征集稿)中明確規定了中小學生關于寫字教學的課程標準和相關實施建議,因此,各級中小學應該對目前學生中存在的規范書寫習慣欠缺的問題給予高度重視,站在中國文化傳承的角度去對待當前小學生書寫規范的養成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小學語文;書寫規范;重要性;培養策略
一、小學語文教學中培養學生書寫習慣的重要性
小學語文教學中,學生規范書寫是提高其思想藝術修養的良好途徑,因為通過規范書寫,小學生的觀察力、注意力及記憶力都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其藝術審美能力也會逐步提高。甚至可以說從寫字能看得出一個人的性格,這個論斷是不無道理的。整潔規范的書寫給人以美好的感覺,而且可以欣賞到漢字的字形美和字理美,可謂“看字識人品”。
另外,培養小學生正確的書寫規范,養成良好的書寫習慣能使學生獲得獨立學習的能力。在寫字的過程中,大小腦的協調性幫助小學生思維的靈活運轉,增強自我控制能力來保持良好的書寫姿勢。漢字的最大特定就是整齊,剛柔相濟。規范書寫能夠從多個方面對學生進行素質的提高,規范的漢字書寫及良好的書寫習慣能夠使得學生注意力提高,忍耐力增加,觀察力和創造力也會隨之提高。這些研究都比較注重規范書寫的教育功能,而實際上,規范書寫最主要的是能夠將中國的漢字文化進行更好的傳承和發揚。
二、培養小學生書寫規范的策略
1.培養學生端正的學習態度
端正的學習態度會幫助學生在學習上花更多的時間,也會提高他們的學習效果。所謂態度,指的是學生通過學習形成的,影響學生在對某一行為選擇的內部準備狀態或者反應的傾向性。態度是學生的內部準備狀態,而不是學生已經實施的行為。同時,態度是一種穩定的內部傾向,也就是說如果學生對某個事物保持著良好的態度,他的態度就會很好。另外,態度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養出來的,當了解了這些以后,教師就會明白如何去培養學生的學習態度了。
態度的結構包括認知、情感、行為這三個部分。所以,我們可以在語文教學中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要向他們強調學習書寫的重要性,讓學生打心底重視書寫知識的學習,從潛意識里改變他們以往的學習態度,讓他們對學習有一個正確的認知。其次,我們要培養學生對學習的情感,讓他們在學習中獲得情感的體驗,體會到學習的快樂。最后促使學生在行為成分上發生改變,產生對認真書寫學習的意向或者意圖。
所以,在平時的語文教學中,我們要提醒學生提高對書寫重要性的認識,同時要強調每個漢字的筆順問題,要求學生在書寫時按著筆順的順序來書寫,因為正確的筆順也是寫好字的一個重要方面。另外,在完成作業的時候,我們要求學生書寫工整,如果學生交上來的作業比較潦草,要督促他們下次改正。經過一定時間的堅持以后,我相信學生的書寫習慣一定會有一個大的進步。
2.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教學中經常會給學生提出問題來讓他們解決。可是發現當我們把問題拋給學生以后,他們不知道從何下手。這是因為在學習的過程中,影響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的因素有很多,才會導致學生在解決問題的時候無法想出問題的答案。在語文的教學中,當學生出現書寫的問題后,他們往往不知道該怎么辦,這是因為影響學生解決問題的因素太多了。
首先是教師設置的問題情境。如果教師沒有設置好恰當的問題,不符合學生的學習基礎,那么呈現給學生的問題就會離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很遠,這樣學生思考起來就會困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按照班上學生的基礎來設置我們的教學情境,不給學生提供他們所處年齡應該掌握的字詞的書寫,那么,學生在學習中就會感到困難,在解決這些字詞的問題時就無從下手。所以,我們在設置書寫問題情境的時候要注意自己所教的年級,根據班上的大體情況制定合適的書寫問題情境。
其次是學生的定勢和功能固著影響。學生之前的學習經驗形成的已有的基礎會對他們解決問題時產生影響。有時候,這些定勢會幫助學生解決問題,有時候又會產生不利的影響。當情境不變的時候,學生以前的知識經驗會促進學生解決問題。當情境改變的時候,已有的知識經驗就會妨礙學生采取新的方法去解決現在的問題,它就會阻礙學生思維的發散。在學習中,雖然學生在每堂課中都會學到相應的知識,但是如果在今后的學習中學生不會遷移的話,就會對他們解決問題產生不利的影響,所以在學習中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會影響學生解決問題。
進入小學階段后,學生就已經開始學習語文,在不斷學習中已經掌握了一定的語文知識,同時也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思維定式。一旦他們在以前的書寫中養成了不良的習慣,在今后的學習中要想改正過來是比較困難的,這就是導致他們解決問題的定式。作為語文教師,在平時教學中就要強調書寫的重要性,讓他們在學習中養成良好的書寫習慣。當學生的書寫不好時,就要去改變他們的定式,讓他們從當前開始,逐步改變自己的思維定式,從而養成良好的書寫習慣。同時,我們也要注意教給學生書寫的技巧,讓他們在平時的練習中要把一筆一畫都寫工整,然后再去慢慢加快自己的速度。
參考文獻:
[1]王加明.養成良好書寫習慣,提升小學語文教學質量[J].科學咨詢(教育科研),2016(6).
[2]趙榮強.淺談提高小學生書寫基本技能和書法藝術欣賞能力的途徑[J].學周刊,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