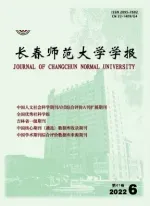狂歡化理論視閾下的《他們眼望上蒼》
王紅葉
(江蘇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江蘇鎮江 212003)
狂歡化理論視閾下的《他們眼望上蒼》
王紅葉
(江蘇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江蘇鎮江 212003)
除反映美國黑人婦女反抗性別歧視、追求自我的女性主義主題外,赫斯頓的《他們眼望上蒼》另一顯著特征是其強烈的狂歡化色彩。書中的狂歡特征主要從狂歡化廣場和狂歡儀式兩個方面體現出來。狂歡化廣場展現了黑人的愛、幽默和樂觀。加冕脫冕的狂歡儀式中蘊含著交替更新的精神。作者以狂歡的形式表達了黑人民眾對等級森嚴的官方世界的反抗和對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他們眼望上蒼》;狂歡廣場;狂歡儀式
《他們眼望上蒼》(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是佐拉·尼爾·赫斯頓(Zero Neale Hurston)的代表作。這部杰作曾一度被湮沒,在愛麗絲·沃克等作家、批評家的發掘下受到學術界關注而大放異彩。在當今美國讀書界和批評界人士的眼中,它不僅是黑人文學的經典,還是女性主義文學和20世紀美國文學的經典。故事以主人公珍妮的三次婚姻為主線,展現了一個黑人女孩反抗傳統習俗束縛、追求生命價值和幸福的經歷。作品體現了濃厚的女性主義色彩,被認為是第一部黑人女性主義作品。事實上,書中還反映了黑人的愛情、歡笑、幽默以及肯定樂觀的生活態度。小說從頭到尾滲透著濃烈的狂歡化色彩,體現著民間狂歡節的精神。
一、巴赫金的狂歡化詩學理論
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是前蘇聯著名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和思想家。他開創的復調小說理論、對話理論和狂歡化詩學理論在學術界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尤其是狂歡化詩學理論更被應用于多學科中進行研究,受到文學評論界廣泛的關注。
通過對中世紀民間狂歡文化和對拉伯雷作品的研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和《拉伯雷的創作和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兩部作品中全面地闡述了狂歡化詩學理論。狂歡化理論首先認為存在著兩種世界,人們往往過著兩種生活。一是現實世界和等級森嚴的生活。在現實生活中,等級的存在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制約著人們的一言一行,統治者擁有無限的地位與權力,而大眾對權力、統治階級和死亡只能屈從與恐懼,過著謹慎本分的生活。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之間時刻存在著一條逾越不得的鴻溝。與之相對的是第二世界,也稱為第二生活。這是狂歡化的世界與生活,是在第一世界之外建起的平民大眾的世界,是人民向往的烏托邦世界。在這種生活中,人們不再遵循等級、財產、身份等限制,“國王”與小丑地位也可以戲謔地互換,人們平等地交往、游戲、狂歡。具體表現為人與人交往中親昵地隨意接觸交往,話語中的插科打諢,將神圣崇高物俯就降格以及粗鄙譏諷等。這些狂歡化特征在赫斯頓的《他們眼望上蒼》中從狂歡廣場和狂歡儀式兩個方面得以體現。
二、狂歡廣場
在狂歡理論中,狂歡廣場有著重要的地位。“狂歡節就其意義來說是全民性的,無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親昵的交際。”[2]因此,狂歡節往往是在集市、廣場、街道等開闊的場所進行。狂歡廣場是公眾性、全民性的象征。大眾自發地聚集在狂歡廣場,隨意自由地玩笑、嬉鬧、表演。現實世界里的一切禁錮、約束得以暫時拋開,人們在這里找到生活的快樂和生命的激情。《他們眼望上蒼》中有幾處關于狂歡廣場的集中描寫。
首先是珍妮在自家后院欣賞的大自然的狂歡。珍妮16歲時,在那個情竇初開的春天,她曾經連續三天在后院觀察梨樹開花。她躺在樹下,凝視著蜜蜂在盛開的梨花間采蜜。書中是這樣描寫的:“她(珍妮)仰面朝天躺在梨樹下,沉醉在來訪的蜜蜂低音的吟唱、金色的陽光和陣陣吹過的清風之中,這時她聽到了這一切的無聲之聲。她看見一只帶著花粉的蜜蜂進入了一朵花的圣堂,成千的姊妹花萼躬身迎接這愛的擁抱,梨樹從根到最小的枝椏狂喜地戰栗,凝聚在每一個花朵中,處處翻騰著喜悅。原來這就是婚姻!她是被召喚來觀看一種啟示的。這時珍妮感受到一陣痛苦,無情而甜蜜,使她渾身倦怠無力。”[3]13梨花與蜜蜂結合的愉悅畫面讓青春懵懂的珍妮感受到內心深處莫名的狂歡與悸動。她不明白那是什么,可又令她魂牽夢縈、激動不已。這不僅代表了她理想中的大自然更象征著珍妮性意識的覺醒和對美滿婚姻的期待。這一刻,怒放的梨花、低吟的蜜蜂、金色的陽光和輕撫的微風激情交流,組成了一場大自然的狂歡,令人忘愁忘憂。做一棵開花的樹,尋找親吻它為她歌唱的蜜蜂從此成為珍妮的追求和夢想。
另一個重要的狂歡廣場在伊頓維爾鎮喬·斯塔克斯商店的門廊前。在這里,當地平民經常聚在一起聊天閑談和相互逗笑講故事。人們喜歡捉弄一個叫邁特·波納的人,因為他有一頭饑腸轆轆卻被迫終日勞作而且性情暴烈的騾子。他們談論這頭騾子將它的主人從西佛羅里達領到伊頓維爾是因為那邊老百姓一星期只吃一次軟餅面包,說它比主人還聰明還明白事理。他們告訴邁特說騾子被洗衣婦女們當成了洗衣搓板,引來邁特半信半疑的詢問,大家便看著他迷惑的表情哄堂大笑。他們取笑邁特用小茶杯給騾子盛玉米再加上皮鞭當作料喂它。當騾子追趕一個小孩的時候,突然風向一變,把騾子刮離了追趕的方向。山姆、利奇和沃特有很多“關于這頭騾子的故事:這畜牲是多么可憐,它的年紀,它的壞脾氣以及它最新的罪行。人人都縱情談論……”[3]56
后來,喬花五美元買下了騾子,讓它獲得了自由。大家依然傳說著它的所作所為。比如它在林賽家廚房里睡了一覺;因為嫌塔利太太體型難看而把她趕出槌球場;它追趕陪基·安德森,只為了躲到她傘下遮陽……甚至在騾子死后,人們還把隆重的葬禮變成了盛大的狂歡。人們以夸張的莊嚴肅穆的語氣贊美和悼念這位故去的尊貴的公民,模仿布道的樣子描述騾子死后升入騾子天堂的情景。“說到此處姐妹們假裝高興,大喊大叫,男人們不得不扶住她們。大家痛快之極,最后才把騾子交給了早已等得不耐煩的禿鷹。”[3]64
在這種狂歡式的生活中,人與人不分彼此,互相平等,可以毫無約束地取笑和戲謔,人們擺脫了特權與禁令,實現了自由與平等的理想。“這是人民大眾以詼諧因素組成的第二種生活”[4]。珍妮很想參加商店門前的聊天,她有時也能編出有趣的故事。在全鎮人去參加騾子葬禮時,珍妮也非常想加入這樣盛大的狂歡。可是喬百般阻撓,不讓她加入到平民們的閑聊中去,更不準她參加騾子葬禮。喬只當她為用來炫耀的擺設和男人的附屬物。這正是珍妮對她與喬的婚姻生活不滿和反抗的原因。
最為突出的一個狂歡場景出現在佛羅里達大沼澤地。珍妮跟隨茶點來到沼澤地,立刻就被這片自由廣袤的沃土征服了。在這里,珍妮體驗了一種與以往全然不同的生活。茶點白天挑選豆種,晚上彈吉他和玩擲骰子游戲。農忙季節開始后,茶點和珍妮過著非常舒適的生活。他們種豆子,一起去打獵。茶點還教她射擊,后來,珍妮的槍法比他還好。農忙季節開始后,人們在地里搭起了帳篷。白天,珍妮穿著工裝褲和茶點一起下地干活。到了晚上,很多廉價的酒吧音樂四起,人們熱鬧狂歡,大沼澤地充滿了野性的力量。茶點家也變成社區的中心,人們在那兒駐足聽他彈吉他。大家在一起斗嘴說笑、打牌賭博、下棋彈琴、唱歌跳舞、打獵釣魚,“一切都是為了取樂”[3]144。所有的活動珍妮都能參加,她“可以聽,可以笑,如果她愿意,甚至可以說”[3]144。茶點平等地對待珍妮,讓她做想做的任何事,這些在前兩次婚姻生活中都是不可能的。
在這塊自由自在、生氣勃勃的大沼澤地上,人們平等而親昵地交往與游戲,盡情狂歡,充滿了活力和激情。“在這個廣闊地帶,黑人們得到全身心的解放,他們親近自然,重新受到浸潤于自然的黑非洲文明之光的普照。”[5]這是打破了一切等級、身份的區別與界限的平民大眾的世界。這里的人們生活健康快樂,友好平等,仿佛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國。
此外,我國還有許多基層水利組織為財政差額撥款或自收自支事業單位,有的甚至沒有編制,由單位內部調劑或與其他科室合署辦公,無法很好地履行職責。
三、狂歡儀式
狂歡節同其他的慶典活動一樣,有非常突出的表演性和儀式性。“狂歡式”即是巴赫金對狂歡節中各種禮節、慶典、儀式的總稱,其中最為典型的當數加冕和脫冕的儀式。加冕和脫冕活動帶有濃烈的戲謔成分。扮演的國王隨時可能會被脫去王冠華服并且受到嘲笑甚至鞭打,而滑稽的小丑卻被加冕為王。最高層與最底層身份地位戲劇性的輪換從本質上說代表的是平民大眾想要擺脫森嚴的等級桎梏、獲得平等自由的愿望。它蘊涵了狂歡精神顛覆更新的本質,拉近了貴與賤、高與下、智與愚的距離。
小說中加冕和脫冕活動首先體現在珍妮的第二個丈夫喬身上。喬聰明靈活,雄心勃勃,渾身散發著征服的力量。他帶著珍妮來到伊頓維爾,在了解了當地情況后立即實施他的宏偉大業。他先買地建鎮、招募居民,再在新的伊頓維爾鎮開辦商店、建造郵局、架設路燈,還雇人清掃街道,把全鎮組織起來,并當仁不讓當選了伊頓維爾的市長。他自家蓋了帶門廊和欄桿的兩層小樓,家里擺著只有白人才會用的痰盂、辦公桌和轉椅。他還把房子刷成光閃閃的白色,這種白色揭示出喬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和對白人文化的推崇。喬聲稱要把伊頓維爾變成州里的大都會。在伊頓維爾,喬被加冕成上帝一樣的人。人們敬他畏他,稱他“我們敬愛的市長”。喬也常常自稱“我上帝”(I God)。在路燈啟用儀式上,他扮演的上帝角色更加明顯。在演講結尾,他說到:“讓它發光!讓它發光!讓它發光!”[3]48這句話就出自福音書中贊美基督耶穌是世界之光的部分。在喬買下騾子并放生以后,珍妮說的一段話也非常具有加冕的意味:“喬迪,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不是每個人都會想到這樣做的,因為這不是一個平常的想法,放了那頭騾子使你變成了一個大人物,有點像喬治·華盛頓和林肯。亞伯拉罕·林肯要統治整個美國,所以他解放了黑人,你要統治一個城市,所以你放了那頭騾子。你要解放什么必須得有權力,這使你像個國王啦什么的”[3]61。
然而,被加冕成國王的喬很快又被脫冕。喬日益衰老,因此他對珍妮的話語攻擊變得愈加刻薄和頻繁。一天,珍妮為一個顧客切雪茄頭時犯了個笨拙的錯誤,喬當著眾人的面斥責她的無能,還侮辱她的相貌。珍妮終于爆發了被壓抑已久的力量。她反駁道:“你腆著大肚子在這里目空一切,自吹自擂,可是除了你的大嗓門外你一文不值。哼!說我顯老!你扯下褲子看看就知道到了更年期啦!”[3]85這樣的侮辱讓喬感到了自己的無能,他在鎮上的名譽一敗涂地,他曾經擁有的力量煙消云散。喬的自負被珍妮當眾擊垮,他一病不起,搬到了另一間屋子,帶著對珍妮的怨恨很快死去。從實質上來說,喬代表著官方世界的權力和財富,對他的脫冕其實是平民大眾對官方世界的脫冕,是對眾生平等的渴望。
在狂歡式中,把國王脫冕成普通人的同時,小丑也被加冕成國王,這兩種反方向的運動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兩個側面。與喬的地位轉變形成對比的是那頭給鎮上人們帶來無窮話題和無限歡笑的瘦騾。起先,它是被眾人調侃的對象。人們嘲笑騾子的衰老和骨瘦如柴。大家圍成一圈逗騾子,害得它虛張聲勢地攻擊眾人,結果累得氣喘吁吁。這里,騾子顯然是小丑的形象。然而,在喬把它買下放生后,它的地位就一點一點開始改變了,它既會擅自闖入別人家中白吃白喝、盡情享受,也會嫌棄塔利太太體型難看而將她追趕出槌球場,或厭煩牧師又臭又長的祈禱而攪亂浸禮會教堂的禮拜。特別是在騾子的葬禮上,山姆模仿布道的口吻對騾子天堂的描述更具有加冕的意味:“他說到騾子天堂的歡樂,這位親愛的兄弟已離開這個苦惱谷到了那里,騾天使在周圍飛翔……在那天堂中,騾天使可以騎在人身上,親愛的死去的兄弟在天堂閃閃的寶座旁自己的位置上將俯視地獄,看到魔鬼在地獄毒熱的陽光下整天讓邁特·波納犁地,而且用皮鞭往他身上猛抽。”[3]64
原本崇高與卑下之間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加冕與脫冕的活動中變得模糊起來。尊與卑可能隨時被轉換位置,一切地位特權都被打翻在地,人人可獲得自由平等。這就是狂歡式中加冕脫冕活動的內涵。同時,狂歡式中關于死亡的辯證精神在其中也有所體現。葬禮結束后,人群一走遠,早已等在一旁的老鷹就準備美餐一頓。在動手之前,牧師老鷹和鷹群舉行了別具一格的問答性的開齋儀式:
“這人是怎么死的?”
“脂肪太少,太少。”齊聲回答。
“這人是怎么死的?”
“脂肪太少,太少。”
“這人是怎么死的?”
“脂肪太少,太少。”
“誰來承擔他的葬禮?”
“我們!!!!!”
“嗯,現在行了。”[3]65
這既是一場全民共享的盛宴,也像節日盛大的表演,全場充滿了歡慶的味道,具有明顯的狂歡特征。這里,騾子的死也不再是簡單意義上的消失,而是輪回轉化,成為滋養新生命的食物。在誕生中就孕育著死亡,而死亡中又孕育著新的誕生,這正是狂歡理論交替更新精神的體現。
四、結語
《他們眼望上蒼》無論是典型的狂歡化廣場設置或是儀式性狂歡行為描寫,都體現了文學狂歡化的特征。在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赫斯頓的這一作品顯然具有了跨時代意義。它的杰出之處不僅在于其反映的美國黑人婦女反抗性別歧視、追求自我的主題,更在于書中展現的黑人“種族健康”,即愛麗斯沃克指出的“黑人民族作為完整、復雜、未被貶低的人的觀念”[6]。在狂歡廣場上,人與人之間不再受等級、性別、財產的限制,民眾放聲歡笑,幽默機智地互相逗趣,樂觀地生活。加冕和脫冕的儀式則代表著平等自由與交替更新的精神,顛覆了占統治地位的真理和權威。大眾的笑聲克服了對官方世界的束縛和壓制的恐懼,達到一種藐視一切的狀態。作為一位有著巨大文學才華的女作家,赫斯頓在《他們眼望上蒼》中找到了一種恰當的形式描繪美國黑人民族的自豪和尊嚴,展現黑人民族的社會理想,并在狂歡式的生活方式中暫時地實現了這種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M].北京:三聯書店,1992:176.
[2]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顧亞玲,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69.
[3]佐拉·尼爾·赫斯頓.他們眼望上蒼[M].王家湘,譯.北京:十月出版社,2000.
[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白春仁,顧亞玲,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0.
[5]徐穎.《他們眼望上蒼》中黑人女性的空間拓展[J].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8(6):63.
[6]WALKER A.In Search ofOur Mother’s Gardens[M].San Diego:Harcourt Brace&Company,1983:85.
An Analysis of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nivalization
WANGHong-ye
(School ofForeign Languages,Jiangsu Universityof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njiang212003,China)
Besides its womanist theme of Anti-sexism and Self-pursuit,Hruston’s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is characterized by its carnivalesque elements,which can be seen from carnivalesque squares and carnivalesque rituals.Black people’s love,humor and optimismare shown in the carnivalesque squares.Carnivalesque rituals implythe spirit of alternating renewal.The author expressed black people’s resistance to the hierarchical world and their pursuit of freedomand equality.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God;carnivalesque squares;carnivalesque rituals
I712.45
A
1008-178X(2012) 02-0084-05
2011-12-27
王紅葉(1980-),女,江蘇鎮江人,江蘇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碩士,從事英美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