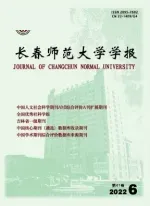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研究述評
李占鵬
(西北師范大學文史學院,甘肅蘭州 730070)
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研究述評
李占鵬
(西北師范大學文史學院,甘肅蘭州 730070)
清升平署戲曲文獻是朱希祖在1924年12月10日從北京宣武門外大街匯記書局發現并購置后才逐漸為世所知的。關于它的研究也已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對它的研究對中國戲曲文獻學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清升平署戲曲文獻;研究;述評
關于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的研究,解放前特別稀少,但也不是沒有人注意。最先是王國維《曲錄·傳奇》 (下) 開頭提到《月令承應》、《法宮雅奏》、《九九大慶》、《勸善金科》、《升平寶筏》、《鼎峙春秋》、《忠義璇圖》,還對它們的作者及內容作了簡要敘述,但王國維只見過《升平寶筏》。在戲曲史著作中部分地提到它的是1926年大東書局出版的吳梅的《中國戲曲概論》,在卷下三“清人傳奇”中列“內廷編輯本四本,《勸善金科》、《升平寶筏》、《鼎峙春秋》、《忠義璇圖》”,在后面的論述中又加了“月令承應”、“法宮雅奏”、“九九大慶”三類。其中評《升平寶筏》說“其曲文皆文敏(張照)親制,詞藻奇麗,引用內典經卷,大為超妙”;評《忠義璇圖》說“其詞皆出日下游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又鈔襲元明《水滸》、《義俠》、《西川圖》諸院本,不及文敏多矣。”[1]吳梅的評語多來源于清昭梿《嘯亭續錄·大戲節戲》。鄭振鐸1927年寫成的《文學大綱》卻未提到清升平署戲曲文獻。這令人感到奇怪,因為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是在1924年發現的,發現后就出現了相關的介紹文字,不知鄭振鐸在距離它的發現不遠的時間里寫成的專著中何以不給一席之地。但他另外寫過一篇《清代宮廷戲的發展情形怎樣》,認為“清代宮廷戲為昆山腔的戲曲發展到最高的頂點的成就,無論在劇場的構造上,在劇本的寫作上,都是空前的宏偉。”并對清代宮廷戲的簡況作了敘述[2]。對它敘寫較為詳細的學者是日本人青木正兒,這對中國戲曲史學者來說是一種不容置喙的警省和促進。青木正兒在1930年寫成的《明清戲曲史》 (后改為《中國近世戲曲史》)第十一章“昆曲馀勢時代之戲曲”第二節“乾隆期諸家”中的第一小節最先列出“內廷七種”的標目。內容如次:
乾隆初年,以海內升平,高宗乃命張照制戲曲進呈,以備內廷樂部演習,應各節令,以奏演之,所編七種:《月令承應》、《法宮雅奏》、《九九大慶》、《勸善金科》、《升平寶筏》、《鼎峙春秋》、《忠義璇圖》是也。《月令承應》應各月令以演其故事者,如《屈子競演(當為“渡”)》 (相傳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江中,故后世于端午節為競渡之戲以吊之。) 《子安題閣》 (唐王勃字子安,過南昌,九月九日登高作《滕王閣序》)諸事,無不譜入。《法宮雅奏》為祥征瑞應之事,遇內庭諸慶事則演之。《九九大慶》為神仙賜福白叟鼓腹太平等事,于萬壽節前后演之。《勸善金科》為目蓮尊者救母之事,歲暮奏之,蓋劇中鬼魅雜出,以代祓除不祥之意也。《升平寶筏》為元奘三藏赴西天取經之事,上元前后日演之。以上五種,其曲文皆為張照所親制,詞藻奇麗,大為超妙云。《鼎峙春秋》為《三國志》典故,命莊恪親王所作。《忠義璇圖》為梁山泊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二宗北狩等事,出于周祥鈺、鄒金生輩之手,抄襲《水滸記》、《義俠記》、《西川圖》等傳奇而成,多不及張照所制云(以上據《嘯亭雜錄》卷一“大戲節戲”項)。余所見者僅《勸善金科》一種耳。劇凡十本,每本各由二十四出而成,共二百四十折云。(《曲錄》卷五。一友云此劇今連載于京報之“京園戲刊”,未見)作此數劇之張照,字得天,號涇南,江蘇華亭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乾隆七年擢為刑部尚書,管理樂部,謚文敏(《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四)[3]。
這就是較早在戲曲史著作中相對詳細地提到清升平署戲曲文獻的文字。核吳梅《中國戲曲概論》,青木正兒的論述是直接參考了吳梅的內容的。從論述看,青木正兒只見過《勸善金科》,其馀的是從吳梅的論述中轉述而來。他是知道清內廷演戲的歷史的,但因為沒有親眼見過,所以把四種宮廷大戲與月令承應戲、法宮雅奏戲和九九大慶戲并列稱為內廷七種,其實,后四種不能以分名與前三類并提。這樣做,不是青木正兒的錯,而是吳梅就是這樣說的。他還敘述了此七種所敷演的大致內容以及作者的情況,這也是由吳梅的論述轉錄而來的。一個日本學者能在此典籍發現六年之后于自己的著作中對它進行如此的轉錄和敘述,雖不甚精賅,但筆者以為也是難能可貴的。鄭振鐸在1932年寫成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4]、盧前在1933年寫成的《明清戲曲史》中都未提到清升平署戲曲文獻,這也使人感到納悶[5]。周貽白1936年出版的《中國戲劇史略》提到了它[6]。同年徐慕云撰寫的《中國戲劇史》第十章“清代之南府”,對清內廷演劇從表演角度進行了較為細致的論述[7]。劉大杰1949年寫成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沒有提到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8]。
解放后,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理應受到較多關注,但由于它是為清朝統治階級的消遣娛樂服務的,所以在建國初及以后的一段時期內,仍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1962年出版的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第三冊在論述乾隆時期的傳奇和雜劇時列了六類,第一類就是宮廷戲曲,舉了張照寫的“九九大慶”和“法宮雅奏”,認為是“把戲劇做為歌功頌德的工具,內容浮泛空洞,和八股文、試帖詩毫無區別”,“這是最惡劣的創作傾向”,完全從當時政治的角度否定了清代宮廷戲曲的價值和意義[9]。1963年編成的影響最大的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就根本沒有提清升平署戲曲文獻[10]。這當然與當時傳統戲曲所處的正受批判的背景有關,一般的傳統戲曲都處于不利的位置,更不要說清代宮廷戲曲了。雖然如此,但作為一部大型的文學史教材,對這樣重要的戲曲文獻置若罔聞,是不應該的。1979年出版的周貽白的《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在第二十二節列出“內廷大戲及其演出排場”,論述較為細致,對《勸善金科》、《升平寶筏》、《鼎峙春秋》、《忠義璇圖》四部大戲的思想內容進行了簡明扼要的評析,像說《勸善金科》“無論這做法是出自編者本人或清廷授意,都是想用神道設教的辦法來鎮壓人心。勸善,實質上就是要制止當時人民對清廷的反抗,而戲中關目,則用懲惡作為對比,如‘妖言惑眾’,‘調唆鎮壓’之列入十惡,已足以看出其面目之猙獰和手段之酷辣,無非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已。”還論述了清代宮廷大戲的服飾、道具和舞臺、唱腔以及南府的制度等。除了宮廷大戲,還提到了根據節令編的“法宮雅奏”戲和“九九大慶”戲[11]。周貽白對清代升平署戲曲的態度因受時代風氣的影響還是很偏激的,幾乎沒有多少肯定,而是從否定的角度提出批評,但畢竟給了它一定的篇幅。1980年出版的吳國欽著《中國戲曲史漫話》第八十六節列出“清代宮廷的戲劇演出”,敘述了清內廷演戲的機構、舞臺及所謂內廷“四大本戲”[12],但在觀念上并沒有對清代宮廷戲給予多少肯定。1981年出版的張庚、郭漢城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是國內影響很大的一部戲曲史著作,但對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的論述篇幅更少,只用了一個自然段,介紹了張照、周祥鈺、鄒金生等詞臣編寫的《勸善金科》、《升平寶筏》、《鼎峙春秋》、《忠義璇圖》、《昭代簫韶》、《封神演義》等,認為“都是宣傳封建道德或因果報應等迷信思想的,但這些戲幾乎都是根據當時舞臺上流行的民間傳統劇目加以貫串連綴而成,因而其中往往保留了不少可供我們研究的資料。”這一評價還算比較公允,但對宮廷中的“月令承應”、“慶典承應”等戲就完全持否定態度,認為“完全是粉飾生活的歌功頌德戲劇,在外間既不流行,也都是毫無什么價值的作品。”這些評價也還沒有脫離當時左傾思潮的影響,而作為一部具有權威性的戲曲通史,這樣處理一部大型戲曲文獻,顯然也有失公允[13]。同年出版的《中國戲曲曲藝詞典》設立了升平署、南府以及《昭代簫韶》、《鼎峙春秋》、《忠義璇圖》、《盛世鴻圖》等辭條[14]。這種情況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生了一些變化,就是對它的評價變得公允起來。1983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列“南府與升平署”辭條,介紹了清代內廷戲曲的機構沿革和演出內容,對它進行了肯定性的評價,認為“南府與升平署的設立,雖為宮廷樂師而置,但客觀上也給戲曲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某些有利的條件,如不少舊演出本,詞多不通,表演藝術亦較粗俗,經入宮演唱,詞曲修改較為明暢,藝術也趨于謹嚴。升平署解散后,不少藝人留京謀生,以教戲為業,帶出的許多劇本,廣為流傳,因而保留至今。”[15]這個評價是符合清代升平署的實際情況的。1987年出版的周妙中著的《清代戲曲史》是研究清代戲曲的一部專書,而周妙中又參加過大型戲曲文獻《古本戲曲叢刊》的編纂,可以說她是此前論述宮廷戲曲的學者中最全面最深入地了解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的學者。她在該著第三章“乾隆年間的戲曲”中雖也用了一節來論述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但比以前的內容都詳盡,而且對宮廷戲的歷史反映得也比較清楚。尤其應該注意的是,她先從肯定的方面入手,說“這些歷史大戲雖然不可能做到全部都很精彩,卻也不能說毫無精華可言”,它們中“有不少片斷是相當精彩的,對后世京劇和地方戲的影響很深很廣,許多沒有機會讀書的人民群眾從中得到了不少有關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知識,受到不少階級斗爭、政治斗爭的教育,增加了識別忠奸的能力”,接著才指出了它的缺點即宣揚封建道德和迷信思想,還從藝術形式方面肯定了它對京劇、地方戲的影響[16]。1990年出版的《中國京劇史》上卷列專節從演戲體制、清廷的控制、宮廷演出場所、宮廷戲劇聲腔以及戲劇的演變等方面,探討了清代宮廷戲曲在京劇形成與成熟過程中的重要作用[17]。1992年出版的馬積高、黃鈞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在論述清代中葉戲劇時只是把宮廷大戲創作當成導致清代中葉戲曲創作不振的原因之一進行了很簡單的敘述,認為“這些大戲雖然無法在民間演出,但仍然起著箝制思想、規范戲曲創作的作用。”[18]這一評價顯然是不夠客觀的。1993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戲劇辭典》設立了“清代宮廷大戲”與“清代宮廷戲曲畫”兩個辭條[19]。1994年出版的許金榜著《中國戲曲文學史》在論述清代雜劇時涉及了內廷承應戲,指出“這類作品的內容脫離現實生活,沒有什么積極意義。它們的大量出現標志著雜劇的宮廷化,加劇了雜劇的衰亡。”這一評價顯然過于簡單化;在評價宮廷大戲時說“這些作品無非宣揚迷信忠義,場面熱鬧,規模宏大,衣飾華麗。清代傳奇的宮廷化,標志著它日益走向衰亡,但這些大戲也往往借助于前代作家同類題材的小說、劇本,吸收了許多民間傳說,保存了一些已佚劇本的片斷,有益于戲曲作家的研究。服飾、臉譜、道具、演技、唱腔、音樂也有新的發展。”[20]1997年出版的李修生主編的《古本戲曲劇目提要》沒有設立清代升平署戲曲劇目辭條,這是很令人遺憾的[21]。但同年出版的王森然主編的《中國劇目大辭典》則幾乎網羅了清代升平署戲曲劇目的全部,可以說彌補了《古本戲曲劇目提要》的缺陷[22]。1998年出版的郭預衡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第八編第三章第二節列“皇家的宮廷大戲”,在臚列了《勸善金科》等五大戲曲之后,說“這些宮廷大戲,都是二百馀出的連臺戲,規模宏大,劇情完整。由于作者多屬詞臣,而且往往受命限期完成,因此,作品多有依傍,或依據小說,或串連舊戲,故無所謂創作個性,在思想藝術方面均無可取。惟一有價值的是戲中保存了一些已佚的劇本的片斷,為中國戲曲史的研究提供了資料。”[23]1999年出版的丁汝芹著的《清代內廷演戲史話》則是第一部以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為對象撰寫的著作,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為清宮戲劇綜述,從概述、清宮演戲形式、主要演出劇目、清宮戲臺、戲裝與切末、太監伶人、內廷演戲的民間藝人諸方面進行了論述;下編為各朝演戲史事,從順治朝始到宣統朝末,對每一朝代的戲曲創作和演出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探討。它不像戲劇史和文學史,把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作為一個片斷或環節,而是對它進行全面論述,這就使對它的論述在材料的占有、分析的準確性上都特別具有優勢,不僅首次披露了一些文獻材料,而且澄清了前人搞錯了的一些問題,如把王芷章認為南府成立的時間為乾隆朝的錯誤根據新發現的資料改正為康熙朝[24]。但由于體例所限,仍然對一些問題未能作更深入的研究。2000年出版的廖奔、劉彥君著《中國戲曲發展史》不論從材料的應用與觀點的確立上都顯得比較公允、客觀,不僅論述了清宮戲曲的創作,而且論述了清宮戲曲演出,認為“宮廷大戲的出現,形成中國戲曲劇目的一大景觀,盡管編撰時詞臣們在原故事中加入了不少的道德說教和封建理念,但它們的存在和演出實踐,為以后的各地方戲劇目增添了廣泛的來源,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這是對于舊文化的一大功勞。其內容和演出形式后來被民間劇種所借鑒,演變成皮黃、梆子和各路地方戲中眾多的劇目,于是中國地方戲舞臺上就出現了無比的蘊藏量。可以說,宮廷大戲豐富了中國戲曲的寶庫,其功自不可沒。”[25]筆者以為,這是對清宮戲最公平的評價。2000年以后,還有2001年出版的郎秀華著《中國古代帝王與梨園史話》與趙楊著《清代宮廷演戲》、2002年出版的吳新雷主編的《中國昆劇大辭典》、2004年出版的鄧紹基主編的《中國古代戲曲文學辭典》與蔣星煜等主編的《明清傳奇鑒賞辭典》、2005年出版的王政堯著《清代戲劇文化史論》、2006年出版的么書儀著《晚清戲曲的變革》,2007年出版的朱家溍、丁汝芹著《清代內廷演劇始末考》、范麗敏著《清代北京戲曲演出研究》,或專門或部分地論述了清代宮廷戲曲的發展與演變。
除了這些著作,還有1993年出版的朱恒夫著《目連戲研究》[26]、1997年出版的劉禎著《中國民間目連文化》[27]在論述目連戲時,專門探討了《勸善金科》。這是就清宮大戲個案進行深入研究的著作。
在論文方面,有趙景深《談清宮大戲忠義璇圖》、龔和德《穿戴題綱的年代問題》、楊常德《清宮演劇制度的變革及其意義》、李玫《清代宮廷大戲三題》、申智英《韓國紀行文中的清宮演劇》等。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清代升平署戲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才剛剛起步。關于它的整理,除了比較著名的宮廷大戲被影印出版外,現在雖然也出版了珍本,但仍舊被保存在個別圖書館,不為一般讀者所易見。而由于它的數量又十分巨大,要全部大量出版非付出巨資不能實現,再加上它沒有所謂的“進步思想意義”,更無一點商業營利的價值,所以,要把它像其它文獻那樣出版出來供讀者閱讀和學者研究,不僅是現在,即使是將來,恐怕都很難做到。關于它的研究,從戲劇史和文學史不給一席之地到作為章節專門論述,從根本否定到基本肯定再到客觀的評述,這都是研究的進步。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不少學者已將目光停留在它身上,雖然還沒有研究性的專著,但以它為對象的史話一類的著作已經出現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欣喜的現象。畢竟與皇宮有關,雖然也遭受過冷落,但終究還會受到青睞的。看來,它比《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元刊雜劇三十種》、《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境遇好得多了。然而,它的數量巨大,又深藏不露,盡管有人關注,但全面研究的難度卻要大得多。
[1]吳梅.中國戲曲概論[M]∥吳梅全集.理論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鄭振鐸.鄭振鐸全集:第10-12卷[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
[3]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4]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5]盧前.明清戲曲史[M]∥盧前曲學四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
[6]周貽白.中國戲劇史略[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7]徐慕云.中國戲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
[9]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10]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11]周貽白.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2]吳國欽.中國戲曲史漫話[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13]張庚,郭漢城.中國戲曲通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
[14]湯草元,陶雄.中國戲曲曲藝詞典[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
[15]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Z].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
[16]周妙中.清代戲曲史[Z].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17]北京市藝術研所,上海市藝術研究所.中國京劇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18]馬積高,黃鈞.中國古代文學史[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
[19]張月中.中國古代戲劇辭典[Z].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
[20]許金榜.中國戲曲文學史[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
[21]李修生.古本戲曲劇目提要[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22]王森然.中國劇目大辭典[Z].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3]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4]丁汝芹.清代內廷演戲史話[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25]廖奔,劉彥君.中國戲曲發展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26]朱恒夫.目連戲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27]劉禎.中國民間目連文化[M].成都:巴蜀書社,1997.
I206.2
A
1008-178X(2012)08-0076-04
2012-03-31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5BZW032);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0XZW021);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0918);西北師范大學基金項目(NWNU-KJCXGC-SK0302-1)。
李占鵬(1965-),男,甘肅正寧人,西北師范大學文史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戲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