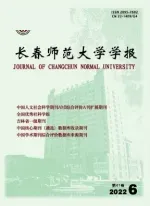論韋勒克批評史研究的地位與影響
宗 圓
(吉林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 130012)
論韋勒克批評史研究的地位與影響
宗 圓
(吉林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 130012)
雷納·韋勒克的八卷本《近代文學批評史》是他以畢生精力完成的一部鴻篇巨制,也是他對西方近代文學理論、批評理論的歷史性研究。本文主要從這部著作在韋勒克的學術生涯中占據的地位,以及韋勒克批評史研究對20世紀美國文學界所產生的影響方面,對其重要意義進行考察。
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批評史研究;地位;影響
雷納·韋勒克以他驚人的博學和過人的耐力,在文學研究領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他的著述涵蓋了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比較文學等諸多方面;他對文學理論的建構,對各種文學問題深入而細致的思考以及他在學術態度上的認真嚴謹至今都影響著廣大的文學研究者。而其以畢生精力獨自撰著的八卷本《近代文學批評史》,則以恢弘的氣度和淵博的學識堪稱他的扛鼎之作。近年來我國學界對韋勒克的關注度越來越多,但對其《近代文學批評史》一書和批評史研究的認識尚不充分,本文旨在從批評史研究在韋勒克學術生涯中的地位和其對20世紀美國學界的影響兩方面來闡述其重要意義。
一、《近代文學批評史》與韋勒克的批評史研究
雖然他和奧斯汀·沃倫合寫的《文學理論》 (TheoryofLiterature)一問世就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至今影響仍不減當年,但是韋勒克在《近代文學批評史》 (以下簡稱《批評史》)上所傾注的心血遠超前者。整個八卷本的完成花費了逾40年的時間,幾乎占據了韋勒克的大半生。該書還是他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是他文學思想的集中體現。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看待這部著作:首先,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看,它反映了文學理論、批評理論在歷史中所呈現的狀態,是一部關于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史書;其次,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批評的歷史又不可能是絕對客觀的和不帶有史家個人眼光的,因此韋勒克對這段歷史的研究,他的取舍、評價、闡述、概括,以及他的理論立場和價值觀念在歷史中的凸顯等問題是這部著作令人關注的另一層面;第三,作為一位優秀的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韋勒克這部著作又是他對其理論的一場實踐,他如何把理論付諸實施,如何堅守自己的陣地,也成為人們對該書的又一關注點。總的說來,這部著作的考察對象主要是西方18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的文學理論、批評理論的歷史,因此這部著作的撰寫實際上就是韋勒克對西方文學批評史所進行的研究。歷史的面貌、史家的個體視角,以及理論家的理論與實踐都統統集中于這部批評史研究成果之中。
韋勒克向來主張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融合統一,因為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這些領域原本就是互相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今天我們去研究韋勒克的文學思想,側重于不同的角度,或是研究他的文學理論,或是研究他的比較文學理論,或是研究他的批評理論,都是為了更有條理、更明晰地解讀他整體的文學思想以及他對諸多文學問題的看法。不同的研究角度只是手段,目的則是融會貫通。因此充分認識韋勒克的批評史研究的地位和影響對于我們考察韋勒克的整體文學思想意義重大。
二、韋勒克批評史研究的地位與影響
(一)韋勒克批評史研究在其學術生涯中的地位
無論是在早期的批評性文章中,還是在《批評史》一書中,韋勒克的批評實踐和他的批評史研究都是相輔相成的。他從來都是一位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識”[1]的批評家,他對于自己的批評標準、價值觀念具有理論上的認知,并能夠系統化、理論化地進行闡述和概括,同時以此為理想應用于他的批評實踐。這種能力或許和他作為批評史家的身份有很大的關系。在他的《批評史》中,韋勒克常常能夠辨析出各位批評對象的批評理論與批評實踐的矛盾之處,或發現他們在不同時期對不同問題的側重。因此在他本人的批評活動中,他不僅強調價值判斷的重要性,同時還主張維護史學家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作為批評家的韋勒克很早就開始了他的批評生涯。早在布拉格的那段時期,他就不僅從事實用批評,還從事每日述評的工作。他當時的專長是評價譯自英文的譯本,其中包括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康拉德的《勝利》、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他當時對流行小說產生了興趣,撰寫了大量書評,介紹以捷克文出版的英美文學作品。
韋勒克被譽為“批評家的批評家”[2],這是對他的批評工作的準確概括。他的批評文章除早期對文學作品所進行的評論、介紹之外,還有一大部分是對學術著作、各位批評家思想的分析和評價。他在其《批評史》中曾談到,對批評家們的思想觀點進行梳理,“對眾多書籍中所闡述的理論、學說和見解的表述、分析與判斷”[3]是批評史的任務所在。他向來以史家的眼光去公正地看待各位批評家們的理論觀念,同時又不放棄自己的價值準則,準確地進行評斷。他曾為《捷克現代語言學雜志》撰寫學術性的批評文章,同時對一些學術論文進行評論。[4]他在《文字和文學》雜志第一期上發表論文,評價了貝特森(F.W.Bateson)的《英國語言和英國詩歌》,其觀點又曾被應用于他的英文文章《弗·威·貝特森的文學理論》[5]中。他還曾經撰寫長篇文章評價劍橋學派的批評家理查茲、利維斯和威廉·燕卜蓀,在《藝術和批評雜志》上與語言學派和俄國形式主義學派展開論辯。這類批評文章為韋勒克寫作《近代文學批評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他在該書的寫作過程中,對這些已發表的論文進行了擴充、刪減、修改,進而完成了在一整部批評史中評論這些批評家的任務。這些論文中所體現的韋勒克的文學觀念和批評觀念與其《批評史》中所反映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韋勒克不僅終生都在從事他的這種批評實踐,并且從歷史的角度出發給予了梳理。
除了這些被收錄進他的《批評史》的專論各批評家的論文之外,韋勒克最為受人矚目的便是他那些針對各類文學問題的理論性文章。這些文章展示了他對理論問題的思考成果,細致闡釋了文學史、文學批評、比較文學方面的定義、概念、術語、研究方法、歷史分期等諸多問題。他的早期論文《文學史理論》中所體現出的對于文學自足的審美價值的肯定,對內容與形式二分法的反對,對文學作品價值問題的關注,以及以“透視主義”的方法看待文學等思想,表明他早在來美國之前就持有許多重要的批評見解。這些觀點在《文學理論》中得到了更為細致的表述。而收錄在《批評的概念》 (Concepts ofCriticism)和《鑒別》 (Discrimination: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中的那些論文,更是考察了各個批評概念、批評方法以及當代美國和西方在文學批評領域的主要趨勢和各種問題。但是《批評史》一書無疑是他文學理論和批評實踐的集大成者,他所有理論文章中的觀點都集中反映在了這部著作中,他的批評理想、歷史觀念以及他對文學的理解都通過這部百科全書式的《批評史》體現了出來。在這部書中,韋勒克對西方近代文學批評的歷史的描述和討論,既廣泛地涉及了哲學、美學、歷史、文化等范圍,同時又緊緊圍繞文學批評的主題做到深入而細致;既有對每個批評對象的分析、闡述、評價,又不失歷史的宏觀概括和勾畫。這部《批評史》既是一部關于文學批評的史書,也是批評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時還是研究文學批評這一學科本身的優秀教材,并且還提供了一個復雜而宏大的批評對象。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韋勒克在文學批評和批評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從根本上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文學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二)韋勒克批評史研究對學界的影響
首先,他要求明確文學批評的研究范圍,這也是任何一門學科確立的基礎。在《批評史》中,韋勒克不止一次地強調他的研究范圍聚焦于文學批評,即關于文學本身的問題的討論。他相信文學批評雖然和社會、政治、經濟、哲學等問題常常是密切相關的,但它總有一個獨立的發展軌跡,有其自身的特點,因此要將文學批評從各門學科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來,承認它的自身價值,肯定它的自足性。不僅文學批評是獨立于其它社會科學的,批評的歷史也同樣不同于其他學科史而具有自身特點,需要獨特的研究方法。韋勒克一直在同那些對文學批評持否定意見的批評家進行爭論,維護批評的地位和應有性質。
韋勒克不僅明確文學批評的研究范圍,同時還確立了文學批評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在許多文章中,他都一直在強調批評過程中價值判斷和闡釋的重要性。針對很多批評家忽視批評的評斷作用的情況,韋勒克堅持認為,那些在理論上否認價值取向的批評家們在其實踐中往往都是遵循著一定的價值標準的。即便是像威爾遜·奈特那樣宣稱回避所有價值判斷,稱“文學批評一向是我尤為厭惡的東西,二十五年來我一直提出別的東西取而代之”[6]的極端例子,韋勒克也指出,他的批評中那種在象征上的簡單取舍也是一個價值判斷行為。更不用說像艾略特這樣的大批評家,在排斥判斷的同時卻以其批評實踐中的品鑒魅力而取得成功的例子了。韋勒克還時刻提醒人們注意忽視價值判斷的相對主義對文學批評的危害,這會導致價值體系的紊亂——“如果每個文本都是歧義叢生,復義交錯,‘無從確定’,我們就走到了學術研究的盡頭,得出一個極其虛無主義的結論。”[7]經典作品和低俗小說沒有了差別,這不僅終結了文學批評,也毀滅了文學自身。然而另一個極端——絕對主義也是韋勒克想要極力避免的,在他自己的批評中,他從不輕下斷語,也對那些裁斷性的批評持有保留意見,充分肯定了細讀、闡釋在批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實際上他主張的是一種價值判斷與歷史的動態平衡,他相信在歷史的進程中,諸多問題不斷被理清,許多關鍵問題上的共識的內核不斷擴大。因此批評家既要承擔價值判斷的壓力,又要從歷史的角度去理解批評對象,盡可能作出公正合理的評斷。
除了在確立文學批評這一學科方面的貢獻之外,韋勒克的批評史研究還在許多問題上提供了理論基礎。其中一個例子便是他在反對實證主義方面的理論貢獻。在20世紀初美國和歐洲的文學研究領域已經有了一系列對于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反駁,但是韋勒克的突出成績在于,“當其他人還在從各自的視角去譴責實證主義或提倡美國文學研究革命時,韋勒克基于文學理論和歷史的視角,提出了全面而論述詳盡的文學研究基礎。”[1]他堅信每一學科都必須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文學研究也不例外,他提倡學者去思考文本自身的研究價值,而不應該在其他學科各自不同的價值體系之下被詮釋為這些學科的表征。在他的《批評史》中,他不僅多次談到這個問題,在這部著作的撰寫過程也一再體現著這一觀點。文學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僅靠描述相關的歷史事件、哲學理論、經濟狀況、社會階級甚至作家生平是無法闡述透徹的,唯有致力于研究適用于文學的研究方法、批評方法才能夠解析出文學問題的答案。在這一問題上他與法國比較文學學者們關于研究方法的爭論,不僅向世界宣布了他對實證主義的毫不妥協,也為美國比較文學學派奠定了了標志性的理論基礎。
[1]Sarah Lawall.René Wellek and Modern LiteraryCriticism[J].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40,No.1(Winter,1988).
[2]Thomas,Robert Mcg.,Jr.“Rene Wellek,92,a Professor ofComparative Literature,Dies.(Cultural Desk)(Obituary)”[J].The NewYork Times,(Nov16,1995):pNA.
[3]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四卷[M].楊自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547.
[4]Rene Wellek,Bibliography,Essays on Czech Literature,Hague:Mouton,1963:13-15.
[5]Rene Wellek.The LiteraryTheories ofF.W.Bateson.Essays in Criticism,1979,Vol.29:112-123.
[6]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五卷[M].楊自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207.
[7]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六卷[M].楊自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486.
I109
A
1008-178X(2012)08-0086-03
2012-03-16
吉林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421010031402)。
宗 圓(1980-),女,吉林長春人,吉林大學文學院講師,博士,從事西方文學批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