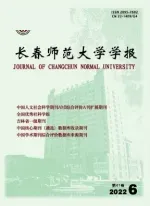伍爾夫小說《奧蘭多》中的哲理思考
牛曉麗
(山西大學(xué)商務(wù)學(xué)院,山西太原 030031)
伍爾夫小說《奧蘭多》中的哲理思考
牛曉麗
(山西大學(xué)商務(wù)學(xué)院,山西太原 030031)
弗吉尼亞·伍爾夫創(chuàng)作的奇幻小說《奧蘭多》是一部有趣的頗具夸張色彩的“假期書”,同時也是一部極富哲理的作品。《奧蘭多》在表面的荒誕之下,蘊(yùn)含作家對男女兩性關(guān)系的探討,對“真實(shí)”、“死亡”的思考,以及對個體“人”的身份追尋,將文學(xué)與哲學(xué)融為一體。
伍爾夫;奧蘭多;哲理思考
一、對“兩性”的思考
奧蘭多是貫穿全文的主人公,從伊麗莎白時代的青年貴族,到詹姆斯國王宮廷里的重臣,再到查理一世時代出使君斯坦丁堡的大使,一直到1928年伍爾夫?qū)懽鞯默F(xiàn)實(shí)社會。在這期間,他經(jīng)歷了男女兩性的性別轉(zhuǎn)換,從一個英俊少年變成了美貌少婦,最后成為創(chuàng)作出多部作品、出版過長篇詩歌的女作家。伍爾夫在敘述奧蘭多400多年的生活經(jīng)歷時,始終聚焦于性別身份的形成與男女兩性的相融過程。
奧蘭多變?yōu)榕灾螅鸪趸燠E于吉普賽部落,并未覺察此刻的女性身份對她有何影響。因?yàn)樵谀抢铮凹杖耍艘粌蓚€重要的特例外,與吉普塞男子別無二致。”①而當(dāng)她坐在駛往英國的“癡情女郎”號甲板上時,她才“大吃一驚,意識到自己所處地位的得失,而這一驚絕對出乎她的意料。”從此,她的性別意識也越來越凸顯出來,很快就感到作為女性要學(xué)會屈服,得尊重另一個性別的意見,甚至要給自己套上枷鎖:“因?yàn)榕瞬⒎翘焐槒摹⒇憹崳瑴喩砩l(fā)著香氣、衣著優(yōu)雅。她們只能通過最單調(diào)乏味的磨練,才能獲得這些魅力,而沒有魅力,她們就無法享受生活的樂趣。”她對男性強(qiáng)權(quán)社會的認(rèn)識隨著女性體驗(yàn)的增多而日益深入。
隨后,頭腦中的兩性氣質(zhì)輪番交鋒,男女兩性的意識在她身上共同發(fā)揮作用。“正因?yàn)樗砩系倪@種男女兩性的混合,一時為男,一時為女,她的行為舉止才往往發(fā)生意想不到的轉(zhuǎn)變。”時而扮成貴族公子哥的模樣,時而又隨興穿上了石榴裙。“她的性別變化之頻繁,是那些只穿一類服裝的人無法想象的。毫無疑問,她用這種辦法獲得了雙重收獲。”這種享受與體驗(yàn)讓她進(jìn)一步明白兩性的同與異。她“生活的樂趣增加了,生活的閱歷擴(kuò)大了。”雖然,最終奧蘭多是以女性的身份登上了藝術(shù)的巔峰,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某一性別的貶低或提高,而恰恰是兩性合作達(dá)到和諧狀態(tài)的一種體現(xiàn)。這兩種性別身份,沒有孰優(yōu)孰劣,而是對立統(tǒng)一于一個人的身上,達(dá)到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狀態(tài)。
伍爾夫通過描繪奧蘭多雙性同體的生活,向人們展示了一種理想的狀態(tài),揭示了兩性互取其長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至此,伍爾夫打破了傳統(tǒng)價(jià)值觀中男性中心論的二元對立,抹平了男性與女性間的鴻溝,消除了建立在它們之上的價(jià)值觀念。
二、對“死亡”的思考
作者在作品中不僅反映了自己在兩性方面的觀點(diǎn),同時也把自己對生活、死亡、時間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融入其中。他始終在探索生存的本質(zhì),最終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完結(jié)困擾她一生的問題。作品作為作家孕育出的生命,它身上或多或少鐫刻著作家的影子。奧蘭多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都發(fā)出了對“死亡”的感慨。
青年時期的奧蘭多認(rèn)為“死是萬物之歸宿”,對他來說,通過對“死亡”的思考才能尋找到人生的真實(shí)。伍爾夫安排奧蘭多在孤獨(dú)中冥想“死亡”來探尋生命的本質(zhì)。“她此時陷入孤寂的心境,……只渴望去獨(dú)自迎接死亡,因?yàn)樗劳雒繒r每刻都在發(fā)生……”之后,奧蘭多在自我思索中,斷斷續(xù)續(xù)地完成了他的詩作《大橡樹》,直至大作完成,作為他對人生思考的回應(yīng)。
真正的作家從事創(chuàng)作,不求名利,只為探究人生的終極意義。對于伍爾夫來說,寫作是她唯一與疾病和死亡抗?fàn)幍姆绞剑@也未能阻擋她走向死亡。她對“死亡”的思索一直到生命的盡頭,最終用自己的生命作了最后的詮釋:“哦,我將一頭砸向你——不可征服、不可撼動的死亡!”《奧蘭多》一文中不斷出現(xiàn)主人公對“死亡”的感受與思索,正是作家借主人公之口來表述對這一問題的哲理思考。可以說,伍爾夫的生活和藝術(shù)是交融共處的,她的藝術(shù)即是她的生活,而她的一生也注定過一種精神的、藝術(shù)的生活。
三、對“自我身份”的思考
《奧蘭多》一文探究了人類個性的秘密,提出了關(guān)于身份和自我確定的問題。一個人的身份是由什么構(gòu)成的?它是固定的、永恒的,還是流動的、多變的?一個人的身份是取決于其性別,還是地點(diǎn)或時間?伍爾夫在《奧蘭多》中不斷進(jìn)行著思索。主人公奧蘭多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的變遷而不斷地調(diào)節(jié)自我、變換身份,以期達(dá)到“真我”的實(shí)現(xiàn)。
在文中,伍爾夫用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手法,追尋和探索著“真實(shí)”與“自我”。
“縈回夢繞!我還是孩童時即如此。野鵝飛過。野鵝從窗前飛過,飛向大海。我跳起來,伸出胳膊想抓住它。但野鵝飛得太快。我看到過它,在這里——那里——那里——英格蘭、波斯、意大利。它總是飛得很快,飛向大海,而我,總在它身后撒出網(wǎng)一般的文字,它們皺縮成一團(tuán),就像收回的網(wǎng),我在碼頭上看到過的,網(wǎng)中只有水草;有時,網(wǎng)底有一英寸的銀子——六個字。但從來沒有捕到珊瑚叢中的那條大魚。”
“珊瑚叢中的那條大魚”是伍爾夫一生所追求的。她不停地探索、實(shí)踐,卻始終無法捕捉到她生命中令她魂?duì)繅衾@的“那條大魚”。
她筆下的奧蘭多如她自己一樣,充滿了對閱讀和寫作的愛。從小迷戀大自然和文學(xué)的奧蘭多把內(nèi)心的情感付諸筆墨。成為女性后的她更是“對筆墨產(chǎn)生了前所未有的渴望”。奧蘭多執(zhí)著于兒時的愛好,追尋著“那條大魚”,一路前行,不停地變換著自我,尋找那個“唯一的自我,真實(shí)的自我”。“一個人完全可能有上千個自我”,而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我呢?是那個走在山坡上,喜歡思考和文字的少年?或是愛上薩莎的青年貴族?抑或是混跡于吉普賽部落中的女子?還是穿梭于社交界的優(yōu)雅貴婦?所有這些自我都不相同,而哪個才是她想要的?她在苦苦思索。最終當(dāng)她全身沉靜下來,成為所謂唯一的自我、真實(shí)的自我時,“就好似添了一個襯托物,于是有了外表的渾圓和結(jié)實(shí),于是由淺變深,由遠(yuǎn)變近,一切都似井中水,只能在深井四壁之內(nèi)回旋。”這樣的追尋結(jié)果讓水一般的奧蘭多有了外型,從而有了意義。也正由于此,奧蘭多得以生存于這個世間,品嘗成功的喜悅。伍爾夫在散文《街頭漫步:倫敦冒險(xiǎn)》里也提出這樣的疑問:“我在這里嗎?還是在那里?或者真正的我既不是此也不是彼,既不在這里,也不在那里,而是形式各異、捉摸不定的。使得只有當(dāng)我們信馬由韁讓自我的愿望任意馳騁時,我們才是自己嗎?”身份是不確定的,但它離不開社會環(huán)境的束縛,要生存人并不能完全陷入無意識、不受控制的狀態(tài),她接著說:“環(huán)境強(qiáng)求一致;為方便起見,人必須是個整體”。沉淀下來的奧蘭多成熟而富有韻味,這也許是伍爾夫理想狀態(tài)的完美展示。
四、結(jié)語
在作品《奧蘭多》中,伍爾夫用其獨(dú)特的手法完成了對內(nèi)在真實(shí)和死亡的探索,以及對兩性的思索和身份的追尋,在表面的荒誕之下蘊(yùn)含了對人生問題的哲理思考,在瓦解傳統(tǒng)寫作模式的基礎(chǔ)上,重新定義藝術(shù)的真實(shí)表述,在趣味與哲理的融合中開辟了新的空間,讓作品煥發(fā)出奇光異彩。
[注 釋]
①本文所引小說原文均出自弗吉尼亞·伍爾夫著《奧蘭多》 (林燕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不再特別注明。
[1]甄艷華.伍爾夫的小說理念[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2][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日記選[M].戴紅珍,宋炳輝,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
[3]易曉明.優(yōu)美與瘋癲——弗吉尼亞·伍爾夫傳[M].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2.
[4]瞿世鏡.伍爾夫研究[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5]呂洪靈.《奧蘭多》中的時代精神及雙性同體思想[J].外國文學(xué)研究,2002(1).
I561.074
A
1008-178X(2012)08-0097-02
2012-05-29
牛曉麗(1977-),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學(xué)商務(wù)學(xué)院助教,碩士,從事西方文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