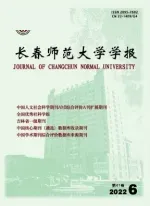解析沈從文與梭羅對自然與生命的價值取向
孫英馨
(1.吉林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 130012;2.長春師范學院外語學院,吉林長春 130032)
解析沈從文與梭羅對自然與生命的價值取向
孫英馨1,2
(1.吉林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 130012;2.長春師范學院外語學院,吉林長春 130032)
沈從文與梭羅這兩位同樣具有浪漫主義氣質的東西方作家在其文本世界里分享著對自然與生命的熱愛。然而,二者對自然與生命的價值取向,對欲望的不同理解又凸顯出民族文化的異質特征。沈從文尚美、敬神、重人欲;梭羅崇真、倡簡、輕人欲。前者受縱情恣肆、厚巫、好祀充滿浪漫主義情趣的楚文化的浸潤,后者受簡樸、內省、克制頗有實用主義意味的清教思想的熏染。因此,二者的文學文本體現出看似相同其實迥異的價值內容。
沈從文;梭羅;尚美;倡簡;文化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在文藝與政治以及權力話語百般糾結的歷史語境下,在工業文明的發展使人性受到強烈擠壓以致扭曲異化的時代氛圍中,沈從文凝眸于人類遠景,意欲重新塑造國人的品格,這不由得使人想起那個生活在十九世紀而今成為美國精神偶像的作家和哲人H.D.梭羅。這兩位同樣具有浪漫主義氣質的東西方作家在其文本世界里分享著對自然與生命的熱愛。然而,二者對自然與生命的價值取向,對欲望的不同理解又凸顯出民族文化的異質特征。
一、在自然中感悟神性之美的沈從文
凌宇曾這樣評價沈從文:“在整體傾向上,沈從文的創作帶著鮮明的浪漫主義色彩。對美——‘生命’自由的熾熱追求與對人間遠景凝眸的幻想情緒,不僅籠罩在他的以鄉土為題材創作的主體畫幅上,甚至涵蓋著他的全部創作。”[1]謳歌“生命”和“美”是沈從文創作的主旋律,尚美是他的文本世界最重要的特征。在他的筆下無論是自然還是人物都投射出美的韻致。美是什么?沈從文在《愛與美》中回答道:“一個人過于愛有生一切時,必因為在一切有生中發現了‘美’,亦即發現了‘神’。”[2]由此看來,沈從文的“神”與“美”是近乎同義的:神,使人景仰、敬畏;美,亦令人臣服、仰視。美是事物呈現出的現象特征,而神則是作家對美的主體精神的抽象。對美的高度敏感和深切體悟使沈從文文本中的自然披上一層神性的色彩,附著著夢幻的氤氳,滲透出詩與畫的意境。他描繪的湘西山巒積翠疊藍,碧溪澄明見底;煙霞、游魚、桃花、彩褂仿佛隨手可拾,霧靄、竹簧、野鶯、橘茶亦漫山遍野。湘西變得既如室外桃園般惹人驚異,又似彼岸圣境令人神往。自然界里光色與形線的變換經作家之手無不予人以無限美感。由此可見,迷醉于自然的沈從文捕捉到的不是大自然的使用價值,而是它的審美價值。美也不僅僅止步于形象呈現。大自然將美傾注于人眼目的同時,也同化著人的靈魂。所以,離開邊城的青山秀水也不會有翠翠純凈靈動的性情。
“美”是自然界帶給人類的感官享受,還是生命使人眷戀的重要因素。沈從文相信生命因勃勃生機而美麗。自然世界中的一草一芥、一蟲一豸都能讓他感受到生命那靜默卻不容置疑的神圣律動:“對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單獨默會它們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關系時,也無一不感覺到生命的莊嚴。一種由生物的美與愛有所啟示,在沉靜中生長的宗教情緒,無可歸納,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對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3]。作家由對自然界瞬間看似靜態的物的感知,體察出其動態下生命的始終。在草木的枯榮之間,他品味著生命的不屈精神。沈從文說:“生命之最高意義,即此種‘神在生命中’的認識。”[4]可見,在沈從文的世界中,生命因其不屈不撓而神圣,因神圣而美麗。自然也罷,生命也罷,離開了美與神,一切都將褪去光彩、失去生機。在此理念的引領下,“美”“神”“生命”“自然”這四個詞在沈從文的文本中被賦予近乎相同的內涵。“美”是作家衡量世間萬物的一把尺,凡合意的,他都要好好收藏。所以,在湘西世界——他愿意用夢想重構的故鄉,哪怕最卑微的生命也會綻放出美的光芒。
沈從文愛生命,重人欲,他標榜自己無從領會道德倫理,其實意在言明天倫、人欲的合理性。他并不認為性是低級而不潔的,因此他的文本中那些充滿自然欲望的男男女女俯伏皆是。沈從文認為性愛如若發乎真心,又不損及他人就不應當受到責備。所以讀者會看到野地里受春風撩撥一時興起的夫婦,吊腳樓里干柴烈火的水手和妓女、山村小鎮里平淡中卻也纏綿著的阿黑和五明以及《月下小景》中一對癡心殉情的戀人等等。作家總是帶著一顆人性的心用溫暖的目光觀察眾生世相,以浪漫的情懷妝點常常是悲劇的人生。于是,人欲便成為自然與天理中最合法的存在。
二、在自然中體會真實與簡單的梭羅
如果說尚美、敬神、重人欲是沈從文面對自然與生命的價值取向,那么崇真、倡簡、輕人欲則是梭羅熱愛自然、強調精神修煉的意識出發點。
梭羅崇真,厭惡欺騙與詭詐,他認為在簡單的自然中才能參悟生活的本質。他主張遠離物質社會的“非人”生活,推崇自然之美,對自然懷著宗教般的感情。在他看來,自然界是精神的現象世界,是超靈顯現的表征,是造物主的意志最直接的體現。大自然生機勃勃,真實而確切,具有滌蕩和提升人類靈魂的功能。梭羅在《瓦爾登湖》中寫道:“我到林中去,因為我希望謹慎地生活,只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看看我是否學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東西,免得到了臨死的時候,才發現我根本就沒有生活過。”[4]在梭羅看來,“自然,在永恒中是有著真理和崇高的。”[4]他于1845年7月4日獨自一人搬入愛默生在瓦爾登湖附近購置的林地。沒有任何現代器械,他只以最簡單的工具在森林中建起一座簡陋的房子。風從木板的縫隙間穿過,露水滲進房屋。這樣的生活環境,仿佛退回到千百年前,人類的始祖沒有如此多的物質欲望的年代。梭羅生活在其中,但他并不以為辛苦。他享受著沐浴在大自然中的美好感覺:“這是一所空氣好的、不涂灰泥的房屋,適宜于旅行的神仙在途中居住,那里還適宜于仙女走動,曳裙而過。吹過我的屋脊的風,正如那掃蕩山脊而過的風,唱出斷斷續續的調子來,也許是天上人間的音樂片段。晨風永遠在吹,創世紀的詩篇至今還沒有中斷”[4]。梭羅深居山水草木之間,早出晚歸,記錄著四季寒暑中動植物的變化,熟知走過的每一寸土地。愛默生曾因此批評梭羅游手好閑,浪費了自己的天賦,梭羅卻自認為在與自然的貼身接觸中感受到生命的真實,體會到存在的終極意義。梭羅熱愛的正是這份直接面對天地、生命與自我的真實。
梭羅倡簡,他堅信簡樸的生活方可使人獲得靈魂的提升。他說“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窮人更加簡單和樸素。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古哲學家都是一個類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窮沒有,而內心世界再富不過。”[4]梭羅追求的簡樸非常極致。常人為衣食住行而奔波,可是在他看來衣服好比人體最表面的角質,不必很多,更不必常新,甚至有漏洞或補丁都沒有關系,只要夠暖,可以蔽體,足矣。過分追求只能徒生煩惱。至于食物,梭羅的觀點是“簡單化,簡單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頓也就夠了,不要百道菜,五道夠多了。”[4]梭羅在瓦爾登湖的生活見證了他倡簡的主張。他在大自然中看到的是最經濟而簡單的生命法則,他認為這才是造物主要傳達給世人的生活真諦;可是現代人卻寧可將自己包裹在奢侈品中,結果是“倒不及野蠻人有著一千種安逸”。這是真正的本末倒置。梭羅呼吁“我們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過一天吧”![4]
梭羅倡簡勝過愛美。假使讓梭羅在美與簡中做出選擇,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梭羅說“世人是在向著所謂富有而優雅的生活跳躍”,然而“我一點也不欣賞那些點綴生活的美術品。”[4]為了簡單、省時、省力,梭羅以為“可以把我們房屋里和我們生活有聯系的部分搞得美一點……但千萬不能搞得過分的美。”[4]梭羅的物質生活可以簡化到無可再簡,但是,他因而擁有了大量省察生命、體驗美好的時光,他的精神世界無比豐富。
與沈從文重人欲不同,梭羅不齒飲食男女之事。他說:“一切的淫欲雖然有許多形態,卻只是一個東西;純潔的一切也只是一個東西。一個人大吃大喝,男女同居,或淫蕩地睡覺,只是一回事……天性難于克制,但必須克制。”[4]他還自勉道:“放縱了生殖的精力將使我們荒淫而不潔;克制了它則使我們精力洋溢而得到鼓舞。貞潔是人的花朵;創造力、英雄主義、神圣等等只不過是它的各種果實……自知身體之內的獸性在一天天地消失,而神性一天天地生長的人是有福的,當人和劣等的獸性結合時,便只有羞辱。”[4]
梭羅崇真、倡簡、輕人欲的思想受東西方文化的共同影響。《瓦爾登湖》中頻繁地引用儒家道家的經典言論證明中國哲學在梭羅的認知心理上找到了合適的生長土壤。但是,倡簡的孔孟哲學之所以能在梭羅的精神世界里生長,是因為他所信奉的清教主義早已為此提供了充分的養料。換言之,孔孟哲學的倡簡思想與清教主義有恰當的契合點。盛行于16世紀至19世紀中期美國的清教主義主張勤勞、簡樸、克制與虔誠,提倡內省與禁欲。它重視人德性的修養,希望信徒通過此生之辛苦勞作取得成就以彰顯上帝的榮耀。梭羅苦行僧般的自我克制表明清教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地盤踞在他的意識之中。愛默生在梭羅的葬禮演講中也證實了梭羅是一位虔誠的宗教信徒,雖然梭羅對清教所宣揚的現世成就有不同的理解。
沈從文自幼生長其中的文化環境與克己觀念完全無關。楚文化縱情恣肆、厚巫、好祀。漢代王逸《楚辭章句》說:“昔楚國南郢之邑,其俗信巫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舞以樂諸神”。[5]楚地集神、巫、歌、舞于一體的民俗,造就了浪漫主義民風,更養成了楚人尚美、愛幻想的性情。他們尊重人欲,青年男女以歌聲尋找愛人的自由戀愛方式是湘西的古老傳統。愛就愛得熾烈,恨也恨得決絕。它與清教主義的精神內核是完全不同的。沈從文曾感嘆:“我正感覺楚人血液給我一種命定的悲劇性”,[4]可見其審美意識是非常自覺的。楚文化泛神、敬神,在一切人事風物中體驗神性的思想在作家內心世界里已如磐石,長期影響著他的生活和他的文本創作。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地理決定論雖過于絕對,但是民族文化對生長于其間的個體產生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沈從文與梭羅雖然同樣選擇了將目光投向自然,讓自然啟迪對生命的認知,但是他們的視角和價值觀念迥然不同。于是,文化與個性的復雜交合生成的不同結果在他們二者的文本中便顯現出來。
[1]凌宇.從苗漢文化和中西文化撞擊看沈從文[J].文藝研究,1986(2):64-72.
[2]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 11 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376,377,291.
[3]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0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288.
[4][美]梭羅.瓦爾登湖[M].徐遲,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79,84,74,11,80,84,31,33,195,194.
[5]孟修祥.荊楚文化特質平議[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2011(2):131-135.
Study on Shen Congwen’s and Thoreau’s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 of Nature and Life
SUN Ying-xin1,2
(1.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2.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Changchun Norma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32,China)
Shen Congwen and H.D.Thoreau are two romanticists.One is a modern Chinese writer,the other is an American poet living in the 19th century.They shared the love of the nature and life.However,they have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 an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life and sex.Shen adores beauty and deity,taking sex as human nature to respect it while Thoreau pursues truth,simplicity and self-restraint.Shen’s view is influenced by romantic Chu Culture which shows great infatuation to witchcraft and ancestor cult.Thoreau’s ideas are much impacted by utilitarian Puritanism which stresses on simplicity,introspection and asceticism.
Shen Congwen;Thoreau;beauty;simplicity;culture
I106
A
1008-178X(2012)08-0083-03
2012-03-14
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12B284);吉林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GH11277)。
孫英馨(1969-),女,吉林長春人,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長春師范學院外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從事比較文學及英語教學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