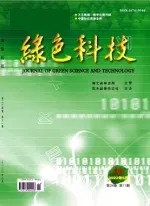多環芳烴污染修復現狀研究
崔海明,王 一,王曉濤,李成合
(河北鋼鐵集團礦業有限公司石人溝鐵礦,河北 遵化 064200)
1 引言
多環芳烴化合物(PAHs)是指含有兩個以上苯環的碳氫化合物,它廣泛存在于自然界,多環芳烴由于對人類健康有致癌、致畸、致突變的作用和較強的生物積累性以及可能是二惡英的前驅物而引起人們的重視。目前環境污染研究中的PAHs一般是指芳香稠環型[1],其中16種多環芳烴化合物已被美國環保局列入優先控制的污染物黑名單。分別是苊烯、苊、蒽、苯并[a]蒽、苯并[b]熒蒽、苯并[k]熒蒽、苯并[a]芘、苯并[g,h,i]菲、苗、二苯并[a,h]蒽、熒蒽、芴、茚并[1,2,3 一 ed]芘、萘、菲和芘。
PAHs大都是無色或淡黃色的結晶,個別顏色較深,具有蒸汽壓低,疏水性強,辛醇-水分配系數高等特點。其溶液具有一定的熒光性,化學性質穩定,不易水解。
多環芳烴主要來源于人類活動和能源利用過程。石油、煤等的燃燒、石油及石油化工產品生產、海上石油開發及石油運輸中的溢漏等過程。此外,森林火災、火山活動、植物和生物的內源性合成等自然過程亦構成了環境中PAHs。
2 多環芳烴概述
2.1 多環芳烴的種類
多環芳烴可分為芳香稠環型及芳香非稠環型[2]。芳香稠環型是指分子中相鄰的苯環至少有兩個共用的碳原子的碳氫化合物,如萘、蒽、菲、芘等;芳香非稠環型是指分子中相鄰的苯環之間只有一個碳原子相連的化合物,如聯苯、三聯苯等。結構如圖1所示。
2.2 多環芳烴的理化性
PAHs大都是無色或淡黃色的結晶,個別顏色較深,具有蒸汽壓低,疏水性強,辛醇-水分配系數高等特點。其溶液具有一定的熒光性、化學性質穩定、不易水解。另外PAHs很容易吸收太陽光中可見(400~760 nm)和紫外(290~400 nm)區的光,對紫外輻射引起的光化學反應尤為敏感。PAHs最突出的特性是致癌、致畸及致突變性,并且致癌性隨著苯環數的增加而增加[3]。

圖1 幾種多環芳烴的結構
多環芳烴(PAHs)作為純化學物質,主要是一些無色、白色或者淺黃綠色的,并有微弱芳香味的固體物質,五環以上的多環芳烴大都是無色或淡黃色的結晶,個別具有深色,熔點及沸點較高,所以蒸氣壓低,大部分的PAHs排入大氣后,吸附于灰塵顆粒,其中一些能夠從空氣很容易揮發進入土壤和水體的表面,大氣中的PAHs比較容易與太陽光和其它一些化學藥品發生反應而發生降解[4]。大部分PAHs不溶于水,一般都吸附在水體中的一些固體顆粒或者沉降到河道和湖泊的底部。土壤中的PAHs能夠很緊密地粘附與顆粒物上,其中一些還能夠通過遷徙而污染地下水,水體和土壤中PAHs易被微生物降解。雖然多環芳烴大多不溶于水,但是辛醇-水分配系數比較高,易溶于苯類芳香性溶劑中,多環芳烴大多具有大的共軛體系,因此其溶液具有一定熒光[5]。
2.3 多環芳烴的來源
除少量天然源外,環境中多環芳烴的主要來源是人為源。人為源包括化學工業污染源、交通運輸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其他人為源。
在焦化煤氣、有機化工、石油工業、煉鋼煉鐵等工業所排放的廢棄物中有相當多的多環芳烴,其中焦化廠是排放多環芳烴最嚴重的一類工廠。監測數據表明,作為多環芳烴污染指數的苯并[a]芘(英文縮寫為BaP)在焦化煤氣工業所排放的廢水中含量可高達25.4 ~ 46.0μg/L[2],遠高于 0.03μg/L 的國家排放標準。
飛機、汽車等機動車輛所排放的廢氣中也含有相當數量的多環芳烴,每100輛客運車每年能排放2-10t的BaP[6]。在煤爐排放的廢氣中,致癌性 PAHs濃度可達1000μg/m3。家庭爐灶每年所產生的BaP含量可達599μg/m3,超過國家衛生標準近百倍[7]。
2.4 多環芳烴的危害
PAHs的危害在于這些物質在環境中雖是微量的,但分布很廣且往往難于降解,并具有生物積累性和致癌、致畸、致突變等慢性作用,有的通過遷移、轉化、富集,濃度水平可提高數倍甚至上百倍。在人類己發現的500多種致癌物質中PAHs占了200余種[8]。另外 PAHs被關注的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PAHs物質以前驅物合成二惡英或者被飛灰吸附后在低溫區可作為初始反應物發生“從頭合成”的反應,形成劇毒二惡英物質,因此這些物質的生成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是一種潛在的威脅[9]。
無論家里、室外還是辦公室人們都暴露在這些PAHs物質中。人體可以通過不同途徑接觸PAHs,包括空氣、地表水、粉塵、食品等,其中食品是主要來源,占了總量的95%以上[4],因此保護食品供應體系的安全就顯得至關重要。
多環芳烴的真正危險在于它們暴露于太陽光中紫外光輻射時的光致毒效應。科學家將PAHs的光致毒效應定義為紫外光的照射對多環芳烴毒性所具有的顯著影響。有實驗表明[7],同時暴露于多環芳烴和紫外光照射下會加速具有損傷細胞組成能力的自由基形成,破壞細胞膜損傷DNA從而引起人體細胞遺傳信息發生突變。PAHs很容易吸收太陽光中可見(400~760nm)和紫外(290~400nm)區的光,對紫外輻射引起的光化學反應尤為敏感。
3 PAHs的生物修復技術研究
PAHs由于水溶性差,辛醇-水分配系數高,常被吸附于土壤顆粒上。因此,該類化合物易于從水中分配到生物體內及沉積層中,土壤就成為PAHs的主要載體。土壤作為一種重要的環境介質,承擔著90%以上的PAHs環境負荷[10]。當進入到環境中的PAHs超過它們的降解能力時,PAHs產生顯著的積累,當存在持續的污染源時,PAHs就會在土壤、植物和水體中積聚。在生物中富集的多環芳烴可以通過食物鏈傳遞,進而威脅到人類的健康。
土壤是非常復雜的多相體系,污染物進入土壤后,通過稀釋、擴散和遷移等作用降低污染物的濃度;通過酸堿反應或氧化還原反應等改變污染物的形態和毒性,或污染物在膠體表面發生吸附或凝聚而被固持,抑或被生物或微生物降解、吸收與轉化。因而土壤對外來污染物有一定的接納和緩沖能力,而土壤污染往往不易被直觀發現[11],因而也容易被人們忽視。
目前國內研究較多的是土壤中有機污染物及重金屬的遷移、轉化及對農作物的影響方面,僅有很少量的文獻涉及了交通干道兩側土壤的有機污染和相關研究[12],如馬玲玲在對北京城近郊土壤中有機污染研究中,對北京高速公路旁土壤的烴類污染的論述。
在國外,土壤污染處理治理技術的研究和應用是荷蘭、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近十年來在環境保護領域開展的新研究方向,德國已通過立法對污染土壤的排放和被污染土壤的使用了嚴格的標準,同時,高校和研究機構在物理、化學、生物治理技術等方面開展了多年的科研攻關項目[2,13]。1979 年美國環保局(EPA)公布了129種優先監測污染物,其中有16種是多環芳烴。2001年5月23日世界各國簽署了《斯德哥爾摩公約》,12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將在世界各地被法律禁止或限制使用。土壤作為一種重要的環境介質,承擔著90%以上的PAHs環境負荷[14]。
為減少PAHs的排放,應盡可能使各種燃料充分燃燒,加強石油產品的監測和管理。對已造成的污染,可以采用生物或化學的處理技術處理,目前主要有吸附法、光解法和生物修復技術3種處理措施[15]。
在PAHs污染土壤的修復方法中,生物處理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因為生物處理沒有副產品,可以在沒有副作用的情況下消除污染物,因此被認為是目前最具潛力的修復方法之一。生物修復根據生物修復所利用的生物材料可分為植物修復和微生物修復。微生物修復技術是在人為優化的條件下,利用自然環境中的微生物或人為投加的特效微生物的生命代謝活動,來分解土壤中的污染物,以修復受污染的環境。
植物修復是一種利用植物修復受有毒金屬、有機物和放射性物質污染的土壤、沉積物、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綠色技術。用物理或化學方法比較起來,植物修復是一種有效的、非強制性、自然的和便宜的修復土壤的方法[15]。植物修復實際上是利用由土壤-植物-微生物組成的復合體系來共同降解污染物的,它有以太陽能為動力的“水泵”、“植物反應器”及與之相連的“微生物轉化器”和“土壤過濾器”,因而該系統是一個強大的“活凈化器”。丁克強等[17]研究了黑麥草對土壤中菲的修復,在60d的溫室盆栽試驗中,觀察到黑麥草加快了土壤中可提取態菲濃度的下降,在5、50、500mg/kg菲處理濃度下黑麥草生長的土壤中菲的降解率分別達到93.1% 、95.6%、94.7% 。黑麥草增強土壤中多酚氧化酶的活性而提高植物對菲的降解率,土壤自身具有修復PAHs中菲的自然本能,種植黑麥草具有強化土壤修復菲污染的作用。增加黑麥草產量,增強土壤多酚氧化酶活性,可能提高黑麥草植物修復菲污染土壤的能力。Pradhan等[16]用植物修復為首要的修復受PAHs污染土壤的技術,用3種植物苜蓿、柳枝稷、藍莖草經6個月的處理后,PAH總濃度減少了57%。
由于PAHs的疏水性、穩定性,嚴重限制了其生物可利用程度和生物修復速度,因此,通過采取強化措施提高其生物修復效率就成為生物修復PAHs污染土壤的關鍵。通過采取一些強化措施,如使用表面活性劑,添加營養物質和提供共代謝底物等,可顯著提高PAHs降解速度和程度,為生物修復技術的成功應用提供前提國內外一些有學者已經利用溶劑,例如正己烷、二氯甲烷、丙酮、乙醇、正丁醇、雙氧水等洗脫土壤中PAHs,降低土壤中PAHs的濃度和毒性,從而為生物降解提供更加適宜的環境[17]。
4 結語
近年來,國內外對土壤PAHs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大多數集中于表層土壤PAHs的研究對深層土壤污染的研究較少。
隨著煤、石油在工業生產,交通運輸以及生活中被廣泛應用,多環芳烴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有機污染物。土壤對外來污染物有一定的接納和緩沖能力土壤污染往往不易被直觀發現,因此土壤曾被認為具有無限抵抗人類活動干擾的能力。其實,土壤也是很脆弱又容易被人類活動所損害的環境要素。一些地區土壤中的多環芳烴污染已經相當嚴重,由于其持久性和生物富集性,致癌致畸致突變效應,已經嚴重威脅到人類的健康。所以加強多環芳烴的監測,開展污染土地的修復勢在必行。
[1]戴樹桂.環境化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楊發忠,顏 陽,張澤志,等.多環芳烴研究進展[J].云南化工,2005,32(2):44 ~48.
[3]Jacob K W.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of environmental and importance[J].Fresenius J Anal Chem,2000(323):1 ~10.
[4]程元愷.致癌性多環芳烴[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0.
[5]趙起越,袁倬斌.多環芳烴的分析發展動向[J].分析試驗,2001(11):25.
[6]張志紅,楊文敏.汽油車排出顆粒物的化學組分分析[J].中國公共衛生,2001,17(7):623 ~624.
[7]袁彥華,孫連軍,郭秀蘭.多環芳烴化合物毒理學研究[J].中國公共衛生,1999,15(8),675 ~676.
[8]占新華,周立祥.多環芳烴(PAHs)在土壤-植物系統中的環境行為[J].生態環境,2003,12(4):487~492.
[9]吉云秀,邵秘華.多環芳烴的污染及其生物修復[J].交通環保,2003,24(5):33 ~36.
[10]Wild Simon R,Jones K C.Polynuclear aromatic hydrocarbom in the United Kingdom environment:a preliminary source inventory and budget[J].Environ PoUut,1995(88):91 ~ 108.
[11]岡吉 W D.土壤和水中的農藥[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
[12]Jones K C.Increase in the polynuclear aromatic hydrocarbons conlent of an agriculture soil the past centuty Environ[J].Envim Sci Tech,1989(23):95 ~100.
[13]沈學優,劉勇建.空氣中多環芳烴的研究進展[J].環境污染與防治,1999,21(6):32 ~46.
[14]李家珍.染料、染色工業廢水處理[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1997.
[15]丁克強.駱永明,劉世亮,等.黑麥草對菲污染土壤修復的初步研究[J].土壤,2002(4):233~236.
[16]Pradhan S P,Conrad J R,Paterek JR,et a1.Potential of phytoremediationor for treatment of PAHs in soil at MGP sites[J].J Soil Contam,1998(7):467 ~480.
[17]陳 靜,胡俊棟,王學軍.混合溶劑解吸土壤中多環芳烴的研究[J].中國環境檢測,2004,20(6):16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