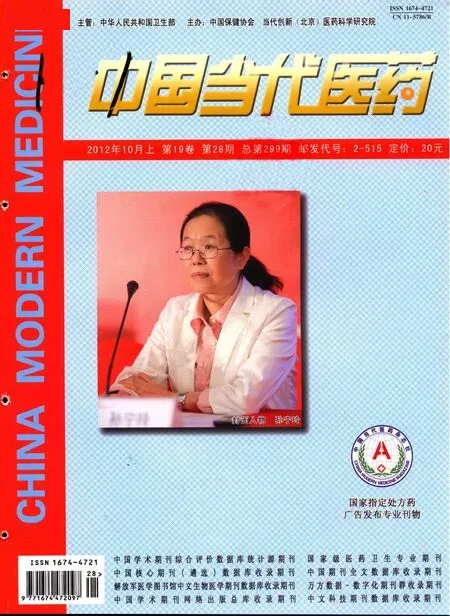經傷椎椎弓根植骨聯合傷椎置釘治療胸腰椎爆裂骨折
任守松 魏見偉 楊希重 陳占文 喬真理
山東省即墨市人民醫院脊柱外科,山東即墨 266200
胸腰段單節段爆裂性骨折在臨床上比較常見,后路短節段椎弓根螺釘內固定融合是治療胸腰椎爆裂骨折較為理想的手術方法之一。長節段的椎弓根內固定術由于較大范圍限制了胸腰段的活動,術后出現較高的內固定失敗率。隨著脊柱內固定失敗的出現,人們開始重視對傷椎的治療,如在傷椎中植骨[1]、在傷椎附加椎弓根螺釘[2]等,以提高手術療效。本院2008年3月~2010年1月選擇后路經傷椎椎體內植骨加傷椎置釘治療胸腰段椎體爆裂性骨折59例,療效滿意。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59例,男38例,女21例,年齡19~65歲,平均37歲。致傷原因:車禍傷41例,高空墜落傷7例,跌傷5例,其他原因 6例。損傷節段:T11 9例,T12 27例,L1 18例,L2 5例。骨折類型,按Denis分類法:A型3例,B型37例,C型9例,D型6例,E型4例。神經損傷按ASIA分級評定,A級5例,B級8例,C級13例,D級29例,E級4級。手術前均行傷段脊柱正側位X線片,損傷節段CT三維重建或行MRI檢查以明確骨折類型及脊髓神經受壓情況。X線檢查傷椎前緣高度壓縮至正常高度的25%~87%,平均47%。胸腰段骨折,Cobb角為15°~42°,平均26.5°。術前椎管內占位 0~79%,平均 57%。CT檢查47例傷椎雙側椎弓根完整,12例傷椎僅一側椎弓根完整。受傷至手術時間3~9 d,平均4 d。
1.2 手術方法
手術在全麻下進行。均采用俯臥位,腹部懸空。后正中入路,暴露傷椎上下兩個節段,顯露椎板、關節突。胸椎按照Roy-Camille法、腰椎按Weinstein法確定椎弓根螺釘進釘點,螺釘進入通道與椎體上下終板平行。傷椎經椎弓根預留鉆孔達椎體前緣骨皮質。安裝臨時連接棒撐開復位并固定。C臂透視骨折復位情況。術前有神經壓迫及損傷癥狀或CT、MRI提示骨折塊突入椎管內者進行全椎板減壓,探查,恢復椎管容積。拆除一側固定棒,顯露傷椎椎弓根預留孔,重新擴大至5~6 mm,用自制漏斗型椎弓根導入器將自體髂骨松質骨骨粒經椎弓根植入傷椎椎體內。植入的骨量根據術中情況而定。在傷椎內置入直徑較椎弓根導入器稍粗的萬向螺釘。螺釘長度需根據傷椎殘留正常骨質的多少選擇(30~35 mm),注意不要使其通過骨折線,以免影響整體復位效果和骨折愈合。若傷椎只有一側椎弓根完整則只植入一枚椎弓根螺釘。其螺釘尾端略高于上下節段的螺釘或連接棒預彎時適當減小其弧度以增加其向前的推頂力。安裝預彎的連接棒,調整棒位置后,擰緊螺栓,鎖定釘棒連接,椎體自動復位,透視復位滿意后,將切除椎板和棘突的骨塊及剩余的髂骨修剪成骨粒植入橫突間。鹽水沖洗切口,放置負壓引流管,逐層縫合。
1.3 術后治療及護理
術后根據積血引流量于48~72 h內拔出引流管,常規預防使用抗生素3 d。4周后戴支具下床。3個月內避免彎腰和旋轉動作。術后鼓勵患者行主動和被動四肢功能鍛煉,鼓勵患者咳痰預防肺部感染。
1.4 隨訪及療效評價
全部獲隨訪,術前術后常規X線及CT檢查,合并神經損傷癥狀患者行MRI檢查。從椎體前緣高度、脊柱矢狀面Cobb角、椎管占位、神經功能恢復情況及術后并發癥等方面評價手術效果。神經功能恢復情況采用ASIA分級。
1.5 統計學分析
用SPSS 10.0統計軟件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59例患者手術切口均一期愈合,術后無傷口感染、神經損傷等并發癥。隨訪12~24個月,平均17個月。術后椎體前緣高度是正常椎體前緣高度的82%~96%,平均91.7%;胸腰段 Cobb 角-1.5°~14°,平均 4.7°;術后復查 CT 示傷椎突入椎管內的骨塊復位良好,椎管占位基本消除,椎管占位1%~12%,平均4.3%。椎體前緣高度、術前Cobb角及椎管內占位與術后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P<0.05)(典型病例見圖1)。脊髓神經功能除5例A級無變化外,其余都有1~2級的恢復(表1)。患者術后腰痛癥狀明顯緩解。隨訪期間未出現內固定松動斷裂等并發癥。傷椎椎體內及橫突間植骨融合效果滿意。
3 討論
后路椎弓根螺釘內固定是目前國內外治療脊柱胸腰段骨折的一種可靠有效術式。單節段骨折常采取跨節段椎弓根螺釘內固定。該技術是通過縱向撐開力使壓縮的椎體恢復高度。但其前提條件是傷椎與上下鄰椎的前后韌帶和纖維環大部分完整。但跨節段椎弓根內固定應力集中于上下椎弓根間,負荷大部分通過椎弓根螺釘、釘骨界面,易出現應力疲勞。通過長期隨訪,術后內固定失敗、骨折椎體高度喪失、遲發性后凸畸形等并發癥的報道也逐漸增多。Mclain RF等[3]報道后路短節段內固定失敗率 (后凸糾正丟失≥10°或內固定斷裂)大于50%。胸腰椎骨折內固定失敗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后路椎弓根釘內固定術后椎體高度有所恢復,但椎體內被擠壓破壞的骨小梁系統未同時得到恢復,即“蛋殼”樣變。骨折復位固定后,腔隙內較大的血腫難以骨化,逐漸被纖維組織充填,從而出現不愈合現象,最終造成椎體抗壓及穩定性下降。多項臨床研究均表明傷椎骨缺損未修復是手術后矯正度丟失的重要因素[4]。

表1 脊髓神經功能改善狀況分布(n)

傷椎置釘治療胸腰椎骨折的理論和試驗研究起始于1994年。Dick JC等[5]首先進行了此方面的生物力學研究。2001年Shen WJ等[6]首次報道了應用傷椎置釘技術治療胸腰段骨折。自2005年起有關傷椎置釘技術的研究明顯增多。研究認為傷椎置釘的生物力學基礎在于椎弓根與關節突或椎弓根峽部間具有解剖連續性,在傷椎椎弓根中置入螺釘可使之不再“漂浮”,并能通過后方結構傳導相鄰椎體上的負荷。傷椎置釘可以將跨越傷椎上下椎體間的連接棒一分為二,連接棒越短,理論上內固定越堅固。傷椎置釘改善內固定系統的應力分布,并起到前推動力作用,協助矯正后凸畸形,同時增加內固定系統的把持力,減少釘-骨界面的運動。在此基礎上,經傷椎椎弓根植入自體松質骨,填充了椎體撐開復位后的間隙,且在植骨區形成網架結構促進骨性融合,最終增加了傷椎的骨密度及強度,使前柱載承功能有效恢復。傷椎置釘技術在傷椎上建立一個支點,使得復位更加容易,同時加上經傷椎椎弓根大量植骨,加快骨折愈合,增加了穩定性,大大減少了內固定松動或斷裂的發生。 通過對該組病例總結,我們認為在病例選擇上,傷椎椎弓根至少一側保持完整。在傷椎進釘時,由于椎體骨折,釘道前端有時無明顯的骨感和阻力感,因此傷椎置釘需更加小心,進釘不宜太深,選擇螺釘不宜太長,以避免通過骨折線。術中傷椎椎弓根進釘點可較正常進釘點偏外,以免誤入椎管損傷神經組織。雖然本手術具有較好的椎管間接減壓效果,若具備減壓指征,建議同時進行椎管探查,觀察骨折塊復位情況。對于復位欠佳者,可對骨塊進行打擊回納,為神經功能恢復創造條件。本組病例術后傷椎椎體前緣高度較術前顯著改善,后凸角明顯矯正。長期隨訪未見傷椎椎體前緣高度及后凸矯正度的丟失,說明該方法能較好恢復并維持復位后的椎體高度和生理曲度。神經功能恢復情況與術前相比,除完全癱瘓的病例外,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復,表明該方法能為神經功能恢復創造條件。
總之,經傷椎椎弓根植骨聯合傷椎置釘內固定治療胸腰椎爆裂骨折能夠恢復并維持傷椎前緣高度和生理曲度,為神經功能恢復創造條件,并能夠防止高度丟失,減少內固定并發癥,是治療胸腰椎爆裂骨折的較為理想的治療方法。
[1]Oner FC,Verlaan JJ,Verbout AJ,et al.Cement augmentation techniques in traumatic thoracolumbar spine fractures[J].Spine,2006,31(11 Suppl):S89-95.
[2]Mahar A,Kim C,Wedemeyer M,et al.Short-segment fixation of lumbar burst fractures using pedicle fixa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fracture[J].Spine,2007,32(14):1503-1507.
[3]Mclain RF,Sparling E,Benson DR.Early failure of short-segment pedicle instrumentation for thoracolumbar fractures.A preliminary report[J].J Bone Joint Surg Am,1993,75(2):162-167.
[4]Crawford RJ,Askin GN.Fixation of thoracolumbar fractures with the Dick fixator:the influence of transpedicular bone grafting[J].Eur Spine J,1994,3(1):45-51.
[5]Dick JC,Jones MP,Zdeblick TA,et al.A biomechanical comparison evaluating the use of intermediate screws and cross-linkage in lumbar pedicle fixation[J].J Spinal Disord,1994,7(5):402-407.
[6]Shen WJ,Liu TJ,Shen YS.Nonoperative treatment versus posterior fixation for thoracolumbar junction burst fractures without neurologic deficit[J].Spine,2001,26(9):1038-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