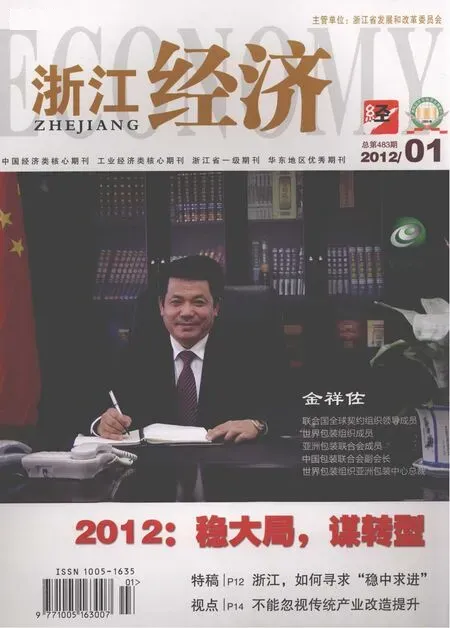臺灣工業化轉型之浙江啟示
□ 文/杜平
臺灣工業化轉型之浙江啟示
□ 文/杜平

臺灣地區的一個最主要經驗,便是從高貿易盈余、高出口導向依賴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轉型為一個貿易均衡、服務業發展較快、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推動的區域經濟體
當前,浙江等沿海地區面臨的一個最大挑戰,是如何在未來數十年通過轉型升級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而期待邁入高收入國家或地區行列。但目前浙江發展陷入了保增長與促轉型的一個雙重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出口導向發展型式日益成為固定的發展模式。在世界經濟環境不確定性日益增強和迫切謀求科學可持續發展方式的當下,如何轉變經濟出口導向發展型式,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轉型升級進而向高收入國家或地區水平邁進,成了一道亟待解決的難題。
無論從區位、人文、習俗等因素考慮,臺灣與浙江都有很多相似性。尤其是有一點上兩者具有巨大的共通性,即在不確定性因素較多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如何在工業化轉型時期、在本幣持續升值(1985-1995年新臺幣兌美元持續升值幅度達31%,年均4%)的壓力與基礎上,實現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雙贏。
出口導向型轉向均衡效率型
1985-1995年,臺灣地區貿易盈余比重大幅下降,出口導向發展型式逐漸轉向經濟均衡增長型式,是臺灣地區發展的又一個黃金十年。十年間,臺灣地區貿易盈余占GDP比重從約20%下降至3%左右,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8%左右,名義年均增長高達15%;人均GDP從4000美元提高至13000美元,一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初步邁入高收入國家和地區門檻,表現好過韓國等。經過這十年增長,臺灣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趨于成熟,歷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而總能夠化險為夷、基本不出現持續大幅衰退,經濟增長韌性彈性很強。
1985-1995年,雖然臺灣地區貿易盈余占經濟比重大幅降低,但貿易的重要性大大增強。十年間,進口占臺灣地區生產總值比重提高了7.3個百分點,進出口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到81.1%,對外貿易對臺灣經濟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臺灣經濟發展外向性或外貿依存度進一步增強。1985-1995年,臺灣外貿依存度平均為76%左右,這一比例比浙江2010年63.0%的外貿依存度還要高出13個百分點。
高速和平衡增長的進出口貿易,與臺灣地區及時調整外貿政策、大幅降低關稅稅率有關。1985-1995年十年內,臺灣地區積極推進外貿稅制體制改革,整體關稅占總稅收比重從16.9%逐步下降至9%左右。同時出口退稅的比例也大幅下調,出口退稅額占政府收入比重從1985年的7.1%左右降至1995年的不足0.5%,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反觀當前浙江地區,2010年出口退稅(1300億元)占浙江地方政府一般預算總收入比重仍高達26.5%、占全國出口退稅總額的18%,高額的稅收收入,大大強化了浙江及各地對原有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的“路徑依賴”。
產業結構與投資結構深刻轉換
1985-1995年,臺灣地區經濟結構變遷的一個重大變化是服務業產值和就業比重均大幅增加,服務業逐步取代工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十年間,臺灣地區服務業占經濟比重增加了約12個百分點達到60%,服務業就業人口大幅增長,服務業占三次產業就業比重增加10個百分點達到51%左右,從業人員增加了約1500萬人,幾乎以一己之力解決了臺灣地區全部的勞動力新增就業問題。1988年,服務業從業人員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成為臺灣地區產業就業結構變動的一個重大轉折。
1985-1995年,臺灣地區工業增長總體低于GDP增速,制造業產出占經濟比重從頂峰值39.4%逐步下降至28%左右,但工業質量和生產效率大幅提升,工業產值與增加值均實現翻番。工業結構變遷呈現出三個特征。一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占據主導地位,技術設備升級較快、人均產出大幅增長,工業結構完成向資本技術密集型、高技術型轉變,電腦、電子產品制造代替食品紡織成為主導行業。二是輕工業比重大幅下降。十年間,輕工業增長速度不及重工業的一半,食品飲料煙草等7個輕工行業占工業比重累計下降了約15個百分點,機械電子等8個重工行業占工業比重上升了約17個百分點。三是建筑業比重快速上升。這一時期無論是產出還是就業,由于城市化快速推進,建筑業增長相對制造業較快,建筑業產出占工業比重快速上升。
1985-1995年,臺灣地區產業對外投資迅速增長,逐步成為資本凈輸出地,有力地推動了低端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同時,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和服務業對外投資加快,金融業對外投資占據主導地位。
社會結構優化與轉型同步
1985-1995年,臺灣地區社會結構不斷優化,并實現了與經濟轉型升級同步。一是收入分配結構不斷優化。十年間臺灣地區分配結構演變體現了發展成果共享、增長與均富的特點,初次分配中的勞動者報酬比重達到51%(浙江僅為39%),最終分配中居民收入在占國民收入77.4%的高點上,繼續提高了約4個百分點超過81%。二是人口結構保持較強的生產性。雖然沒有實施類似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定階段,臺灣地區人口總和生育率開始自動穩定,人口穩步更替和緩慢增加,人口撫養比穩中有降,始終保持了較好的人口結構生產性,沒有出現由于人口干預政策形成過早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三是社會階層結構繼續優化。中小企業主、中上層技術人員官僚、企業管理層、專業人士等為主的中等收入群體快速發展,并成為社會主導階層。
1985-1995年,是臺灣地區城市化快速推進和城鄉一元結構最終形成的十年。根據臺灣有關機構及學者研究,按照人口口徑,十年內臺灣城市化率大約提高了10個百分點達80%,大大提升了區域現代化水平。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主要與臺灣工業化及其城鄉統籌發展政策有較大關系。值得關注的是,臺當局與時俱進出臺了一系列推進農村土地產權改革,實現土地宅基地等農民資產可流轉、可買賣、可抵押等的政策,大幅提高了農民收入和促進城鄉統籌發展。臺灣城市人口不斷集聚,城市郊區化、城鄉一體化發展顯著,大中心城市人口擴散溢出,10-50萬人口中型城市發展較快,人口在更廣義的空間上集聚,分布漸趨合理,城鄉差距不斷縮小,城鄉一元結構形成。

總結與啟示
“十年磨一劍”。可以說,臺灣地區用了十年左右時間(1985-1995年)成功實現了轉型升級,從中等收入一舉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究其原因,主要是:重視進出口貿易平衡增長,大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積極促進服務業發展,以城鄉土地流轉推動城市化工業化,及時改革完善政經體制、社會制度,促進增長與均富等等。這些都值得浙江及沿海其他地區借鑒。
——把握產業調整方向。工業內部以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積極研發技術裝備、機電等高附加值產品,引導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高新技術方向發展,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改造延伸。從工業為主轉向工業與服務業并重發展,打破服務行業壟斷,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積極引導二三產勞動力進入服務行業,使得服務業成為增長與解決就業的主力軍。
——平衡進出口貿易。應對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和出口退稅政策等的調整,注重省內消費,注重擴大進口,鼓勵企業到省外海外投資,實現經濟貿易平衡發展。呼吁中央針對浙江由于升值引起的出口退稅收入減少部分,通過其他方式從中央轉移至浙江地方,比如降低企業所得說、增加地方財政稅收比例或加強對地方的一般性轉移支付等。
——推進發展方式改革。當前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高附加值產業發展相對缺失導致人才大量流失,浪費了大量資源環境和受過良好教育等的高素質人才。應積極推進地方資源要素市場化、服務業去壟斷化、政績考核去GDP化、教育去行政化、省屬國有企業改革和財稅體制等改革,推動經濟發展進入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驅動的增長軌道。
——積極推進城市化和城鄉一元化。預計到2020年,浙江常住人口將達6000萬以上,杭寧溫三地將形成3個常住人口1000萬左右的城市帶或都市圈。這就需要切實盤活沿海沿江一帶縣市區的可利用土地資源,明確農民對土地的產權擁有,推進農村產權改革、耕地土地可流轉抵押,增加農村農民可售、可轉換資產,加快推進城鄉統籌和“農民工市民化、外來人口本地化”,但其中的許多方面有賴于中央宏觀層面的允許和突破。
——促進社會結構優化。臺灣經驗表明,社會建設發展、社會結構變遷與經濟發展結構變遷密不可分。尤其是處理好增長與均富的關系,形成一個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和中等收入群體,是轉型升級成功的重要內在力量。未來應加快調整優化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縮小貧富差距,壯大中間階層,推進包容性增長,以形成維持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良好環境。切實推進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為主轉變,大幅增加教育醫療培訓等的人力資本投入。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