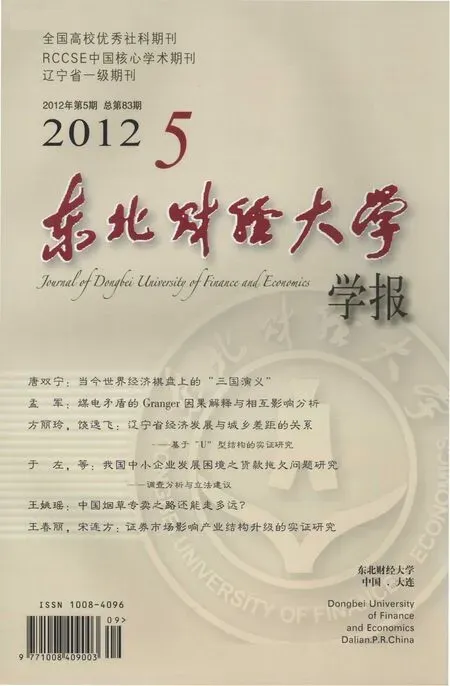基于制度分析框架下的計劃生育政策與女性就業
朱力凡
(東北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一、問題的提出
現有的經濟理論主要將女性與男性就業的差異歸因于兩個方面:第一,由比較優勢、人力資本、稟賦差異所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性別差異。第二,由雇主偏好、統計性歧視等所引起的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歧視[1]。實證方法如工資差距分析方法如Oaxaca 分解,Neumark 分解、Brown分解等也通過分解男女之間的性別工資差距,來得出這兩方面因素的影響程度[2]-[4]。
綜合來看,傳統的經濟學分析似乎都沒有將制度作為一種獨立的影響因素來研究其在女性就業過程中的作用。哈羅德·德姆塞茨認為,一個社會所面對的機會部分地由它的制度所決定,這是制度最重要的作用,制度的變化能產生新的機會組合[5]。諾斯將制度定義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6]。制度包括人類用來決定人們相互關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約。正規的(人類設定的規則)還是非正規的(如習俗和行為準則)兼而有之[7]。正規規則能貫徹和增進非正規制約的有效性,它們可能會降低信息、監督和實施成本,因而使得非正規制約成為解決更為復雜交換的可能方式[8]。正規規則也可能被用于修正、修改或代替非正規制約。
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認為,人口增長的限制來自于土地所能長期提供食物的能力[9]。這一理論已經遭到廣泛的批判。貝克爾認為,生育率的重要變化主要是由對孩子需求的其它變化引起的[10]。中國的情況是,制度是解放后中國人口的急劇增長及數量控制的重要因素。①前者指“人多力量大”的意識形態的重要影響,后者指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控制。1979年以后,中國旨在實現控制人口數量的計劃生育政策推行,除少數民族及一些特殊規定的情況,推行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宏觀上,政府面臨人口數量與資源稀缺矛盾的權衡,也面臨人口結構與就業、養老等各項社會民生是否協調發展的選擇。微觀上,家庭內部生育子女個數的決策受到限制,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也使家庭對子女性別的選擇偏好受到制約。
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一種正式制度,會對人們的行為選擇構成何種激勵?會如何對非正式制度產生影響?具體來說就是,計劃生育政策是否有助于抑制傳統的性別偏見?是否對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有負向激勵?該政策對女性就業究竟有何影響?本文嘗試用制度理論的分析方法,來探尋這些問題的究竟。
二、計劃生育政策的前勞動力市場效應
1.計劃生育政策的性別偏好效應
主流經濟學家往往認為偏好受傳統文化、習俗信仰等的影響。偏好是人類的一種天性,是起獨立約束作用的一個經濟學分析工具。在制度因素作為一個重要變量被納入經濟研究之后,對偏好的研究也將翻開新的篇章。制度通過對傳統文化、生活習慣等非正式制度的影響來改變人們的偏好。確切地說,制度和偏好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并不斷在發生變化。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使一個家庭只有一個男孩或只有一個女孩成為普遍的家庭結構。
諾斯指出:“如果不認識主觀偏好在正規制度約束邏輯下的重要作用,我們就不能理解歷史(或當代經濟),它使我們以零或非常低的成本表達我們的信念和思想,有組織的意識形態以及宗教狂熱在決定社會和經濟中起的重大作用。”[6]計劃生育政策不斷向人們傳遞一個信息:“生男生女都一樣,女兒也是傳后人”。這個信息是對中國家庭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的否定,也逐漸改變了人們的內生偏好。①主流經濟學認為偏好是固定外生的,正統分析制度影響的方法往往只討論偏好給定情況下的資源配置。但是制度會直接影響人們的偏好,從而改變偏好給定的簡單假設。Bowles 將此定義為制度的解釋效應:當參與人具有相同的備選條件時,制度不同,人們的選擇不同[11]。
相關調查表明,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無論是城市婦女還是農村婦女,理想子女數都顯著減少。大多數女性偏好小型家庭結構:35%的女性愿意只要一個孩子,57%的女性喜歡兩個孩子,只有5.8%的女性偏好3 個或更多孩子。與此同時,傳統偏好男孩的思想意識也有了變化,調查發現中國目前很多婦女尤其是城市中的年輕婦女偏好女孩[12]。可見,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家長對子女數量及性別的偏好會發生改變。
2.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力資本投資效應
家庭在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受家長偏好、家庭預算約束及預期的收益所影響。可以運用貝克爾的家庭效用函數方程來說明這個問題[13]。

方程中假設家庭預算約束為I,pc表示一個質量單位不變成本,q 表示孩子的總質量(花在每個孩子身上的費用),n 表示家庭孩子個數,z表示其它商品,πz表示z 的成本。商品及數量和質量的相互影響是非線性的。以此推論,在家庭預算約束不變的情況下,孩子個數n 越少,對每個孩子的平均花費q 就越高。與貝克爾分析不同的是,中國生育率的顯著變化不是因為家庭對孩子的需求有所改變,而是由制度引起的。家庭生育率降低,對每個孩子平均花費q 提高,對子女的人均人力資本投資預算也就越多。以此推論,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改變了家庭生育子女的個數,從而也將改變家庭平均的人力資本投資預算。當家庭只生育一個孩子時,這個孩子擁有家庭對子女全部的人力資本投資預算I。這將有效避免因家庭預算約束有限而又多子女的情況下,父母只對男孩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偏向。(中國傳統文化中“養兒防老”等非正式規則的存在,使得父母形成對男孩養老的期待。在“投資—收益”的角度看,從前父母更愿意對男孩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也得到一部分解釋。)
三、計劃生育政策的勞動力市場效應
1.計劃生育政策與女性勞動力供給
人口數量的不斷增長與經濟資源的有限性相互矛盾,計劃生育政策直接降低了生育率,控制了人口的過度增長,在未來一定時期內,避免了由于人口過度增長引起的那部分資源消耗,降低了人口擁擠效應造成的就業壓力。
計劃生育政策改變了家庭中人均人力資本投資的預算約束,總體上增加了家庭對女孩的人力資本投資,進而改變了女性勞動力供給的質量。理論上分析,女性也更多的參與到科技水平含量高、對人力資本儲量要求高的職業中去。Elisa于2002年的研究證明,人力資本稟賦、人口統計學變量和家庭的特征等都會顯著的影響女性就業偏好及勞動供給。
職業女性面臨家庭和工作雙重責任平衡的難題,嬰幼兒的生育和撫養直接改變了女性勞動力供給的周期及時間。為了生育孩子女性不得不間斷性的退出勞動力市場。假設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和次數由子女個數決定,則生育子女個數越多,退出勞動力市場時間越長,次數越多,從而造成女性職業生涯的間歇性中斷。有些女性甚至完全退出勞動力市場將所有精力用來照顧撫養孩子。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家庭生育子女的個數顯著減少,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和次數也隨之減少。正如制度的一個作用就是通過向人們提供一個日常生活的結果從而減少不確定性,降低交易費用,計劃生育政策正是通過改變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時間和次數,減少了其不確定性,降低了交易費用。
2.計劃生育政策與雇主需求
統計性歧視理論從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的角度解釋了雇主對于女性的歧視。雇主獲取求職者信息的方式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通常為了節約成本,雇主對求職者的個人信息判斷來自他所屬群體的一般特征。而群體的一般特征有時候是生產率高低的外在表現,有時候則是因為某些約定俗稱的因素、傳統文化的定性(非正式制度)而存在的。制度因素對雇主統計性歧視的解釋即:計劃生育政策在改變家庭生育子女個數的同時,提高了女性勞動參與率。從雇主的角度出發,女性較之從前生育多子女的情況,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和次數的不確定性降低,雇主對女性就業預期的不確定性也會降低。從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統計性歧視。①這里專指生育率降低對女性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不考慮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總體差別。
四、計劃生育政策的混合效應
1.計劃生育政策的成本效應
新制度經濟學家已經證實,制度的實施是需要成本的,當制度實施的成本小于因制度實施而降低的交易成本時,制度的實施是有效的。但是制度不能杜絕參與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威廉姆森認為人們有“狡詐的追求利潤的利己主義”的傾向,為了謀取個人利益最大化,會采取隱蔽的手段,投機取巧的實現利己心。“當騙人能增加利潤時,交易中的誠實未必可取。”參與者的機會主義傾向增加了制度實施的復雜性,加大了交易成本。
人們計劃生育政策的機會主義行為表現為,為了實現個人生男孩的偏好,參與者通常采取隱蔽的方式,如:選擇性墮胎、不給女嬰上戶口、遺棄或殺害女嬰等方式躲避政策約束,造成性別比例失衡、人口撫養比例的降低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問題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成本之一。第一,違反制度規定(胎兒性別鑒定及人工終止妊娠)的成本較低,那些偏好男孩的家庭,選擇嬰兒出生性別的機會主義行為不能被有效抑制,導致出生性別比失衡,由此造成了人口性別結構失衡。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19 歲以下年齡段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到2020年時,中國適婚年齡男性人數比女性多2400 萬。這對中國當前及今后的人口再生產、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養老機制甚至社會穩定都構成了一定威脅。同時,勞動力市場中男性比例的增高,男性對女性就業的擠出效應上升,使原本就處于弱勢的女性就業更趨艱難。第二,計劃生育政策規定,夫妻雙方均屬農業人口,第一個子女是女孩的,可按規定再生育一個子女。這個規定直接導致農業人口家庭中只有一個男孩的比例升高。基于城鎮戶口與農業戶口的制度約束不同,城鎮家庭與農村家庭中撫養子女的個數與性別比也出現差異,制度安排直接導致城鄉家庭結構差別的不斷擴大。基于計劃生育政策前勞動力市場效應的分析,農村多子女家庭的父母在家庭預算約束下,傾向于對男孩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城鎮家庭多為獨生子女,對女孩的人力資本投資比農村要高。因此,總體來說,農村女孩受到更多的性別歧視,得到的人力資本投資概率也低于城市女孩,未來的就業前景與城市女孩之間的差距也自然越大。②在此不進行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前后的城鄉對比,只比較計劃生育政策針對戶口屬性不同而采取不同措施所造成的城鄉差別。
2.混合效應
諾斯指出,制度框架可能同時混雜著某些相反的結果。這種相反的結果包括兩層涵義:第一,單一制度的混合效應。計劃生育政策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女性人力資本投資和降低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歧視,另一方面也會導致性別比例失衡,擴大城鄉女性人力資本投資及就業之間的差距。第二,多種制度的混合效應。計劃生育政策是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實施的,而女性就業問題是由多種制度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因素等綜合作用的結果。計劃經濟時期,女性勞動力資源得到了空前的動員,過去只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也參與經濟工作,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于同時期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經濟時期,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弱勢體現出來,即使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大學生就業也頻現困境。因此,理論上推論,市場經濟中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城鎮女性所遭受歧視的境遇要好于未實施該政策的境遇,對農村女性就業的效應究竟是正是負還難以預測。但是,現實的結果,計劃生育政策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具體如何,因為得不到未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女性就業的情況,使得理論估計難以得到實證的驗證。
五、結論
制度因素對女性就業的影響作用已經超出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本文運用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探討計劃生育政策對女性就業產生的影響。
在前勞動力市場,計劃生育政策有利于提升女性的人力資本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家庭對子女性別的偏好。勞動力市場上,計劃生育政策降低了女性生育決策的不確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改變了雇主對女性就業的預期,降低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歧視,從而有利于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女性勞動力資源的供給。但是,計劃生育政策也產生了負效應,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及政策條款的城鄉差異,提高了性別比,使更多的男性與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造成了擠出效應不利于女性就業,也擴大了城鄉女性的就業差距。此外,計劃生育政策也產生了一系列混合或相反的作用結果。
以上只討論了計劃生育政策對女性就業的影響。但是,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作用范圍非常廣泛。各種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往往相互影響,并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特點。因此,制定一項政策要綜合考慮政策的各種效應,應當盡量規避政策的負效應、增加社會整體福利。
[1]Gneezy,U.,Niederle,M.,Rustichini,A.Performances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Gender Difference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3):1049-1074.
[2]Oaxaca,R.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73,10(3):693-709.
[3]Newmark,D.Employers Discriminatory Behavior and the Estimation of Wage Discrimination[J].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88,23(3):279-295.
[4]Brown,R.S.,Moon.M.,Zoloth,B.S.Incorporating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Studies of Male- Female Earnings Differentials[J].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80,33 (1):3-28.
[5]哈羅德·德姆塞茨.經濟發展中的主次因素[A].科斯,諾斯,威廉姆森,等.制度、契約與組織——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的透視[C].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82.
[6]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1,61.
[7]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4,63,64.
[8]Paul,M.,North,D.,Weingast,B.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The Law Mechant,Private Judges,and the Champagne Fairs[J].Economics and Politics,1990,2(1):1-23.
[9]馬爾薩斯.人口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54.
[10]加里·貝克爾.家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147.
[11]Bowles,S.Endogenous Preference: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Markets and Other Economic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8,36(1):75-111.
[12]屈堅定,Therese,H.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與家庭理想子女數、子女性別偏好和出生性別比:國家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調查結果[J].英國醫學雜志(中文版),2006,(4):209-212.
[13]加里·貝克爾.家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