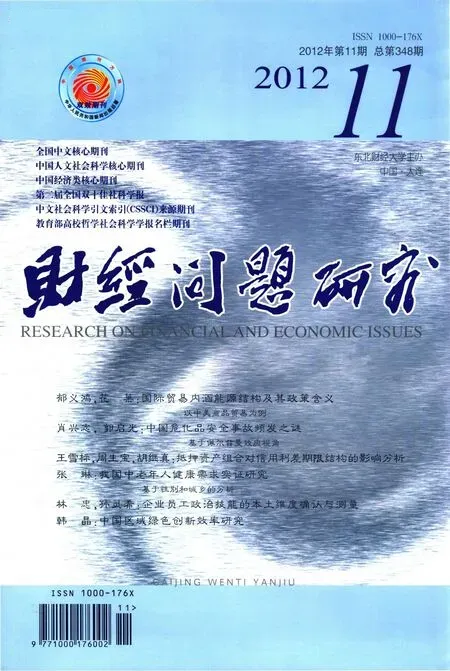中美人民幣“匯率操控”爭端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李雙久,楊 敏
(1.貴州財經大學 西南地區經濟發展研究院,貴州 貴陽 550004;2.貴州財經大學 國際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4)
作為開放經濟核心經濟變量的匯率不僅與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直接相關,也與其他宏觀經濟變量密切相關。一國匯率的波動對其進出口貿易、國際資本流動和就業等都有著極大的影響,關系著一國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人民幣匯率作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重要經濟變量及其與其它經濟指標之間的普遍聯系,造成了人民幣匯率變動經常成為美國對中國經濟加以詬病的工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也正是通過匯率這一有效杠桿不斷地對中國經濟施加壓力。
一、中美人民幣“匯率操控”爭端表現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在給世界經濟伙伴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在相對經濟意義上給世界各大經濟體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壓力。在資本主義所主宰的世界經濟次序以及美元霸權統治的國際貨幣體系下,“人民幣操控論”、 “人民幣快速升值論”、“人民幣罪惡論”以及“中國威脅論”等論調此起彼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針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正在采取形式各異的“約束戰略”和“積極防御戰略”。
2009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伊始就在西方社會大肆渲染“人民幣匯率操控”的論調。美國候任財政部長蓋特納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為其舉行的提名聽證會上說:“美國總統奧巴馬相信中國正在‘操縱’人民幣匯率,并將積極通過所有能動用的外交途徑,尋求讓中國在匯率方面做出改變”。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則針對美候任財政部長的言論表示,“這些言論不僅不符合事實,更是對金融危機原因分析的誤導”。
2009年5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先生在其中國行期間,就拋出了“人民幣匯率操控”的論調,“中國巨大貿易順差是政府干預操控匯率的結果。中國通過設定相對固定的匯率,然后通過大量購買外幣來維持其貨幣比較弱的估值”。中國學者對此發起了激烈的論戰。龍永圖先生反駁克魯格曼說:“中國目前不實行貨幣自由兌換其實是美國主導的金融秩序導致的后果,而不是中國政府的操控”。“現在全世界的國家當中,有些是實行本幣不可兌換,有些決定不開放自己的資本市場,克魯格曼先生認為凡是選擇實行自己的貨幣不可兌換的就是操控匯率嗎?”[1]。然而,2009年10月,美國財政部報告指出,在過去4年中人民幣兌美元升值21.2%,因此中國沒有為獲得不公平的貿易優勢而操縱匯率政策。由此可見,美國所謂人民幣匯率操控與否的評判標準其實就是人民幣兌美元是否升值。

表1 2010年人民幣匯率操控爭論簡覽
2010年,中美兩國關于人民幣匯率操控與否的爭論并沒有因人民幣匯率的緩慢升值而降溫。根據《國際金融報》的統計整理,中美兩國2010年在該問題上已進行了數個來回的論戰,如表1所示。
二、研究綜述
王凱等通過對1994—2010年中美兩國相關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中美貿易收支和人民幣實際匯率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美國的需求因素才是真正影響中美貿易收支的主要原因”[2]。王志指出,“中美之間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開始出現于2002年,始作俑者來自日本。日本財政部官員提出了‘中國通過人民幣盯住美元,輸出通貨緊縮’的說法,強調人民幣應該采取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自此美國開始接受,一再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打壓中國,要求人民幣升值”[3]。張宇燕認為, “中國的崛起讓美國各界感到憂慮,美國希望利用某種武器對中國形成某種行之有效的打擊,而人民幣匯率問題正好是這樣一種武器”[4]。張銳認為, “只要人民幣升值達不到美國的要求,或者說人民幣還有升值的空間和利用的價值,美國就不會放棄借此大做文章的機會。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的恢復異常艱難與曲折,人民幣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將成為‘替罪羊’”[5]。吳萍萍認為“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來是美國用來對付中國的一招棋”。中國政府應該采取措施,“在與美國的匯率干預周旋中爭奪話語主導權,引導世界不僅關注美國的失業問題,同時注意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就業的巨大沖擊”[6]。卜拙認為“人民幣的問題,并不出在中國,而是在美國國內。美國出口不振,債臺高筑,才是施壓人民幣升值的動因所在”[7]。王小寬和徐娟認為“要最終解決中美之間的匯率問題,還是要通過加強雙方對話,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理解,本著和則兩利、斗則兩敗的認識,通過協商對話來解決問題,最終取得互利雙贏的結果”[8]。
三、人民幣“匯率操控”的由來
“匯率操控”這一名詞起源于《IMF協定》。《IMF協定》第4條第1節第3項對“匯率操縱”進行了規范,即IMF成員國不得通過操控匯率或國際貨幣體系,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而獲得比其他成員方更有利的不公平競爭優勢。該規定的核心思想就是為了避免在國際貿易中通過對匯率的非市場化干預,獲得相對競爭優勢的行為發生。很明顯,條款中包含兩個要素,即匯率的非市場干預和不公平競爭優勢的獲取。但是,這兩個要素在實際操作中很容易遇到障礙,也就是兩者的因果關系很難界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IMF在2007年通過了一個《決議》,對匯率操縱的含義作了明確界定,并對為取得對其他會員國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而操縱匯率做出了明確的規定。根據2007年《決議》,一國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第一,操縱匯率的行為是客觀存在的,即成員國采取了實際影響匯率水平的政策,并使得匯率嚴重低估,擴大凈出口;第二,該行為的主觀意圖在于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或取得對其他成員國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雖然,IMF對于匯率操控的規定進行了修改與勘定,但是由于匯率這一經濟指標的復雜性,最終導致該條款仍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首先,該條款和《IMF協議》的其他條款所規定的邊際交叉模糊。根據IMF的規定,成員國有權安排適合本國經濟的匯率制度。根據這一條,當前中國亦有權利將自己的匯率政策重新安排到固定匯率制,并且對美元的匯兌比例為1美元/10元人民幣 (在現實中,這不可能,但理論上存在可能性)。如果這樣,是否有違《IMF協議》有關匯率操控的規定呢?顯然,沒有違背。但是理論上這種假設的制度安排卻為中國的出口創造了十分優越的競爭優勢。由此可見, 《IMF協議》的規定在現在來看,并不科學。其次,該條款中提到的匯率低估和擴大凈出口同樣不準確。匯率被低估的前提就是必須出現一個均衡匯率,而這個均衡匯率根據目前不同的手段和方法進行核算,其結果并不是唯一的,核算過程中有太多因素可以影響最終的結果,比如消費偏好和通貨膨脹。再次,對于擴大凈出口,目前的爭議很多。凈出口由出口減去進口得到,因此凈出口的增加可以是因為出口的增加,也可以是因為進口的減少,還可以是出口和進口的同時減少,只不過出口的減少沒有進口的減少多而已。最后,對于主觀意圖的判定過于模糊。世界上意圖與期望結果不一致的事情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某種意圖未必就能獲得初始的期望結果,并且某種期望結果未必就是通常情況下人們所能臆測到的某種初始意圖。在沒有特定條件的限定下,意圖與結果兩者之間是一種非充分非必要條件。因此,對于人民幣匯率操控的主觀意圖的判定實際上是非常模糊的。
四、人民幣匯率操控的實證檢驗
依據前文對于《IMF協議》中匯率操控規定的理解,本人認為,在不考慮主觀意圖的核實的情況下,匯率操控定義的核心內容就在于匯率波動對一國凈出口,也就是經常性賬戶的影響。如果兩者存在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的正相關性,則可以模糊地證實該國存在匯率操控的嫌疑。如果在統計學意義上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則可以證實該國不存在匯率操控的行為。
馬歇爾—勒納條件指出,當進出口需求彈性之和必須大于1,本幣貶值會改善貿易逆差。因此,本文對于人民幣匯率變化能否顯著影響中美貿易收支的實證檢驗就轉化為對中美兩國進出口需求彈性的核算。
首先,我們考查等式:

其中,XR表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與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額的比值,P中表示中國的價格水平,EX表示中國向美國的出口額,P美表示美國的價格水平,IM表示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額,R直表示直接標價的匯率。
這個式子可以經過以下變形:

根據購買力平價公式,上式可變形,變形后E代表實際有效匯率。

其次,出口和進口需求方程如下:

最后,我們將上面的幾個式子整理,最終得出凈出口需求彈性核算的模型。

根據模型,實證檢驗過程中需要進行參數估計的就是LnE之前的系數。這個系數表示的是出口需求彈性和進口需求彈性之和與1的差。如果該參數大于0,表示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本模型中,所涉及到的經濟指標有四個,即出口額與進口額的比值 (XR)、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 (E)、美國的國民收入 (Y美)、中國的國民收入 (Y中)。為了考察變量間的彈性關系并盡可能消除異方差性,所有變量以自然對數形式進入計量方程。根據經驗分析,設計時間序列的計量檢驗一般都必須進行協整檢驗。因此,對于人民幣匯率以中美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檢驗就是兩者間的一個協整檢驗。
考慮到實證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的是1992第一季度到2010年第二季度的連續時間序列數據。其中,出口額與進口額的比值(XR)選取IMF的IFS統計數據庫的進出口數據進行計算得到;人民幣有效匯率選用中美兩國的雙邊匯率,來源同樣是IFS統計數據庫。美國的國民收入選用的是IFS統計數據庫中的GDP季度數據。中國1992—2005年的GDP數據來自于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于2008年編寫的《中國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1992—2005》,2005年之后的數據來自于國研網的季度數據。并且,本文所用數據均進行了季節調整。
我們對原方程進行直接的簡單多元回歸。從回歸結果中,我們很容易發現,這個回歸是一個典型的偽回歸,原因就在于擬合優度值與DW檢驗值太低,并且R2大于DW檢驗值。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認為,有可能是由于原序列的非平穩性引起的 (無論隨機變量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這些隨機變量的不平穩性越高,回歸方程擬合程度就越高,發生偽回歸的可能就越大)。
因此,我們需要對原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確定其平穩性。通常情況下,進行單位根檢驗的方法是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所使用的工具是EViewS5.0軟件。單位根檢驗的基本原理是首先假設各序列存在單位根,然后將ADF檢驗的結果值與特定水平下的臨界值進行對比,如果ADF值>臨界值,則表明接受原假設,即序列存在單位根,序列是非平穩的,反之亦然[9]。如表2所示。

表2 單位根檢驗
表2就是ADF單位根檢驗的結果。根據ADF單位根檢驗的結果,我們發現原序列都是非平穩序列,但是他們的一階差分序列卻都是平穩序列。多元時間序列的協整檢驗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階序列的平穩。顯然,本部分的時間序列滿足這個條件。
協整檢驗的目的是為了考察非平穩序列之間或者他們的線性組合之間是否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如果多個時間序列變量是不平穩的,但它們的同階差分是平穩的,則這些非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通常情況下,用于檢驗多元變量的協整關系所用到的方法是Johansen協整檢驗法。Johansen檢驗中最重要的一個參數選擇就是滯后期數的選擇。本文研究中所選用的數據是季度數據,因此本文中的Johansen檢驗所選擇的滯后期為4。
進行Johansen檢驗中,對原方程的殘差項進行了自相關檢驗、正態分布檢驗和異方差檢驗。檢驗結果表明,對人民幣匯率的中美貿易彈性的協整檢驗是一個無偏的、有效的檢驗。最終的參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
根據參數估計結果,我們可以寫出最初的方程:

方程中,LnE之前的系數小于0,這就說明中美貿易并不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并不是引起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人民幣匯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中美之間的出口與進口之比將下降0.34個百分點。根據檢驗結果,我們發現,Y美之前的系數為正,這表明每上升一個百分點,中美之間的出口與進口的比值就要上升3.52個百分點。而中國的GDP對中美貿易不平衡沒有顯著的影響。美元主宰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國內經濟規模、美國的出口管制、美國的經濟結構和消費模式等才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最主要原因。
五、中美貿易實踐的理論分析
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美兩國的經貿關系無論從廣度和深度上都獲得了長足發展。與此同時,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也日益加劇,逐漸成為雙邊經貿關系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障礙。美國對華持續的反傾銷案、反補貼案、反傾銷和反補貼“兩反”合并調查、有關知識產權的“301條款”和“337條款”調查,以及對華“特定產品過渡性特別保障措施”調查等各種貿易救濟措施的依次不斷實施。與此同時,美國還不斷地聯合其西方盟友一再地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這種指責不僅缺乏如前所述的理論依據,也不符合美國國際貿易逆差的事實基礎。
1.匯率波動不是導致中美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理論研究的確為構建和諧、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各不相同的設想。但是,基于有限的假設條件而構建的任何一種國際經濟理論都與當今的國際政治經濟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迄今為止的理論與實踐都一再地證明,一國貨幣升值或貶值對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都是極其有限的。在20世紀70—80年代,在面對德國和日本經濟迅速崛起,美國的貿易逆差與日俱增的條件下,美國也曾經向德國和日本施加壓力,迫使兩國貨幣大幅升值。但是直到2008年,美國對德國貿易仍有400多億美元的逆差,對日本貿易逆差則達到700多億美元。2005—2008年,人民幣對美元快速升值,同期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年均增長20%多。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相對穩定,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卻下降為16.1%。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并不是造成中美貿易大量順差的主要原因。以2004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為例,當年美國的貿易逆差總額為6 500億美元,其中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約為1 600億美元,占同期全部逆差的24.8%。而同期源自于日本、加拿大、德國、墨西哥、委內瑞拉、韓國、愛爾蘭、意大利、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亞、中國臺灣、泰國等13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逆差總量為3 800多億美元,占同期貿易逆差的58.3%。兩倍于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在此期間,美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的匯率也是有升有降的。
2.中美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自身
從經濟結構上看,在美國的三次產業構成中,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0年為24.2%,2009年下降為21.4%;相反,第三產業增加值自2000年以來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2000年為74.6%,2009年為77.4%。從美國的經濟政策上看,美國政府長期實行低利率的貨幣政策,刺激了國內消費的膨脹,尤其是日常消費品需求的增長導致了美國國內對國外消費品大量進口。1990年和2000年,美國居民消費率分別為66.7%和69%,2005年以來美國居民消費率一直處于70%以上。直接導致消費品進口的增長。與此同時,美國對高技術出口和管制,不僅沒有實現靠高技術產品出口彌補消費品進口所形成的逆差,而且自2003年高技術產品還出現了268.22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這一數額擴大到370.24億美元,增加38%。
美元主宰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自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際貨幣體制已不復存在,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并沒有改變,美國靠發行本幣支持強大的本國消費的行為不再受到黃金儲備的約束。同時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經濟金融化的過程中,美國始終是各種金融創新工具的發源地,不論是危機前的次級貸款、美國國債,還是其它金融創新工具都吸引了大量的國外游資流入,也直接造成了美國的逆差。
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20年時間里,美國是世界工廠,其實體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均在40%以上,包括金融房地產在內的虛擬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最高年份也不超過19%。70年代以后,美國的虛擬經濟成分逐年上升,到2009年,虛擬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接近40%。“隨著美國經濟的虛擬化和去工業化,美國經濟的對外交往方式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70年代以前美國經常項目持續順差、資本項目持續逆差的格局發生了根本性逆轉,“現在的美國不再是對世界提供大量產品和技術裝備的凈出口國,卻是對世界大量輸出各種債券和金融資產的凈出口國;靠美元國際本位貨幣的地位,美國成為國際經濟生活中靠購買產品和各種能源參與世界經濟的凈消費者。從世界工廠的產品凈生產者到世界凈消費者的轉變是美國經濟對外交流方式的根本變化”。同時,經濟虛擬化與經濟對外交流方式之間相互促進,并外在地表現為國際貿易失衡和境外美元資產膨脹。
據胡小娟和劉玉的研究,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對于改善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結構具有明顯的相關性[10],另根據梁艷的研究,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同時也增加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即美國在華投資加劇了美中貿易逆差[11]。上述事實也進一步證明了,美中貿易的不平衡除美國經濟政策、產業結構、居民消費等因素外,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也加劇了美中貿易的逆差。
六、結 論
我們通過實證檢驗的方法對“人民幣匯率操控”這一論題進行實證解析。匯率操控的定義是指成員國通過操控匯率或國際貨幣體系,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而獲得比其他成員方更有利的不公平競爭優勢。從匯率操控的定義看,一國對匯率所采取的措施必須能夠帶來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才有可能是匯率操控。但是,通過實證分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中美之間的對外貿易并不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即人民幣貶值并不能帶來中美貿易順差。因此,中國并不是“匯率操縱國”,人民幣匯率也不存在匯率操控問題。
不論從實證研究方面,還是在理論分析上,或是在中美貿易實踐的角度看,美國對中國操控匯率的指責都缺乏有效的根據。
[1] 丁曉琴,周鵬飛.龍永圖反駁諾獎得主克魯格曼“中國操控匯率”論[N].新京報,2009-05-12.
[2] 王凱,龐震,潘穎.人民幣實際匯率與貿易收支:中美、中日比較分析[J].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11,(3).
[3] 王志.國家/社會視角下中美人民幣匯率糾紛[J].理論界,2008,(11).
[4] 張宇燕.國際經濟政治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00,250.
[5] 張銳.人民幣匯率中美再博弈[J].金融與經濟,2010,(5).
[6] 吳萍萍.中美“匯率操縱”之爭[J].中國外資,2010,(5).
[7] 卜拙.中美匯率博弈困境[J].價格與市場,2010,(6).
[8] 王小寬,徐娟.中美匯率博弈透視——訪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J].今日中國論壇,2010,(8).
[9] 尹希果.計量經濟學:原理與操作[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349-365.
[10] 胡小娟,劉玉.美在華投資與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結構關系研究[J].金融與投資,2007,(12).
[11] 梁艷.美在華直接投資對中美貿易平衡的影響[J]. 宏觀經濟,2010,(9).
[12] 謝杰.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對中國經濟各產業的影響——基于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分析[J]. 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