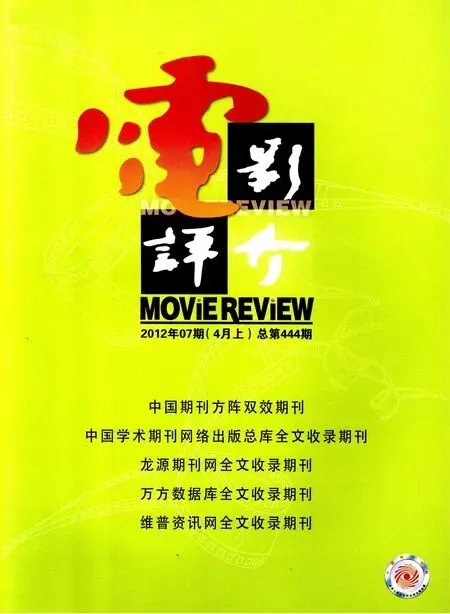文化記憶中的影像符碼——解讀春晚三十年
一、視覺鏡像中的家國變遷
春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它的存在是維系民族情感、體現家國認同的重要紐帶。三十年來,春晚已成為國人歡度春節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如若不加特別說明,“春晚”就是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特指,這足以表明它在人們心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可以說,春晚對于整個民族而言,不再是一種普通的聯歡晚會,它是過年不可或缺的一道年夜飯,是一種儀式,一種情結,一種新的民俗文化,一種意識形態的文化符碼。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三十年的風雨兼程,春晚承載了越來越多的文化元素和時代使命。它用視覺影像記錄著我們國家各個方面的歷史演變,映射著人們思想和價值情感的轉變軌跡,塑造著一代又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和文化情懷。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社會物質相對貧乏,電視還未大范圍普及,人們剛剛從“文革”的“傷痕”歷史中回返過來,長期禁錮的思想牢籠被打開,人們朝氣風發,充滿了昂揚向上的淳樸激情。1983年,央視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拉開了帷幕。在導演黃一鶴的一再堅持和觀眾的熱情電話點播下,李谷一那首被視為靡靡之音的《鄉戀》才得以上演,這段插曲成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性解放的標志性事件,一時傳為佳話。盡管,當時物質條件有限,舞臺不大,節目不多,主持人服裝不那么光彩耀人,但春晚卻給千家萬戶帶來了節日的歡樂,成為一代人難忘的美好回憶。9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的發展、商業資本的入侵,在極大豐富了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春晚開始步入青少年時期,少了幾分童年的乖張,多了幾許少年的叛逆與囂張。春晚開始以華麗宏大的舞臺和人數眾多的演唱來吸引觀眾眼球,商業元素介入,觀眾開始對春晚感到陌生。而駛入新千年以來,人類進入了一個知識爆炸的新時代,網絡等高科技不僅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且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判斷。在時代的巨變面前,春晚仍然按部就班地邁著小腳前進,難免讓人產生審美疲勞。主持人、演員總是那些老面孔,舞臺、節目也總是沒有多少新意。于是,很多人改變了原來過節的傳統習慣——春晚成了可有可無的存在(尤其對于當下的年輕人)。
近兩年,隨著中國GDP總量的持續攀升,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深化,圍著電視看春晚的人不多,坐在電腦面前“圍觀春晚”者卻大有人在。大家通過微博、論壇紛紛談論著,似乎春晚已成了一種無意識的集體圍觀。在網友們看來,80年代的“孔雀公主”楊麗萍今天跳的孔雀舞是專給高雅人看的“原生態”;當年的“小虎隊”重聚首,被網友戲稱為穿著東北二人轉衣服的“老虎賣萌”;天后王菲的失常發揮更是引起不少人調侃……毋庸置疑,春晚的路將會越來越艱難。
很明顯,從1983年開始至今春晚已經走過了長長的30年。中國人常說“三十而立”,三十歲是一個人成年的標志。同樣地,在億萬觀眾的陪伴中,春晚也漸漸從幼稚走向成熟。所謂“眾口難調”,隨著社會的開放,選擇的豐富,價值追求的多元化,春晚將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在商業、政治、文藝、消費的權力博弈中,春晚依然在摸索中前進著。
二、消費邏輯下的懷舊情結
“如果說80年代文化著力于展現嘎然有聲的歷史階段的劃定與歷史斷裂的描述,那么90年代文化則更多地是以‘臨淵回眸’或悵然回首的姿態書寫歷史的綿延,或者說是在個人與命運的故事中書寫生命之流。”[1]那么,當時間之軸指向21世紀的消費坐標以后,“懷舊”成為一種文化需要應運而生。
一般來說,“懷舊”情結貫穿于整個人類文明史,具體到當下這個欲望橫流、競爭激烈的社會,“懷舊”儼然已是消費社會邏輯下現代人感性泛濫的一種文化表征。現代社會距離感的產生,使每個人都渴望獲得一個獨立自由的空間,但這種“距離感”的產生,愈發使得個體害怕與他者進行接觸,誘發所謂個體身心的“畏觸感”。[2]而“懷舊”為人們建構了一方暫時逃避外界紛擾的心靈庇護空間,于是越來越多的懷舊小說、懷舊音樂、懷舊建筑、懷舊影視充斥著我們的生活。
與此同時,隨著傳統時間觀念的打破,現代社會中的個體被迫進入一種碎片化的、流動不息的空間之中,個體生命充滿了孤獨與不安,對自身價值和身份確認的渴望更加強烈,這就是馬斯洛文化心理學所說的“歸屬感的需要”。歸屬感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每個個體都希望自身歸屬于某一個群體或者共同體,同時在這個歸屬集體中得到相互的關愛和支持,獲得生命存在的價值與認同。因此,現代人急需一種集體懷舊的儀式,來化解我們既渴望自由,又極力尋找歸屬的矛盾心理。每年一度的春節晚會無疑是中國人化解這種心理矛盾的最好方式之一。春晚自身的娛樂屬性很容易使個體得到放松,而且,作為一個公共的文化場域,春晚以前不變的“懷舊”姿態,很容易讓觀眾產生一種凝聚力和親切感。于是,在這種共同的文化記憶中,個體很容易獲得一種歸屬感。
有人說,“記憶是一種相生相克的東西,它既是一種囚禁,對流離在外的人是一種精神的壓力,嚴重的時候,可以使人彷徨、迷失到精神錯亂;但記憶也是一種持護生存意義的力量,發揮到極致時,還可以成為一種解放。”[3]作為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民族,中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轉型就意味著某種程度的斷裂與隔絕,意味著某些歷史記憶和文化傳統的喪失。當前,在消費主義的話語體系中,一切都是為了消費而存在。于是,歷史記憶成為消費的游戲,未來也變得虛無縹緲,能抓住的只有當下,只有此時此刻,這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態逐漸演變成一種挫敗感,并導致一種得過且過的享樂主義和懷疑一切的犬儒主義的流行。
在大眾傳媒與消費主義合謀之下,春晚所極力營造的個體歸屬與家國認同成了碎片化的記憶。沒有了文化記憶,沒有了審美價值,沒有了思想深度,懷舊成為時尚流行的商業元素。此時,在溫情脈脈的“懷舊”面紗之下,“掩蓋著一種集體迷戀的巫術”。[4]這正是消費文化的吊詭邏輯。
三、文化記憶的審美符碼編織
戴錦華說,“歷史是一種權力的書寫……而記憶則似乎是個人化的,或者用福柯的說法,是人民在某種意義上對抗歷史的場域,或者說記憶是歷史所不能吞沒、規范的場域”。[5]無論消費文化的邏輯如何強權,作為精神本質的文化記憶是不會被磨滅的。跨入而立之年的龍年春晚已嘗試著用全新的形象來闡釋“聯歡會”的藝術本質,復歸民族國家的文化記憶。
2012年的央視春晚去除了商業廣告植入,改變了政治說教傳統,選用新生代演員節目,打造了敞開式舞臺背景,顯得更溫馨、更親民、更有時代特色。特別是“致敬春晚三十年”這一“懷舊”板塊,用美輪美奐的視覺影像讓人們重新拾起了記憶的貝殼,獲得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共鳴。費翔、張明敏、李谷一、韋唯等相繼亮相,《冬天里的一把火》、《故鄉的云》、《我的中國心》《前門情思大碗茶》、《愛的奉獻》等經典老歌再度響起,勾起了無數人心中存留的美好記憶。當張明敏再度唱起當年那首紅遍全國的《我的中國心》時,整個舞臺瞬間成為蜿蜒盤旋的立體式長城,舞臺依舊,歌曲依舊,演員依舊,不同的是時間變了,舞臺前面的LED屏幕上前后相差近30年的畫面輪回交錯。在蒙太奇般的轉換中,觀眾可以清晰地對比出歲月流逝的痕跡。此情此景,怎能讓人不動容?歌曲唱罷,三位男主持系著和舞蹈演員一樣的紅圍巾,吟唱了幾句歌,還配合默契地把圍巾向后一甩,并附上一個字“帥”,這種歡娛又親切的表現深受廣大網友好評。總起來說,龍年春晚置換了消費、政治、資本等的權力爭奪,留下了那些“接地氣”的真實記憶,盡管還存在很多缺陷,但“能繞回來,終究是好”。[6]
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認為,個體的記憶其實是一種關于文化的記憶。文化記憶的實質已經超越了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的范圍,關涉到人類社會和思想的歷史延續性問題。因為,在文化記憶中,“通過群體成員一起參加紀念性的集會,我們就能在想象中通過重演過去來再現集體思想,否則,過去就會在時間的迷霧中慢慢地飄散。”[7]作為中華民族文化記憶的一部分,春晚已走過輝煌,進入了最為爭議的時期,但是,它依然有著自身不可抹殺的意義和魅力。春晚的未來發展,必須把握住自身獨特的屬性和功能。換言之,春晚的節目不能簡單滿足消費娛樂的需要,還應該增加其文化內蘊,使春晚重新擔負起個體身份認同和民族身份建構、彌補現代人心理和情感需求的歷史使命。因此,我們應該以批評的眼光重新建構起春晚文化記憶的審美藍圖。
注釋
[1].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頁。
[2].西美爾《門與橋》,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第231頁。
[3].葉維廉《雙重的錯位:臺灣五六十年代的詩思》,《創世紀》,140-141期合刊,第62-63頁。
[4].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剛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1頁。
[5].戴錦華:《再現:歷史與記憶——電影中的歷史書寫與呈現》,《中華讀書報》,2012年2月8日第17版。
[6].曾憲皓:《春晚減法的成功》,《南方都市報》,2012年1月24日。
[7].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