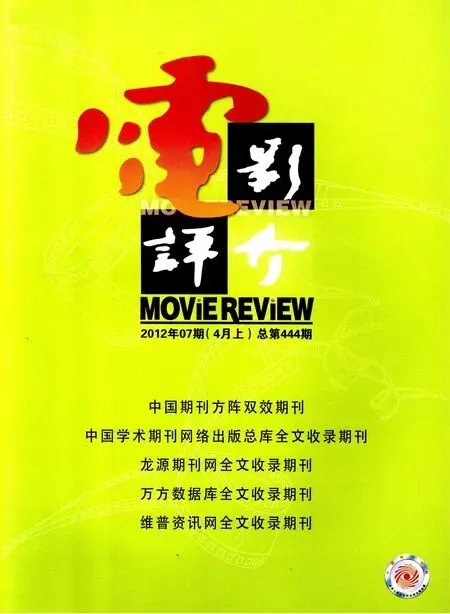畫意攝影的文化背景與情感表達
攝影從誕生之初,就與繪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西方,從高藝術攝影(High Art)到畫意攝影(Pictorialism),再到后來的沙龍攝影,各個流派的攝影家們都竭盡全力試圖讓攝影接近繪畫藝術,不論從拍攝內容、畫面構圖、還是表現形式,甚至挖空心思研究各種照片印相技法來增加其“畫意”的效果,如紙基底版印相、照相凹版、碳素印相法、油彩轉化法、樹脂重鉻酸鹽印相法等,為的是想讓攝影成為像繪畫那樣的真正的藝術,而被藝術界接受。如《美國ICP攝影百科全書》所說:“畫意派運動的先導是19世紀50年代末期雷蘭德和羅賓遜的‘高藝術’攝影。他們的作品像以后畫意派作品那樣深受當時風行的繪畫格式的影響,但他們都曾為攝影取得和其他視覺藝術同等地位而竭盡全力。”
畫意攝影強調直接的拍攝或特殊工藝的制作手法,營造畫意的空間。法國攝影家羅伯特?德馬奇(Robert Demachy)的作品可以說是當時歐洲畫意攝影的最高峰,他主張攝影作品以達到繪畫的意境為最高目標,從而還告誡巴黎攝影俱樂部的同好們要好好研究在美術館和定期沙龍中展出的繪畫作品的表現手法、構圖方式、背景設置及光線運用,并以此作為創作的樣本。美國人斯蒂格利茨在攝影生涯的最初,也與德馬奇的主張類似,他宣稱為達到作為繪畫表現的攝影的目的,以一切手段對底板及照片加以處理都是正當的。諸如此類的畫意攝影家們為了使攝影更具繪畫效果使出渾身解數,其中不乏為了唯美的畫面效果而忽略了攝影的主題和內容的攝影師,就使得有人認為他們的攝影作品“嚴重偏離攝影媒介特性,淪為表面效果的奴隸”。[1]縱觀整個攝影史,我們會發現對于畫意攝影的評價歷來不高,究其原因也始終逃不出題材有限、脫離攝影本質、過分注重表面化而忽略內容價值、不具時代性等耳熟能詳的原因。當攝影術傳入中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和種種質疑,但似乎它和西方攝影的發展過程又是極其類似的。
攝影進入中國的最初,也是被以一種藝術的形式所認識、接受和應用的。如蔡元培所言:“風景可攝影入畫,我們已經用美術的條件印證過,已經看作美術品了。”“攝影術本為科學上致用的工具,而取景傳神,參與美術家意匠者,乃與圖畫相等。”胡伯翔也說:“昔人稱畫之佳者。曰惟妙惟肖。予意用此語為美術攝影之釋意。尤為恰當。”當時的攝影家們自然而然的將攝影與中國傳統水墨山水繪畫與書法聯系起來,展現了中國特有的古老文化情懷和意境之美。中國的文化人非常自主性的將攝影納入自己的文化當中,誕生了如朗靜山、蔡俊三、錢萬里等一大批以攝影術作為媒介的藝術家,深厚的中國文化,在這些藝術家的身上再次顯現了巨大的融合能力和自主性,但他們的攝影主要是模仿古代中國的山水畫,并追求其意境。中國畫意攝影的代表人物郎靜山在1939年以中國山水畫理論為基礎與攝影的特點相結合,創造了“集錦攝影”的獨特技法。但在當時博得滿堂彩,獲得各種獎項以及獲得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高級會士、美國攝影學會高級會士等多項榮譽稱號的他,在當今卻引起了種種質疑和批判,藝術評論家鮑昆的文章《風花雪月一百年》中說“郎氏的攝影嚴格說知識運用了攝影的技術,而沒有攝影獨特的基本特征,即瞬間感和細節記錄的特點。”“郎靜山的‘集錦攝影’從本質上看,應該屬于繪畫性質的美術作品,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攝影”,說郎靜山的作品和“時代藝術前沿根本就不搭界,和現實生活也毫無關系”,即“沒有時代的意義,不過是泥于古意的仿畫情節和逃避現實生活的文人意趣。”說到底,之所以對以郎靜山為代表的中國畫意攝影家們有如此偏激的批判,說它“給后來的中國影人帶來的多是負面的影響”,[2]就是因為他們的畫意攝影作品缺乏時代性和脫離攝影本質,沒有在當時特有的社會背景之下傳達出特有的思想情感。不錯,倘若說剛開始的畫意攝影為追求其表面效果,不論在前期拍攝還是后期制作上都費盡心思,是為了開創一種中國特有的攝影方式,表達一種在中國文人骨子里沉淀了幾千年的閑情雅趣、精神寄托,我們當然不可否認這種獨有的中國式攝影形式。與西方早期畫意攝影一樣,如雷蘭德的《人生兩條路》和羅賓遜的《彌留》,他們所追尋的是西方油畫的質感和效果,而在中國本土,攝影師們模仿中國水墨山水畫也無可厚非。可問題是如何超越這種停留在表面效果的唯美主義,而使其更具攝影價值,一再的重復是沒有意義的。
那就要說到何為攝影本質,“無論從哪個角度理解攝影,攝影本質的命脈乃至最高級的形態恰恰不是‘唯美’,而是‘紀實’——這是從攝影誕生之日起就早已界定的。”[3]對攝影家來說,追求畫面的唯美效果并沒有錯,問題是不能僅僅停留在這種表面化的形式主義上。形式固然是重要的,而要使作品深刻,有價值,就必須使這種“形式”富有“意味”,正所謂“有意味的形式”。將紀實與畫意結合,用“畫意”的表現形式去“紀實”也未嘗不可,揚長而避短,用更美的畫面效果、視覺感受去表達作品的主題、思想和情感,使作品更易于被接受和認可。陳復禮的“影畫合璧”雖然引起攝影界的許多評論和爭議,批評聲也不少,有些再次用繪畫來提升攝影的藝術地位,用繪畫的角度來評判攝影好壞的回歸偏頗思想之嫌,但其將紀實與畫意相結合的想法和實踐還是值得人們借鑒和學習的。正如他所說:“我搞影畫合璧,除了創新,還有一個意思,就是通過攝影與繪畫聯姻,來提高攝影藝術的地位,從而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為畫意攝影開辟一個新天地。當然,這只是一個嘗試。后來,我還是從攝影的特性出發,在攝影的構思與拍攝上下功夫,把主要精力放在從大自然、從社會生活中攝取真景實情,并嘗試把中國畫意與西洋畫意結合起來。”
如果說陳復禮的攝影作品還有違背攝影本性的地方,那黃貴全近年來的作品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全新的角度去認識畫意攝影,它呈現出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繼承與創新。“黃貴權先生沒有簡單地以攝影術對中國古典畫意進行表面模仿,他恰恰是從攝影媒介的本體性出發,創造性地將中國古典畫意中的一些思維方式放進極具攝影性的表達中。他的作品既有攝影本體美學特征的表達,又有一個深諳東方視覺藝術思維的藝術家的個性。他以多重曝光的純粹攝影技術,營造一個虛實相間、充滿動感的惟美意象;他以超常焦距攝影鏡頭制造的虛幻效果,營造了類似中國古典繪畫潑墨大寫意的粗獷感覺。近年來,黃貴權先生的實踐路向,也恰恰像一個中國古典畫家對現象處理的變法過程。他前段的影像,自由快意,跳躍奇幻,但略有些強調技巧的感覺,但最近的‘英雄樹’系列,則越發顯得直抒胸臆,質樸和單純,跨越了技術技巧的思維屏障,進入一種大巧若拙的境界。黃貴權先生的藝術,也回答了東方藝術在攝影,這一現代性媒介中如何重新獲得生命力的問題。他的藝術,是值得關注的現象。他也自然成為人們必須關注的人物。”[4]
所以,我們不能以固有的眼光和視角去審視和評判畫意攝影,唯美的畫面效果是它的優勢,但這并不妨礙其用紀實的功能去反映社會、生活、風景、人像,也并不能阻止其視野的廣闊度,更不影響其思想情感的表達和傳遞。我們得在繼承和運用好它的優勢的基礎之上,使拍攝的內容更加豐富、自然、深刻、具有時代感。也可以運用它固有的手法,譬如柔焦拍攝、在拍攝時晃動相機來營造畫面的氛圍,還可以運用當下一些創新的但仍屬于攝影本性的技術手段來強調攝影作品的中心思想、情感沖突,如多重曝光、慢門拍攝、虛化焦點等。從而使攝影作品不但具有紀實的特性,內容豐滿,同時又表達出了作者的思想情感、立場觀點,而且在畫面效果上又不缺乏其美的感受,這不正是我們所追求的嗎?
注釋
[1]顧錚:《世界攝影史》,浙江攝影出版社,2006.7,P33
[2]鮑昆:《觀看?再觀看》,中國文聯出版社,2009.9,P92
[3]林路,《攝影思想史》,,浙江攝影出版社,2008.3,P69
[4]鮑昆,:《中國攝影》,[J],2008(2)
[1]顧錚,《世界攝影史》,浙江攝影出版社,2006.7
[2]鮑昆,《觀看?再觀看》,中國文聯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3]林路,《攝影思想史》,浙江攝影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4]鮑昆,《中國攝影》,[J],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