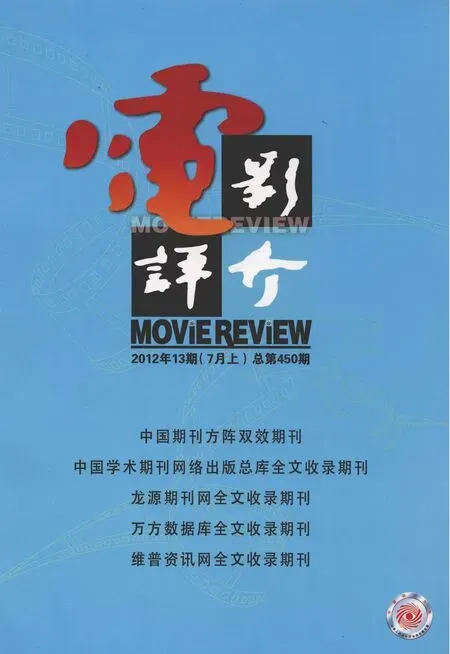電影藝術在二十世紀后期美國社會的變革
一、“新好萊塢”與二十世紀美國社會
“印刷術的發明對書寫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但是并沒有改變散文與詩歌的性質。新的樂器對音樂的影響比較復雜,但工藝方面的變化并沒有產生關于音樂藝術的全新概念。留聲機讓千百萬聽眾聽到了錄制下來的聲音,但演奏還是老樣子。”[1]
——霍華德?勞遜
從1895年盧米埃爾兄弟拍攝的“火車進站”中活生生影像畫面將觀眾嚇得驚惶四散開始,電影在人類紀實工具的發展史上展現了劃時代的意義。電影的誕生,作為“自然造物的補充,而不是替代”[2],使物質現實的空間形式得以復原。從而,使人類又一次獲得了一種全新的感知世界的經驗,獲得了一種全新的影像思維的方式。
進入二十世紀后,電影業高速發展。在法國“新浪潮”等電影運動的沖擊下,美國好萊塢電影于六七十年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于是便有了我們現在所稱的“好萊塢黃金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的電影廠系統破裂。麥卡錫時期的反共主義和電視等媒體的普及極大地縮小了電影的文化力量。而在六十年代由于人們對越戰保持著不同的態度,美國政治文化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民權運動頓時風起云涌。少數種族群眾為取得應有的社會地位和權利而斗爭。這一切動搖和化解了美國意識形態共識的社會基礎。直到越戰時期,好萊塢電影的主要創作思路源頭仍為70年代黃金時期的電影,這些電影將民族神話和意識形態非神秘化。無論是外星人,機器人還是諸如印第安那?瓊斯那樣的孤膽英雄都充滿了關于民族神話、夢幻和思想的比喻性內蘊。美國電影業借以諸如喬治?盧卡斯的星球大戰系列等“美國夢”題材電影或個人英雄題材電影來逃避美國社會經歷了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越戰失敗后“垮掉”一代給美國主流社會文化帶來的影響及創傷。1970年的“水門事件”更是讓美國議會有史以來第一次彈劾了他們的總統。民主政治,戰爭政策和民權運動形成了當時美國社會政治運動的三大潮流。新好萊塢電影運動便誕生在這樣一個“社會動亂、民主危機的時代”,其社會和政治的原因是無法回避的。
20世紀后期,美國社會主流文化開始停滯不前并出現了文化斷層,這一現象在里根時代最為突出。許多人對于歷史含義出現了分歧的意見。許多社會科學家認為,為了使社會凝聚在一起,當今的人們需要將現實社會進程與過往的歷史發展進行比較,而不是僅僅對當下社會進行感性分析。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認為,對歷史的記憶只能通過閱讀、聆聽或者通過節日紀念活動被撩撥起來,由社會機構存儲和闡釋過去的歷史。于是,在這一段時期之后,好萊塢的電影制作人開始不僅關注電影的商業價值,也關注歷史的題材在電影中的展現。對歷史的回憶與反思開始逐漸成為電影文化力量的試金石。
二、歷史元素對美國二十世紀后期電影的影響
“起來,否則就永遠沉淪下了!”
(《彌爾頓詩選》,彌爾頓(英),第一卷)
90年代初,許多好萊塢電影制作人從開始在他們的電影中試圖加入歷史這一元素。例如奧立弗?斯通在90年代初拍攝的電影《J?F?肯尼迪》中試圖探索肯尼迪事件的真相并暗示其美國高層政治斗爭直接導致了這一悲劇事件的發生的可能性。再如史蒂夫?斯皮伯格根據英國布克獎同名獲獎小說改編拍攝的《辛德勒名單》則通過主人公的經歷重現了納粹大屠殺這一歷史真實事件,這部電影講述作為德國工業家的主人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軍團企圖滅絕猶太民族的行動中拯救了一批猶太人的故事。這些電影試圖重現對歷史的回憶與反思的行為是90年代電影重新界定一個更為廣泛的文化言語的重要嘗試。
正如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塞托提出的觀點,“對于歷史的了解不僅僅是個人研究的結果,也不僅僅是對過去的‘現實’的再現,那是‘一個地方的產物’。而對于奧立弗?斯通來說,越南正是他心中的‘那個地方’”。1965年,奧利弗斯通帶著對外面世界的無限遐想從美國耶魯大學退學,隨后前往西貢中國城當英語教師。在越戰升級后他積極參軍,但令他深感震驚的是當他終于離開戰場回到祖國,卻發現許多美國人和曾經參戰的老兵均對戰爭十分冷漠。驚訝之余,他決定要嘗試探索美國社會的政治動向,于是懷著電影制作人和編劇的夢想走進了紐約大學電影學院。
1976年,他根據自己的參戰經歷撰寫了后來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電影《野戰排》的初稿。轉年,他改編了海軍陸戰隊老兵羅恩?科維克的自傳《生于7月4日》。在《野戰排》取得的成功的基礎上,斯通拍攝了由年輕的湯姆?克魯斯出演的《生于7月4日》。如果說《野戰排》與一群人有關,那么《生于7月4日》便是與整個美國民族有關。正如在阿基琉斯與普里阿摩斯的交談中,荷馬所展現出人性中至高的憐憫以及奧德修斯在艱險旅途中展現出來的對家庭的忠誠一樣,《生于7月4日》通過一個愛國青年因為受其母親影響,成為一個如大衛?里斯曼所謂的“外向型”的人物并積極參加越戰,最后受傷癱瘓后開始反思戰爭的故事來勾勒出越戰士兵內心的空虛與惆悵并反思戰爭的意義與其帶給人們的心靈創傷。
斯通后來在影片《J.F.肯尼迪》中則試圖從另一角度闡釋這場戰爭。根據導演描述,他在拍攝前無意看到了一些資料,這些文件表明J.F.肯尼迪被謀殺期間,正計劃從越南撤回美國的軍事力量。這無意中的發現使他陷入沉思。如果肯尼迪沒有被謀殺,也許就不會有那么多士兵戰死沙場。
“電影唯一能做的就是使時間的流逝變得甜美。它給人做伴,讓我們的生活稍微好一點,那就是好電影、好詩的作用。它不能改變世界,人才能改變世界。你知道人多么經常地嘗試改變世界,同樣的故事一次次重復,最終他們總是犧牲品,幾代人迷失其中。”
——西奧?安哲羅普洛斯
注釋
[1]霍華德?勞遜 《電影的創造過程》
[2]安德烈巴贊 《電影是什么?》
[1] Charles L. P. Silet《O liver Stone:Interviews》[J]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 鄧亞玲 胡濱《外國電影史》[J]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5(07)
[3] 王恩銘《當代美國社會與文化》[J]上海外語教育 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