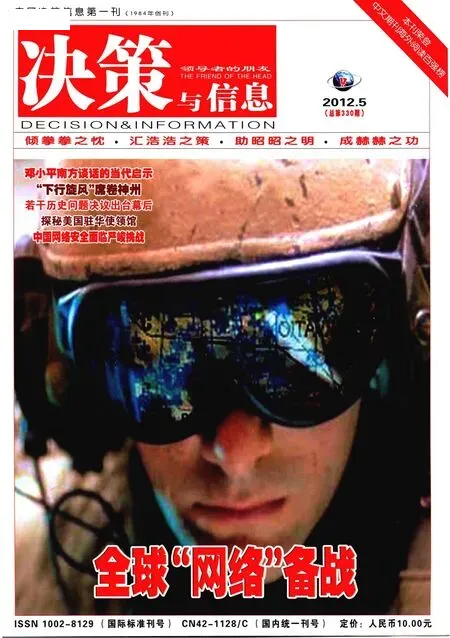謠言:清末革命黨的政變利器
文/瞿駿
辛亥革命作為一個扭轉歷史、牽涉極廣、影響久遠的大事件,與之相關的人與事,百年后看來都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感,更何況當時那些身處時勢劇變之中、茫茫然不知未來將向何處去的困局中人。從辛亥八月到壬子二月間,中國幾成一充斥著謠言的“八卦世界”。吳宓就感慨:“吾輩今日處此,如在夢中,外間真確消息毫未聞知,實為不妥之至。”葉圣陶也覺得當時各類消息互有異同,莫衷一是,真假難辨。
報紙公開“造謠”
從洋務運動開始,中國現代轉型之路已走了五十多年,上海、廣州、北京等大城市開始成為全國的新聞中心,并與歐洲諸國間的信息流動接軌,其中最重要的中轉傳播渠道當然是新興的電報。不過就國內新聞而言,各報往往把最強力量放在本地和北京,其余僅是在重要城市設置一二訪員,且薪金微薄,消息的可靠性很難得到保證。而就國外新聞而言,當時即使是路透社電也不會直接送中文報紙,中文報紙要發布其新聞需要從西文報轉譯,更無論其他外國通訊社。
正因辛亥時期的報紙如此運作,謠言也就從空隙中生產出來。以當時報紙的集中地上海為例,《時報》、《申報》、《新聞報》、《民立報》等大報報道革命的重要形式就是來自全國各地乃至東京、柏林、巴黎、倫敦等“寰球世界”的電文。表面上看,這些電文來源廣泛,讓讀者足不出戶即能知道革命形勢,而實際上其中卻充斥著各種不可深究的謠言。像一外國通訊社憑道聽途說就發新聞說荊州、沙市等地滿人屠殺漢人,“慘狀”不堪目睹。宋教仁、徐血兒等革命黨人馬上跟進炒作,利用其大做文章來鼓吹反滿的急迫與必要,而假裝對此消息來源的可靠性一無所知。
“民賊”亦是當時謠言的一大主角。革命后沒幾天,袁世凱在《民立報》北京專電中已被俠士所殺。據守南京、縱兵殺人的江南提督張勛則在南京專電中被路人看見手持人心購買豆腐,然后以油煎之,下酒甚樂。
在滿人和“民賊”被全面“污名化”之際,革命領袖則在報紙電文中被塑造出一個又一個的神話故事。來自東京的電報就說黎元洪在甲午戰后游學日本時即成了革命黨,且在好幾年前已擬定了起事文告。
無論是滿人、“民賊”的“污名化”,還是革命領袖的“神話化”,都是革命正當性來源的一個層面。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層面,就是塑造“國際觀瞻”。
在清末,稍大的政治變動都脫不開洋人的幕后推手。武昌起事后,革命黨擔心的一大問題就是列強是否承認,因為如果不承認,“革命足招瓜分之禍”的擔心將愈演愈烈。在國家主權完整基本已成時人共識的情況下,這種擔心對革命的正當性傷害尤大。
從當時的“友邦輿論”看,各國實際上對革命支持與反對互有。蔡元培、章士釗等人在國外不斷“發明”有利于革命的電文、譯稿,以借此向公眾塑造革命獲得列強認同與支持的印象。
在德國,革命剛起,蔡元培就試圖發電給上海報館,大意謂“外國均贊同吾黨,決不干涉,望竭力鼓吹,使各地響應”,后又加入“孫文舉袁世凱為總統事”。為何蔡氏添加孫舉袁為總統這樣屬于空穴來風的故事呢?據他分析:
孫之推袁,確否固不可知,然此等消息,除離間滿、袁之外,于半新半舊之人心極有影響。外交亦然,如德國政界推服袁甚至,……請公(吳稚暉)以英文電示此訊,并勿參疑詞,以便傳示德報館,易于取信。(《蔡元培全集》第10卷)
在英國,章士釗則奔走往返于住所與電報局,剪貼整理各大報紙關于革命的報道,“擇議論之袒己者”,每日一電或數電發回上海,這樣的電報往返足足堅持了一個多月。

張勛

蔡元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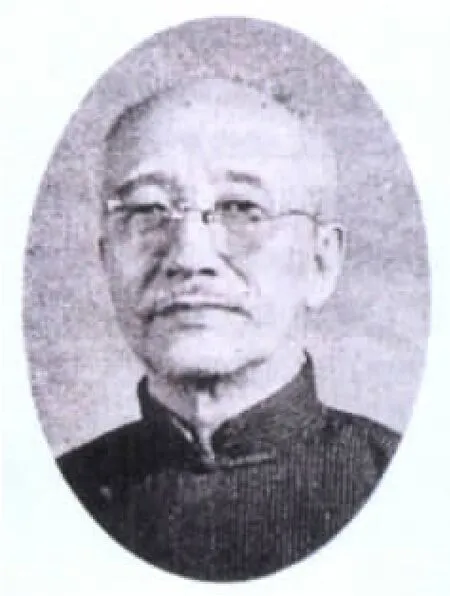
章士釗
革命狂熱催動謠言傳播
大城市里的公共空間和消費市場則是當時謠言制造與傳播的第二個溫床。辛亥革命時各種各樣的政治集會都會在馬路街道、開放私園、民間會所等城市公共空間中舉行,這些集會的演說、誓詞、講話很多都意在激發革命狂熱,灌輸革命已取得巨大進展,并一定會取得最后成功的理念。如1911年11月24日宋教仁在廣肇會所募餉會議上通報湖北情形時,基本不提北洋新軍已大兵壓境,而是宣布武昌“軍精餉足,可支十年”。12月2日張園募餉大會議,袁恒之則言之鑿鑿前幾天漢陽失守消息乃是傳說,即便“地方或有暫時之疏虞”,但“我漢族四萬萬同胞之心終不失守”。
這些前后矛盾、含糊其詞、夸張失實的言論,會依托公共空間產生,經由紙媒放大,由謠言而變成被聽眾所接受的真理,最后竟然發展到報館發布真實消息就被暴民搗毀的程度。馬敘倫就回憶:
袁世凱叫馮國璋攻破了漢陽,上海各報不敢發表,因為那時人民寧信《民立報》為宣傳捏造的消息,而對于真實的如革命軍失敗的消息,就會打毀報館的,《申報》、《新聞報》就被打過。(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之前》)
城市中發達細分的消費市場則讓政治與生意紛紛掛上了鉤,其中最多的就是各類書籍的出版。這些書的內容中謠言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如“民賊”張勛的各種丑史、野史就在那段時間大量出版,連其愛妾小毛子也能夠“博得新書賣幾文”。明明學社就出版有《小毛子傳》,書中夸張地寫道,張勛七十三歲,小毛子卻年方十五。
更有一則匪夷所思的小毛子軼事廣為流傳:南京光復后,小毛子未能和張勛一起逃走,被革命軍捕獲。此事立刻吸引了各方注意。上海軍政府都督陳其美就建議把她押解到上海,陳列張園,任人參觀,每人收門票四角,以提充軍餉。此事真假如參照《申報》新聞,基本可確定為謠言。不過,顯然在城市公共空間革命狂熱氣氛的催動下,人們更愿意期盼的是小毛子在萬人前的公開展覽。
“狼來了”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發展不平衡,在現代轉型進程中已漸漸形成了以沿海口岸城市為主體的“洋世界”與以廣大內陸城市、鄉村為主體的“土世界”。“土”、“洋”世界間觀念與信息的落差也催生了革命中的謠言。
很多時人都在武昌首義后立即把革命偉人與神秘的《推背圖》、《燒餅歌》聯系在一起,像黎元洪就被發揮為“元洪”兩字隱含元末朱洪武崛興之意。身處廣東梅縣鄉間的黃藥眠則聽說孫中山法術高強,在被清兵團團圍住、看似難以脫逃之際,卻腳踏祥云騰空飛走了。
對那些在革命中有天下社稷、身家性命之虞的官員來說,每個事關時局動向的謠言,都是極大的刺激。郭沫若就認為像川督趙爾豐這樣的倔強之人,到11月25日居然把成都和平移交出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訊息隔絕,他只能相信報紙上清廷已經滅亡的消息。
辛亥革命時期,謠言的制造與傳播一方面確實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起到了積極作用。章士釗就對其剪貼整理的電文頗為自得。連對手方也承認謠言的作用,說:“此次共和之成立,新聞記者實與有大功。譬如報告南軍如何精強,如何雄猛,如何眾多,鋪揚厲。”
但另一方面,這亦是一把雙刃劍,過多謠言震動了人心、時局、社會,使得“好亂者皆從而和之”,最終產生了“狼來了”效應。壬子中秋上海某地僅僅因為士兵聚談,“人聲嘈雜,旋即走散”,就馬上傳出謠言說軍隊今晚要嘩變索餉,全城氣氛頓時異常緊張。謠言的“制造”也改變了清末尚算不錯的言論生態,而變得黨同伐異,漸失底線。于右任就觀察到辛亥革命后“發一言,論一事,異黨以政見不同而爭,同黨以意見不合而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連篇累牘地利用報紙來散播謠言,攻擊對手。此種歷史發展的吊詭曲折頗令人深思,也很讓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