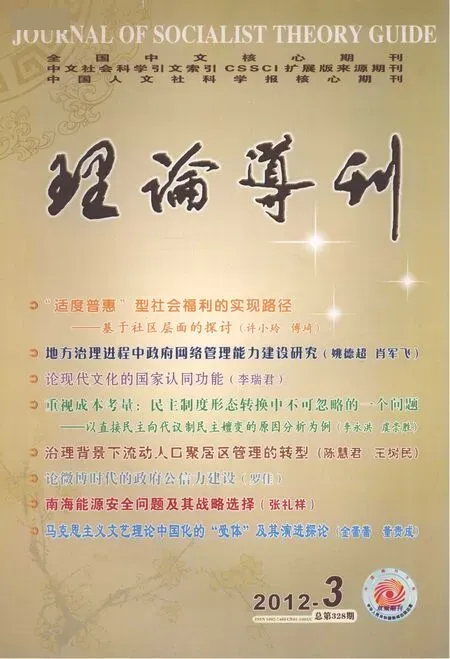環境與心靈的雙重救贖:環境危機的人性之維
劉建濤,賈鳳姿
(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大連116026)
環境與心靈的雙重救贖:環境危機的人性之維
劉建濤,賈鳳姿
(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大連116026)
環境危機表面上看是工業化發展的產物,其實質是人性異化的惡果。人性異化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及人與人關系的異化,而這兩種關系的異化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對自然資源的透支與對自然的污染。人性危機得不到拯救,環境危機就無法根除。馬克思最注重人性的解放與發展,指出人性解放的根本途徑在于破除私有制與掌握人性的活動規律,過與自然規律相協調的生活;我國的傳統文化也是以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為目的,這對于遏制人性異化有著特殊的重大意義。
環境與心靈危機;人性異化;拯救人性
馬克思認為,社會一切變遷皆在人性之中。環境危機表面上看是生態退化、環境污染與資源短缺,實則是人性對自然的惡,是人失去自己是其所是的規定性所導致的惡果。因此克服環境危機的根本途徑在于把人性從異化中解放出來,掌握人與自然及人與社會的整體規律并以其指導人們的實踐。
一、馬克思對人性的界定
什么是人性,這是千百年來人們一直追問卻又難以解答的問題。有的學者從物理學、化學、心理學的視角切入,把人性歸結為物理的性質、化學的性質、心理的活動,然而這些都缺少說服力。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而理論的徹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馬克思正是從研究人本身入手,揭示了人的本性。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神圣家族》、《資本論》中多次提到“合乎人性”、“適合人性”,并對人性給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指出:“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于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1]57可見,馬克思認為人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即勞動、生產、實踐。這一見解是基于對勞動的闡述,正是在人與動物的對比中,馬克思正確揭示了人性。動物也生產,但是它的生產是片面的,直接受肉體支配,只生產自身;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甚至不受肉體支配,生產整個自然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之所以是人類區別于一切動物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人的生產是自由、全面、有意識的,而這種創造性的生產是以屬人方式與自然打交道的,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是對人的本質與生命活動的全面占有。然而建立在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勞動基礎上的人性,具體到實際生活中,只能在社會關系中得到體現,“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說來才是人與人之間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1]83而勞動是不斷發展的,社會關系也是不斷發展的,所以人性也隨著勞動、社會關系的不斷發展而具有了具體的社會歷史性,也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2]但人性的私有制的社會現實決定了人性還不能立即實現它的本質,即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而是出現了異化,自由自覺被扭曲了,勞動背離了人性,成了精神和肉體痛苦的根源,人的感官不再是人的。馬克思正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剖析,敏銳地洞察到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對人性的扭曲,所以,提出了“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1]81及人的解放和發展的任務,并把共產主義作為這種回歸和解放的有效形式。因此,人性的回歸和解放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出發點和歸宿,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價值訴求。
二、環境問題的人性透視
馬克思揭示了由于私有制的社會現實導致了人性異化的規律。而人性包含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包含了人與社會的關系,人性的異化直接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及人與社會關系的異化。這兩種異化關系把人性鎖定在對物質的過度追求上,從而對自然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
動物的生命活動和它自己是直接統一的,而人則把本身的生命活動變成了自己意識的對象,生命活動成了完成意識活動的手段,自然更不例外。人性的異化,即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的異化首先表現為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因為人在勞動過程中首先發生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對自然物的占有被定化為“只有當它為我們擁有的時候,就是說,當它對我們來說作為資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們直接占有,被我們吃、喝、穿、住等等的時候,簡言之,在它被我們使用的時候,才是我們的”,[1]85人對自然的享受被理解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對自然物占有的這種態度導致了自然的工具化,自然只是滿足我們占有欲望的工具、材料,這種片面的、扭曲的實踐把人的貪婪的欲望和利己思想激發到了極致,造成了對自然無節制的逆生態的開采。印度之父“圣雄”甘地指出:“地球能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但不能滿足每個人的貪念。”[3]個人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占有、爭奪更多的有限的資源,結果導致了資源的枯竭。對于維護共同的環境,人人為了利己普遍存在著“搭便車”的心理,結果導致了“公地悲劇”,致使環境保護陷入了“囚徒困境”。這種情況體現在國家之間、民族之間、階級之間帶來的后果就更為嚴重,造成了生態殖民主義。作為環境污染重要來源的發達國家,通過把污染嚴重的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把工業廢物傾倒到發展中國家的手段來緩解本國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而同時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則加重并惡化了。另一方面,貫穿于西方文化和哲學史中的二元論通過背景化和對依賴性的否認、工具主義和對象化以及同質化和刻板化的手段徹底地把人與自然分割開來,摧毀了人與自然的任何關聯,造成了兩者之間的真空地帶。以相互對立和相互排斥為基本特征的二元論的邏輯結構,構成了反自然文化價值觀念的前提假設,奠定了工業文化的思維框架,塑造了主宰西方的文化模態。這種理論造成并進一步加重了自然觀、價值觀、發展觀、道德觀的二元性,認為自然不是道德關懷的對象,沒有價值。西方文明正是用道德的二元論把自然工具化為服務于人類目的的手段。貪婪的欲望和利己思想與建立在二元論的邏輯結構地基上的反自然的文化價值觀念相互強化,相互凝固,最終自然界對人的豐富的關系被單面化為純粹的有用性,導致了對自然的非可持續的利用模式,導致了自然的不可持續性及社會的不可持續性。
馬克思始終從人與人關系的維度考察人與自然的關系,認為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根源于人與社會關系的異化,即私有制。“所謂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異化,是指人類在改造社會的同時,創造出不完全合理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社會體制,它們破壞社會的和諧,損害人類利益,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甚至成為敵視人類的異己力量。”[4]這種人與社會的異化主要表現為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異化。以利潤最大化為內在邏輯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所形成的發展模式的確創造出了巨大的財富,但這種財富的創造是以資源的快速枯竭和環境的嚴重污染為代價的,且這種畸形發展模式以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為基本特征,呈現出單向流動的特點,不可能顧及到自然的環境容量和生態規律,呈現出反自然擴張的態勢。因此,這種高投入、高消耗、高環境影響的生態不道德的生產發展模式從本質上講是不節約、不環保、不可持續的,經濟只能在榨取資源和污染環境中增長。不幸的是,改革開放后主導我國現代化的邏輯或范式依然是西方式的,即沿襲了西方傳統工業文明的價值取向、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將制度優越性寄托于經濟高速增長的“趕超戰略”上,忽視了生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造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破壞了支持生命系統的生態的平衡。可以說,人口基數大、人口絕對量持續增長與人均資源少、環境容量小、生存空間小及偏離國情的發展模式緊密地糾纏在一起,日益沖擊著我國環境的承載能力與極限。人的消費方式與生產方式密切相關,有什么的生產方式就會有什么樣的消費方式。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中,生產以利潤增值為核心,而不是以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為追求。異化的生產方式背離了需要的基本要求,從而也導致了消費背離了需要,消費的功能發生了質變,已不再是滿足人的基本需求的手段,而成為了滿足人的貪婪、欲望的工具,追求奢侈、揮霍性消費與渴求無節制的物質享受成為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價值,成為人們獲得地位、自由和理想的精神假象。消費主義者的人生格言就是:我買故我在。而這種追求無限欲望滿足的消費方式反過來又成為經濟繁榮發展的保證。在這種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控制體系里,人日益失去了批判性的思維,日益成為單向度的人,結果出現了經濟增長與道德墮落、精神空虛的“二律背反”現象。這種異化的消費方式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對自然資源的透支和對自然生態的污染,致使全球生態環境指數不斷下降,生態足跡指數日趨攀升,生態赤字日益擴大,甚至威脅到了人的生存。正如《21世紀議程》指出的:“全球環境問題不斷惡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尤其是工業化國家的這類模式。”[5]其實馬克思早就告誡人們:“如果人的需要長期在物質享受層次上停留,就會產生惡性消費和惡性開發,從而破壞環境也摧毀人自身。”[3]
三、拯救人性,諧和人與自然的關系
人類活動的自由性被私有制的社會現實扭曲了。在這樣的社會里,人性被貪婪、欲望所牽制,需要被鎖定在對物質的過度追求上,結果就是人的過分物質化,唯物主義成了拜物主義、拜金主義,從而導致了對自然的不道德的無節制開發,忽視了自然的承載極限和可持續性,產生了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可見,外在具體環境和人類生態危機實質是心靈危機或人性危機及其外化。因此,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的路徑就在于對環境和心靈進行雙重救贖,醫治心靈無節制欲望,醫治人性扭曲、異化。
馬克思最注重人性的解放與發展,并把它作為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出發點與歸宿。正是透視到私有制特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下人的生存狀態及人性的異化,馬克思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及私有觀念的深刻批判,以使社會真正成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1]83除此之外,人對人本身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整體規律認識不足,認為對自然、對物的占有就是直接地使用,即吃、喝、住、穿,這樣從人性的高度來看對物的占有越多就越不自由。因此,馬克思對于人性的解放開出的藥方是消滅資本主義,而消滅資本主義的關鍵是消滅資本。資本是一個歷史范疇,是創造剩余價值的價值,是資本主義社會賴以建立的基礎。但資本的消滅靠強制力是無法實現的,只能靠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來消滅。此外,馬克思還主張人應該過與自然規律相協調的生活。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的理論表明:人與自然是互嵌式的整體,是自然的人道主義和人道的自然主義的統一,是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的統一。正是在人與自然動態的相互創造中,人們“中介、調節和控制著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6]保持著人與自然生態之間的平衡,從而使人借助于自然使自己的整體生命得以體現和對象化并使人—自然結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1]56但人“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1]88人必須變革自然、人化自然,不斷地使“自然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在這一過程中,近代工業雖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卻在對立中思維,把人與自然分裂開來,造成了全球性的污染和生態危機。但人除了要遵循社會的規律,還要遵循自然界的規律,因為社會經濟本質上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只按照人的尺度而不顧自然的外在尺度或只按照合目的性而忘記合規律性地變革自然必然會造成生態的失衡。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這無論對外部自然的規律,或對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律來說,都是一樣的”。[7]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人與自然或環境應該也必然地是這樣一種狀態:以人為核心的人天和諧整體。這一和諧整體不是自然的復舊,而是按照人的類本質的發展規律建立的人化自然,是“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1]81的統一。
我國的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張允熠教授在《試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學脈淵承》一文中用詳細的史料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我國傳統文化內在精神的融通性。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指出:“辯證唯物主義淵源于中國,由耶穌會士介紹到歐洲,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一番科學化后,又回到了中國。”[8]因為我國的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一樣以人為根本研究對象,從研究人體生命活動尤其是人的精神活動發展起來的,屬于人文文化,以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為目的。這對于當今人性的解放及重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國的傳統文化主要以儒釋道三家為主,在天人關系上三家都主張“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在欲望上都主張要克制。道家認為“道”以化氣以生萬物,“德”蓄養萬物,并具有“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本性即玄德,從而使宇宙呈現“生生不已”的生機。故應循“德”修“道”,以達“物我同觀”、“人我同等”的境界。用今天的環境語言來說,就是要與自然和睦相處,遵循自然的規律并用這樣的規律去作用萬物以利其生存,以成其生生不息之象。這樣自然就成為了人的生命體驗的對象及修德的內在要求,人與自然達到了高度的和諧。老子主張約束抑制自己的欲望,主張“知止知足”,反對以世俗的價值觀念進行無節制的消費和鋪張浪費,認為過多的物質享受會使人心志迷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9]認為人應去奢崇儉,因為儉才能“無欲”,“無欲則剛”,節儉可以使人的心態保持穩定寧靜,剛而不阿。道的自然之性在社會的人身上體現為“中和之性”,它是“道”在人這一道的具體表現,而這恰恰是儒家所關注的。獨處時要達到“中”的要求,寂然不動;與自然界的事物作用時要達到“和”的要求,感而隨通。“和”是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的統一,單獨地從一方面出發,必然會造成人在自然面前消極無為或人奴役、控制自然。故,儒家主張“仁民”而“愛物”,進而“民胞物與”。同時強調在社會實踐中要注意用“禮”來克制“人心”(私欲),即“以禮制心”,認為“禮”是對人欲的約束,是維系人類群體生活穩定的必要條件,是秩序。佛家認為,宇宙本身是一個巨大的生命之法的體系,生命不只存在于生命體之中,而且還會以潛伏的狀態存在于無生命物當中,宇宙的變化具有產生生命的力量,并且提出了“依正不二”的思想。“依”即“依報”,就是指自然環境,“正”即“正報”,也就是各種生命主體。就是說生命主體的存在是要靠自然界的健康存在來維持的,人類只有和自然環境融合,才能獲得自身的發展。并把人生“三毒”——貪嗔癡列為我執的范疇,認為我執是煩惱之根,證佛之障,極力主張通過“掃三心”(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泯四相”(人相、我相、眾生相、壽者相)來破除我執,破除人的貪欲、邪欲,并進一步破除法我執,以跳出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外,獲得真正的自由。儒釋道三家在天人關系上都以非二元論的思維方式看待人與自然,都主張克制欲望,可見,華夏文化從來以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為圭臬,信奉道法自然,遵循自然法則,追求天人合一,關注生命的安全和文明的延續。這就是五千年的華夏文明留給我們精神上的也是世界的豐富遺產,它是解決當代生態危機、超越工業文明、建設生態文明的文化基礎。
正是基于以上認識,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黨又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在繼承我國優秀的環境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的要求和我國的實際,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生態文明等一系列新理念,倡導可持續的綠色消費,著力構建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以人為本”、“和諧”、“可持續發展”已成為黨的新的政治思維理念。我們須使這些反映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新理念掌握群眾,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在大力發展生產力中逐步促進人性的發展,推動我國環境問題的解決,以完成黨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2.
[3]顏孟堅.當今人類反思的若干問題[EB/OL].(2006-04-0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14c060100039c.html.
[4]王鳳珍.人類理性的重建─—環境危機的哲學反思[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5.
[5]尹貴斌.反思與選擇:環境保護視角文化問題[M].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116.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7.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
[8]竇宗儀.儒學與馬克思主義[M].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2.
[9]邱岳.道德經注評[M].北京:金盾出版社,2010:34.
C912
A
1002-7408(2012)03-0040-03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文化學視域下我國環境問題根源及對策研究”(10YJA850018)的階段性成果。
劉建濤(1983-),男,河北邯鄲人,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賈鳳姿(1956-),女,山東嘉祥人,大連海事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碩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
[責任編輯:宇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