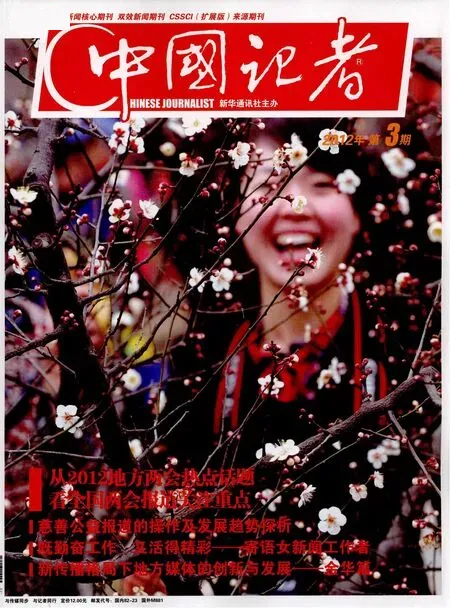正業(yè)之外,活得很“業(yè)余”
□ 文/陳娉舒
(作者是《中國(guó)青年報(bào)》文化閱讀周刊主編)
每一個(gè)“ 忙DAY(Monday)”都很精彩
“如果我總在不務(wù)正業(yè)地刷屏,那是因?yàn)槲艺凰^的‘正業(yè)’折磨著。”
2月19日,周一下午,上傳了這條微博。那時(shí),我正在為幾篇編不下去的稿件著急。都是當(dāng)編輯做記者的,你有沒有這樣的感受:每當(dāng)稿件編不下去或?qū)懖幌氯ィ蝿?shì)所需你必須繼續(xù)與之對(duì)峙與之周旋,你會(huì)不會(huì)一遍遍從第一段第一句開始,反復(fù)地?fù)炱鹚磸?fù)地從頭再來?——沒錯(cuò),我總是在那樣一個(gè)糾結(jié)的狀態(tài)下干著各式各樣的活兒,或編稿,或?qū)懜濉]辦法,誰讓它是咱的“正業(yè)”呢。
我所在的《中國(guó)青年報(bào)》“文化周刊”和“閱讀周刊”,每周二見報(bào)。每周一是出報(bào)日,這一天可謂“戰(zhàn)斗日”。每到周一,最怕有人找,最怕接電話和短信。咱們都明白,“報(bào)紙質(zhì)量大于天”,編稿一分心,影響質(zhì)量不說,還可能隨時(shí)出錯(cuò),而編稿進(jìn)度哪怕耽誤一分鐘,拼版工、制圖工、檢查組、分管領(lǐng)導(dǎo)、核查組,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都將因你的耽誤而延誤,這在報(bào)社出版流程里是不被允許的。就這樣神經(jīng)高度緊張地一路忙到夜里。我的周一,被朋友們戲稱為“忙DAY(Monday)”。
新一輪“戰(zhàn)役”,從每周二開始:已經(jīng)見報(bào)的選題,總結(jié)得失;尋找適合新一周的選題;已布置下去的報(bào)道,繼續(xù)催促,同時(shí)尋找添加新素材;一些有“雷區(qū)”的選題,需“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時(shí)刻留意有無紅牌叫停,同時(shí)籌措備稿……對(duì)我來說,生活,就是一個(gè)七日接著又一個(gè)七日。
進(jìn)中青報(bào)的時(shí)候,我不滿22歲,如今已邁入不惑,在一家報(bào)社待了將近19年,把“編輯—記者—編輯”這兩個(gè)角色顛來倒去地輪番做了十幾年,如果我說我沒有職業(yè)倦怠,那一定是大瞎話。因此,問我“女記者如何活得精彩”?我挺懵的。周而復(fù)始的組稿編稿編版,一周周一月月一年年,還有精彩可言嗎?尤其是,何謂精彩?我眼里的精彩,是否是你眼里的精彩?生活觀、價(jià)值觀不同,精彩的定義必將大相徑庭。
好在,人到中年,看清了一個(gè)道理:面對(duì)別人,最好別太拿你自己當(dāng)回事,你并沒有你年少輕狂時(shí)以為的那么重要;關(guān)于自己,很多東西是可以不去重視的,很多東西是可有可無的,很多東西是完全可以放棄的。
因此,我是這么想:做報(bào)紙是你的“正業(yè)”,即便有再多的折磨、委屈,可你天生又做不成“撂挑子”“溜肩膀”的那種人,那就唯有堅(jiān)持。職場(chǎng)中人,凡事拿出職業(yè)態(tài)度好了:認(rèn)真對(duì)待,負(fù)責(zé)到底,無愧于心,足矣。
不過,在 “正業(yè)”之余,我就比較“不務(wù)正業(yè)”了。
“骨灰級(jí)宅女”的幸福生活
曾幾何時(shí),可能因?yàn)闊釔鄞蚯颍赡芟矚g寫各種游記類文字,因此有那么一些年,很不幸,落下“愛玩”的壞名聲。
我確實(shí)喜歡打球。乒乓球是打小就喜歡,一路玩到剛工作的那幾年。2001年甚至還作為報(bào)社特派記者單槍匹馬地到日本大阪采訪報(bào)道了最后一屆的團(tuán)體與單項(xiàng)合一的世乒賽。
還有保齡球,上世紀(jì)90年代這項(xiàng)運(yùn)動(dòng)熱遍全國(guó)時(shí),我是走哪里玩到哪里,隨叫隨到,因?yàn)橥媲颍€拿過幾次小獎(jiǎng)。本世紀(jì)初,突然改迷羽毛球了。為了這幾項(xiàng)運(yùn)動(dòng),球具球包球鞋等全副武裝樣樣配齊。但這幾項(xiàng)運(yùn)動(dòng)在近年來一一停下,我從熱愛運(yùn)動(dòng)的家伙,變成不鍛煉的“資深亞健康”。
年輕時(shí),有那么幾年做著專職記者,時(shí)間上自由度大,心態(tài)上有激情有好奇,一聽說能出遠(yuǎn)門就開心。時(shí)間長(zhǎng)的幾次,一走大半個(gè)月甚至一個(gè)月以上:1995年有一個(gè)月在西藏四處跑;2001年,上半年有大半月獨(dú)自泡在大阪采訪世乒賽,下半年有40多天在昆明到長(zhǎng)江源頭沱沱河的路上;2000至2003年,有幾次新疆內(nèi)蒙古甘肅貴州西藏等地的采訪,戰(zhàn)線長(zhǎng),每一趟一出去都是大半月;2004年,隨一個(gè)車隊(duì)從北京開車進(jìn)入西伯利亞,橫穿亞歐大陸抵達(dá)法國(guó)巴黎,在路上跑了一個(gè)月。而最近這八年,大概是因?yàn)楸话婷嫠浪浪┳×说木壒剩易畛B(tài)的業(yè)余生活,是“宅著”。
只要在家,我總是滿屋子里外翻找著各種能洗的東西,然后轟轟烈烈展開洗曬行動(dòng)。此外,吸灰,拖地,洗碗,倒騰衣柜里各季衣服,各種家務(wù)活一遍下來,心情大爽。對(duì)于非常厭惡逛街,又對(duì)跑到健身中心跑步舉啞鈴這類行為覺得“太事兒了”的我來說,做家務(wù)活,足不出戶就把周遭環(huán)境搞好,順帶也把“心情垃圾打掃干凈”,還有比這性價(jià)比更高的業(yè)余生活嗎?
可洗可不洗的東西洗完了,灰也吸了,地板也拖了,接下來干的事依舊很業(yè)余——看報(bào)紙、看書、上網(wǎng)看新聞。我這樣四處“圍觀”的目的,其實(shí)很功利——為了知道這星球上發(fā)生了什么事,尋找合適我們部門的選題……
說心里話,很后悔應(yīng)下這次稿約,在每天活得風(fēng)風(fēng)火火的我的那些優(yōu)秀同行看來,我這種周而復(fù)始的工作是多么的平淡與乏味。如果這份“作業(yè)”最終還是發(fā)表了,我只想老老實(shí)實(shí)地說,在有利于本職工作、不妨礙旁人、不給社會(huì)添麻煩的大前提下,每個(gè)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調(diào)整著自己,安排好自己,這就夠不錯(cuò)了——好吧,給自己鼓個(gè)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