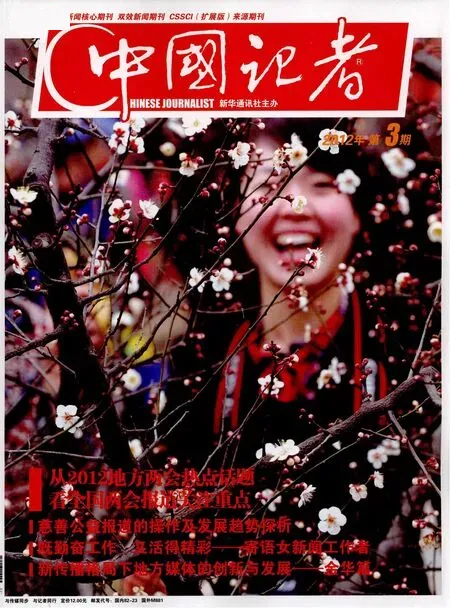守望在“三農”新聞的田野上
□ 文/王朝霞
(作者是《甘肅日報》主任記者)
車窗外蜿蜒起伏的山路、銀裝素裹的梯田、零零星星散落山野里的小村落……這是16年來,我最常見的景色。我熱愛腳下這片土地!這片土地是中國西北的鄉村,盡管她貧瘠落后,但她像母親一樣從未嫌棄過我,她是滋養我采寫新聞的源泉;盡管她偏遠封閉,但她是我新聞事業的良師益友;盡管她荒涼貧窮,但她是我挖掘的“新聞寶藏”。
守望的苦與甜
甘肅地域狹長,東西跨度千余公里,農村基礎設施差,許多鄉村不通汽車。舉一個例子,我到北京采訪中國國際農產品交易會,乘飛機近3個小時,而我從蘭州出發,到慶陽市正寧縣采訪,乘汽車得整整10多個小時,如果再到某個偏遠村子采訪,時間沒法計算。這意味著我在甘肅從事“農口”新聞報道,要比跑時政、經貿、文教、工業等行業新聞的記者要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和體力。
2012年春節,正好在甘肅天水市甘谷縣過年,這里正是甘肅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掐辮子”的故鄉。“掐辮子”是草編工藝品的傳統手工藝,“掐”的“辮子”用途十分廣泛,可用于編草帽、編花籃、編壺墊、編草鞋、編茶座墊等。于是我便想利用這一探親的機會對此進行采訪。
但當我來到甘谷縣魏家新村時卻發現,隨著近年農村城鎮化的發展,這里已看不到往昔農民“掐辮子”的熱鬧情景了。一位老人告訴我:“魏家新村自從2006年搬遷到新農村居住點后,大部分農民逐漸到城里打工去了,不種地了。不種麥子,哪來麥稈?沒有麥稈,農民怎么‘掐辮子’?”另一位老人介紹:“要采訪‘掐辮子’,要到北山地區,那里的土地大部分種小麥,山區農民把‘掐辮子’作為一項家庭副業收入。”還有人說:“你就近采訪一下魏家新村的奶奶、姑姑們,‘掐辮子’都曾經是她們的 ‘拿手好戲’,你沒必要跑遠路去采訪。”
但我心里明白,新聞必須靠事實說話。問清采訪路線后,有兩條路可選擇:一條是乘公共汽車從魏家新村先到縣城,再換汽車盤山繞嶺到北山的謝家灣鄉,由于春節期間普降大雪,路上時有翻車事故發生;另一條即從魏家新村爬山走到謝家灣鄉。
于是,我選擇了步行去采訪,由魏家新村一位老鄉帶路。陡峭的山路布滿積雪,陰坡處雪很厚,走上去咯吱作響,陽坡處融化成泥路,路上很難走。一些羊腸小道需要手腳并用才能通過。從上午10點50分出發,經過魏家新村經過魏家灣村、陰屲村、春樹坪村、趙家峴村等許多小村落,一直走到下午2點20分,才到達目的地——謝家灣鄉東莊村,走這么長時間的山路,累得夠嗆。但我看到東莊村許多農家房前屋后堆放著黃燦燦的麥稈,以及用麥稈編織的一捆捆草編,年邁的老太太、年輕的小媳婦大姑娘、五六歲的小女孩,三五人聚在一起,一邊拉著家常,一邊用麥稈在她們靈巧的手指間“掐辮子”。頓時我的累意全無,為這些第一手素材而興奮。
當我采寫的《黃燦燦的麥稈里“掐”出新生活》(《甘肅日報》2012年2月4日)見報后,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后來我把這篇報道的相關報紙寄給采寫的農民丁金順時,他看到這篇報道后高興地說:“‘掐辮子’是我們山畔畔里的一項民間手工藝,很普通的事,但你寫出來,把它變得很高檔了!我們要繼續‘掐好辮子’”。
守望的記憶
甘肅是一個2600萬人口的農業大省,但也是一個農業窮省,連續多年來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位居全國末位。但無數次農業、農村、農民“三農”新聞報道實踐告訴我,只要能吃苦,深挖掘,思考問題,捕捉亮點,隴原大地的山山水水、溝溝坎坎,都蘊藏著“三農”新聞的“金子”。
作為甘肅長期跑“農口”的記者,我最為關注的就是“一方水土能否養活一方人”的糧食問題。同時,糧食問題也是影響國際政治民生的重大問題,國際學者早就發出“21世紀誰來養活中國?”的質疑。中國北方地區連年干旱,糧食問題倍受國際關注。由我采寫的《甘肅旱農技術探索出北方農業發展新路》(2010年12月7日《甘肅日報》二版頭條),全方位報道了甘肅科技人員獨創的全膜雙壟溝播技術,探索出中國北方農業跨躍式發展的新路子。這篇新聞被評為2010年度甘肅新聞獎一等獎。相關領導、農業專家稱贊我為這項技術推廣在新聞宣傳上立下了“汗馬功勞”,而農民通過這項技術能夠多打些糧食,能夠增收致富,則是我最大的欣慰。
記得采訪全膜雙壟溝播技術時,通渭縣平襄鎮宋堡村村民王明道高興地說:“有了全膜雙壟溝播技術,等于挖了集雨窖,天上只要下一點小雨,就能把雨水聚匯在地里,保住土壤墑情,種莊稼不用發愁了”。農民們的語言十分樸實,讓人聽了十分感動,他們對這項科技成果的認可,成為我采寫這項農業科技新技術的原動力。
女兒和事業都是我的最愛
作為一名女記者,在進行一些難度較大的新聞采寫時,我有著“巾幗不讓須眉”的自信。然而,作為一位孩子的母親,在采訪背后,心中總有那么一絲苦澀、一點遺憾。
2001到2002年的青藏鐵路建設采訪,是我從事新聞采寫生涯中最為艱苦的一次采訪。青藏鐵路(格爾木至拉薩段)建設舉世矚目,要在沉睡了上萬年的青藏高原凍土上鋪鐵軌,是一項世界性難題。2001年10月,我乘汽車來到青藏高原,采寫的《四十年心血解秘萬年凍土層/兩代人智慧奠基千里青藏線》,向外界宣告中科院寒區旱區研究所成功攻克了在凍土層上鋪鐵軌的世界性難題,獲得2002年度全國黨報新聞三等獎。
當時,我與中科院冰川凍土專家們來到青藏高原,一路上感到身體極度不適,頭暈、惡心、嘔吐,快走幾步,感到頭痛欲裂,心臟急跳得像要蹦出來。那時,正值給女兒斷奶,每每想到僅11個月大的孩子時,眼淚時常滑落。結束采訪后到了拉薩,同行者都去旅游了,我急急乘飛機回蘭州,見到女兒變瘦了,哭著不肯讓我抱她,心中有的不僅是傷痛,更是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愧疚。
有了第一次到青藏高原成功采訪的經驗后,2002年7月,報社再次派我前往青藏鐵路建設現場采訪。記得出發時,報社司機送我到火車站, 1歲8個月的女兒離開我懷抱時,急得哇哇大哭喊媽媽。那時那景讓我肝腸寸斷,但強烈的新聞使命感又催促我要加緊行進的腳步。
現在女兒快12歲了,不會再為我出差采訪而哭鼻子,但我仍覺得愧對女兒。可是作為一名記者,我深知自己肩負著什么,那些父老鄉親勞作的背影,讓我無法停止采訪的腳步。
有朋友曾經問我“這么久做著農口的新聞,不覺得苦嗎?累嗎?”是的,新聞是用腳“跑”出來的,但每每看到老鄉因為我的報道充滿喜悅時,卻讓我有了無法割舍的情懷。這么多年,只要有空我就會爬山,每當登上山頂俯瞰山色時,心中的遼闊讓我會忘記所有的疲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