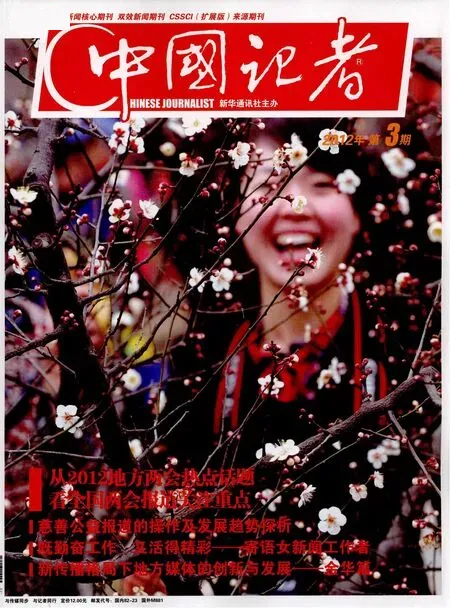中東:一個“80后”女記者的新聞征途
□ 文/何奕萍
(作者是新華社中東總分社記者)
本欄編輯 梁益暢 46266875@qq.com
王清穎 wangqy1012@gmail.com
一個“80后”女孩,穿梭于埃及亞歷山大教堂的爆炸中,行走在班加西的路途上,陪伴她的只有如親人般的同事,泡面、綠茶是她每日最享受的生活,而不絕于耳的槍聲、滿目瘡痍的土地讓她年輕的心深深地明白,和平對于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意義。
2012年2月2日,在吉薩的斯芬克斯廣場,我從容地作完一次出鏡。在我身后是上千名抗議的群眾,聲討前一天晚上在塞得港球賽中導致74人死亡的肇事者。這是2010年10月16日我成為一名中東地區的新華社視頻記者以來所做的一次普通采訪。回首這一年多,我著實不敢說我在新聞上有什么作為,但作為一名視頻記者,我確實收獲了很多。
動亂造就勇敢與從容
對于視頻記者而言,首先要適應的就是出鏡報道,要想做好,不僅要克服在鏡頭前的膽怯,還要無視周圍環境的干擾。開羅人民向來以熱情著稱,尤其在我們這些“老外”的鏡頭前更是活躍。當我們出鏡的時候,他們經常會在我們身后推推搡搡。剛開始時,我特別不適應這種嘈雜的環境,每次出鏡都要做十幾二十次,自己感到非常煩惱。
2011年元旦的鐘聲剛敲響,我正要進入夢鄉,卻被手機的鈴聲吵醒,電話那頭,傳來埃及第二大城市亞歷山大一處教堂爆炸,造成20多人死亡的消息。如此重大事件,不敢耽誤。接下任務,我就和同事趕往200多公里外的亞歷山大。到達事發地的時候,只見教堂四周的街道已被警察封閉。教堂旁邊的一條街道上,一些群眾正在向警察投擲石塊,而警察的催淚彈煙霧很快就熏到了眼前。不久,在與那條街道垂直的路上,數百人開始游行吶喊,聲音不絕于耳。出鏡,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要快,沖突場面可是不等人的。深深吸一口氣,我努力克服膽怯與吶喊聲的干擾,開口說起來。那次出鏡,做得非常順利,也許是壓力導致動力的緣故吧。
年初的這一次報道,極大地鍛煉了我的勇氣,而后我才敢于去報道更大規模的沖突。作為視頻記者,事發之后要第一時間趕往現場,很多消息還要靠我們傳達出去,所以那種時候,深感自己身上的重任,沒有別人可以依靠,自己就要變得堅強和勇敢。
自從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發大規模的抗議游行以來,我們的視頻報道就沒有脫離過驚險。還記得1月28日的晚上,我和幾個同事為了避開警察的視線拍攝,躲在解放廣場上的一處高樓內,把鏡頭偷偷地擱在陽臺上偷拍,目睹著憤怒的青年從廣場的四面八方攻入被警察封鎖的解放廣場,半夜的時候,四十多輛坦克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廣場,那一刻,我們都屏氣凝神。直到好多青年爬上坦克,開始歡呼,我們知道軍隊和百姓站到了一起。就在第一時間,我們的消息也發了出去。
埃及從爆發抗議游行到穆巴拉克下臺的18天,局勢充滿了跌宕起伏,沒有人能猜到結果。因為宵禁,人們都很少出門,只有我們這些記者,還穿梭在開羅的大街小巷采訪。平安度過那段日子,我最大的體會是和平多么重要,這幾個字說出來很容易,而分量卻是沉淀于心的。
同甘共苦,收獲親情般感情
在我所在的新華社中東總分社有四十多人,在2011年一年的報道中,從社長到廚師,都為作好報道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工作,彼此之間建立了親情般的感情。1月28日晚上,我們完成報道任務,從解放廣場趕回分社,已經是凌晨四點多了。可當我們踏進分社大樓,社長和衣躺在會議室的沙發上,辦公室主任的辦公室燈火通明。他們都在等著我們回來。當時有說不出的感動。而他們這種關懷一直延續著,不管在埃及,還是在利比亞,我們在前方報道,他們總在后方支持、關心著我們。
而和同事們在困難時期建立的情誼更是這一年報道中的強大支柱。2011年4月18日,我和我們的阿文、英文以及攝影記者接到任務,前往利比亞反對派大本營班加西進行利比亞局勢報道。當時,是卡扎菲的雇傭軍和反對派正激烈交火的時候,聯合國的禁飛令已經施行。我們只能從陸路,途徑利埃邊境的塞盧姆進入利比亞。
20多個小時的車程,旅途勞累不說,因為當時在禁飛問題上,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的是棄權票,外面流言說利比亞反對派已經拒絕中國記者進入。走在半路上得到的這個消息讓我們很喪氣。是進是退?我們幾個達成一致,既然來了,就沒有回去的道理。所幸的是,憑著我們當地雇員的關系以及利比亞民眾對中國人的好感,我們通關成功。
四月的利比亞,天氣已經開始轉暖,從利埃邊境前往班加西的路上,鮮有人家。而半路上那一片無際的青草地更無法讓人想象前面就是政府軍和反對派對峙的戰場。經歷了埃及動蕩的18天,對于這份美景格外珍惜。不去想未來的日子會是怎樣,我們都感到起碼眼前要好好享受這片寧靜的田園。
在班加西的時候,有兩件事情讓我非常難忘。第一件是4月30日的深夜11點多,我做完了一天的事情準備睡覺,可是窗外卻傳來斷斷續續的槍聲,而且越來越密集。本已困意十足的我立刻警覺起來,難道晚上搜捕革命委員會的人發生槍戰?這時,我的房門也開始被咚咚敲響,同事站在門口,“卡扎菲的兒子和三個孫子被打死了。”這在當時利比亞雙方戰局僵持的情況下是一個特別大的消息。二話沒說,我們拿起設備就沖出酒店,當我們在酒店門口等待車子的時候,很多其他媒體的記者紛紛下樓,那一刻,我感到自豪,我們對新聞的敏感性和專業性是數一數二的。直到后來,還經常會有人到我們這來打聽或確認消息。
那天的班加西解放廣場上如同過節般熱鬧,我開始站到人群中去做出鏡,同事一邊給我打燈,一邊緊緊地盯著四周的人群,一怕人群推搡,二怕亂槍流彈傷人。當時正因為有他們的存在,我才可以安心地把出鏡平穩做完。
在班加西時,雖然住在酒店,但供應并不充足。很多時候,我們就泡方便面解決吃飯問題。其實這個時間是比較幸福的時候,因為那意味著沒有突發事件、沒有例行新聞發布會,時間是我們自己的。煮上開水,我們一邊泡方便面,一邊拿出自己帶過去的綠茶沖起來。吃完方便面,便可以喝會兒茶,閑聊一會兒,是非常不錯的休息。而今回想起來,去年每次出差都是一個小分隊,雖然視頻、文字、攝影大家分工有別,但總是通力合作,互相幫助,播下的是辛苦,收獲的是友誼。
2012 ,且行且珍惜
駐外的日子隨著中東的局勢跌宕起伏過得非常之快,轉眼間,2012年來到了眼前,距離離任的日子還有半年多的時間。我的記者使命還在敦促自己前行,如果說過去那一年有太多的意想不到,那么2012年我們則是做好準備,更加理性地去面對可能發生的一切。
這些天,關于敘利亞的局勢,各國外交的博弈更加激烈的展開。表現在媒體上就是,西方的媒體開始大量報道敘利亞政府軍炮轟霍姆斯,造成平民死亡的消息,為推翻阿薩德政權大量造勢。而我在敘利亞采訪的同事卻在微博上發表了這樣一條微博:“我所感受到的敘利亞,絕對不是歐美政客口中的樣子。當然我不敢說所見代表了全貌,但是至少有一點,敘利亞人想要什么樣的自由和民主不應該由美國來定義,看誰不順眼想讓誰下臺,也應該是敘利亞人民說了算,這個“人民”,也不該由別國人來定義。”下面是一張2月5日,大馬士革支持阿薩德的人群的照片。
我非常贊成這位同事的觀點,經過中東的亂局,經常關注西方媒體的報道,有時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報道是明顯地違背中國人道德觀的。所以對同一件事情的報道,我們往往得出完全相反的觀點,在這種時候,有自己的記者,堅持自己的聲音,顯得非常重要。而作為其中一員,我倍感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