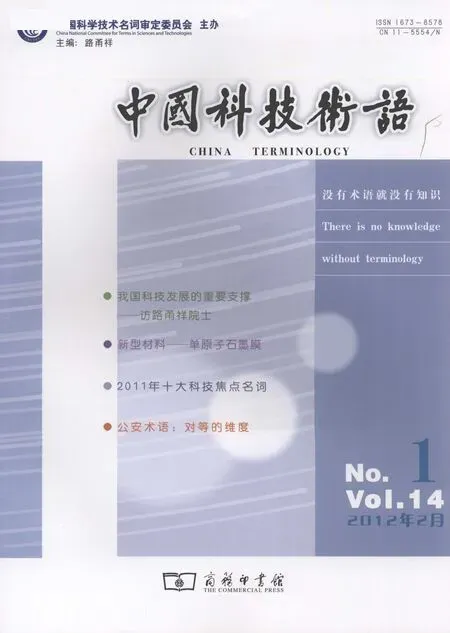論譯者主體性與中醫術語英譯的關系
裘禾敏
(浙江旅游職業學院,浙江杭州 311231)
論譯者主體性與中醫術語英譯的關系
裘禾敏
(浙江旅游職業學院,浙江杭州 311231)
作者以中醫術語為例,從語義學的角度探討譯者主體性與術語翻譯之間的內在關系,指出譯者不僅要把握與權衡中醫術語的字面含義與學術含義,而且要掌握足夠的語義學、術語學與中醫學等跨文化與跨學科知識,才能充分發揮譯者主體性,創造出成功的中醫術語譯名。
譯者主體性,中醫術語,語義學,字面含義,學術含義
引言
中醫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我國傳統科學中少數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并在當今以自身獨特的體系繼續不斷發展的學科,她憑借其獨特的學術體系影響著當今世界,并越來越多地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與認可。
豐富的中醫理論離不開獨特的概念,而其概念源于大量的術語。總體而言,我國現有的絕大多數自然科學的術語譯自外語(主要是英語與俄語),對中國的現代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飽含濃郁民族特色的中醫術語始于先秦,經過幾千年的歷時演繹,中醫學已發展成為富含“國情”的醫學體系,其術語與中國的傳統哲學、文化密切相關,富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很大一部分術語很難在英語中找到對應的譯詞。中醫走向世界,術語翻譯無疑是巨大的障礙。多年來,中醫翻譯研究一直偏向于醫古文文本與譯入語英語文本之間關系,循著從文本到文本之路,較少探討在翻譯實踐中起主導地位的譯者作用。
基于多年中醫翻譯實踐的經歷,筆者試圖從語義學角度解讀中醫術語的內涵,結合中醫術語的特點,提出在翻譯實踐中要積極發揮譯者主體性的作用,以探討譯者主體性與中醫術語翻譯的深層關系。
一 譯者主體性的界定
基于翻譯本身的復雜性,國內譯學界對什么是翻譯主體還眾說紛紜。許鈞認為[1],譯者是狹義的翻譯主體,而作者、譯者與讀者均為廣義的翻譯主體。楊武能則認為[2],作家、譯家與讀者都是翻譯主體。
筆者對上述觀點均表示異議。第一,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曾對由“在場(presence)的形而上學”與“語音中心主義”構成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指出,文字使作者與作品相分離,封閉的在場就被解構(deconstructed)了。這就表明,文本一旦以文字形式固定下來,作者就失去了說話的當下性。由此看來,作者不能充當翻譯主體[3]。
第二,盡管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論關注讀者對文本的建構作用,但是這種作用是在譯者所提供譯本的基礎上進行二度解讀而產生的,其反撥作用十分有限。所以,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是翻譯的唯一主體,而作者是創作主體,讀者是接受主體,它們三者之間呈現的是“一種平等的主體間性關系”[4]。
有學者這樣總結:“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5]這樣看來,譯者主體性雖然具有自主性、目的性與能動性,體現的是一種十分活躍的、個性化的創造意識,但它同樣受到相應客體不同程度的制約。將這種主體性的核心引入中醫術語英譯領域,不僅可指導中醫翻譯實踐,而且能豐富翻譯理論,有助于把握中醫術語文化內涵。
二 從語義學看中醫術語
術語是指通過語音或文字來表達或限定專業概念的約定性符號,它跟普通詞語的區別在于:術語的語義外延(denotation)是根據所指(signified)的關系確定的。換而言之,它跟能指(signifier)沒有直接的附屬關系。根據術語學規定,術語一般具有單義性(univocal)與單一指稱性(monoreferential)的定義要求。現代語義學認為,概念是邏輯思維的主要形式,是反映事物本質特征的思維產物,語義是客觀事物在語言中的反映。俄羅斯學者謝爾巴指出:“任何一種語言的絕大多數概念詞與另一種語言的概念詞毫無共同之處,只有術語是例外。”[6]不同語言之間的語義內涵(semantic connotation)有寬窄之分,語義范圍有大小之別。
中醫術語是指中醫里確定某個概念時所使用的專門語匯,它是整個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基礎,是中醫概念與原理的基本表述單位。一般認為,中醫術語包含兩層含義:字面含義(literal meaning)與學術含義(scientific meaning)。語義學家往往著重研究其字面含義,中醫學專家較多注重其學術含義,翻譯研究學者則必須兼顧其字面含義與學術含義。
中醫術語的字面含義是由構成該術語的每個漢字以及由這些漢字結合而成的句法規則(syntactical rules)共同決定的含義,而其學術含義則取決于專業定義。據現代語義學,術語的字面含義是其學術含義的語言基礎,術語的學術含義不能游離于字面含義而獨立存在[7]。就內容而言,中醫術語的學術含義應該比字面含義更為豐富;其次,中醫術語的學術含義應該與學術的字面含義保持一致,并只能在其字面含義基礎上加以科學的界定而形成;再次,中醫術語的學術含義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的內涵(connotation)通常會隨著學術的發展而不斷豐富。
譬如,《黃帝內經》里有這樣一句話:“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這里共出現了三個中醫術語“太陽”“陽明”“少陽”,若光從“字面含義”看,似乎與天氣天文有關。其實它們是傳統中醫學里辨證分析病證的術語,表示疾病的深淺程度與邪正盛衰,以揭示外感病邪侵入人體的病機變化與傳變規律。譯學研究者必須同時考慮字面含義與學術含義,一般分別將其譯成greater yang、bright yang、lesser yang。
三 譯者主體性在中醫術語翻譯中的能動作用
中醫術語門類繁多數量龐大,具有以下的特點[8]:(1)歷史性;(2)人文性;(3)定性描述;(4)民族性;(5)傳統性;(6)抽象的概念由具體的名詞來表述。譯者翻譯時須借助語義學、術語學、中醫學等知識。
中醫翻譯因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中醫理論的深奧玄密而變得“趣不乖本”與難以“曲從方言”(漢朝佛經翻譯的經驗),著名英國翻譯家魏逎杰(Nigel Wiseman)就說,世界上恐怕很少有幾個人能夠,甚至愿意從事這項工作的。從譯者的角度看,英語里缺乏中醫術語的對應語,這既是面臨的最直接與最現實的難題,但同時也是最能發揮主體性的地方,因為成功的譯文主要取決于譯者如何設法選取合適的譯入語。
1.盡力把握好中醫術語的學術含義
例如,中醫術語“賊風”,從詞源學看由“賊”與“風”兩個普通的漢字組成,起初有譯者望文生義,把它翻譯成 thief-wind、evil wind與 thievish wind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上這樣描述“賊風”:“自孔隙透入之風,易致疾病,故稱賊風。宋王袞博濟方四胎產:床頭厚鋪裀褥,遮障孔隙,免有賊風所傷。”[9]這其實還是語義學上所指的字面含義。而作為中醫術語,其學術含義主要指“能引起四時季節性疾病的病邪”(it refers to all abnormal climatic changes and exogenous pathogenic factors,which may attack and harm the human body without being noticed)。譯者在參照“賊風”的字面含義時,要更多考慮其中醫學術含義,因而經過不斷改進,目前形成了pathogenic wind這個比較科學的譯語。
又如,針灸有眾多穴位(acupoint),其中“遠道刺”一詞源于《靈樞·官針》:“遠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輸也。”它指“身體上部有病痛取用肘膝以下陽經的穴位進行治療”[10],因其針刺穴位距離病灶較遠而得名。從語義學看,可把“遠道”與“刺”當作兩個意群處理;就術語學角度而言,“遠道刺”的字面含義比較明確,可理解為“距離比較遠的針灸療法”,其學術含義指“對離患處較遠部位進行針刺的方法”。據此,似乎可譯作 remote needling,distant needling,distal needling等,但如從中醫學術含義考慮,distal一詞本身包含了“遠側、遠端、末梢、末端”等與醫學相關的內涵,所以譯為distal needling最接近本義。
2.字面含義與學術含義的取舍
醫古文含義豐富,行文簡潔,語義大多呈提示性,英譯時提示性術語往往變成了明確的陳述,這給譯者帶來很大的挑戰。如術語“純陽之體”,如果光從字面含義去理解,就恐怕很難聯想到它與“小兒的體質特點”有關,其學術含義特指“小兒正處于陽氣盛發、生機蓬勃之生長期”。有的譯者把它譯成infantile body,從語義的內涵與外延來看,意義不夠明確,而譯為body of pure yang更貼近“純陽之體”的學術含義,因為infantile body沒有指明“小兒充滿生命活力,茁壯成長”的核心內容。
針灸學里有“交會穴”,指有兩條或兩條以上經脈交會通過的穴位,大多分布在頭面與軀干部位[10]。該術語字面含義與學術含義都比較明確,而且也比較靠近,在這種情形下,主要取決于譯者對譯入語英語近義詞的取舍。現在常見的譯法有confluent acupoint,crossing acupoint、convergent acupoint等[11]。據《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辭典》,confluent一詞解釋為“匯流的,匯合的;尤指兩條河流的合流點”,而“交匯穴”的學術含義是“有兩條或兩條以上經脈交會通過的穴位”,與confluent正好吻合,以此看來,可譯為confluent acupoint。
3.努力保留中醫術語固有的文化異質
中醫術語的特點往往要求譯者在努力保持那些中醫學固有的文化特質,特別是要竭力保留中醫學有別于現代醫學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
有些中醫術語似乎能在西醫里找到對應的術語,出于方便或其他因素考慮,譯者可能會自然而然的選擇該“對應語”,其實,這種簡單的處理辦法很有可能會導致中醫術語文化異質性的丟失。如“郁證”從表面上看好像與西醫術語“抑郁癥”相同。其實,在中醫語義語境下,“郁證”的學術含義是“因情志不暢、氣機淤滯而引起的征候”,譯者只有準確把握這層核心意義,才有可能從譯入語里重新構建較為妥帖的譯名,可以譯為 stagnant syndrome或depressive syndrome,尤其是stagnant,從語義學的學術含義看帶有中醫的原質標記。有譯者提出譯為melancholia,也未嘗不可,但不是理想的譯語:第一,它在學術含義方面與中醫“郁證”只是存在部分重疊,并且導致該癥狀的病理原因也很不相同;第二,作為術語,melancholia似乎有一點西醫色彩,它表示“以情緒低落與莫名恐懼為特征的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 marked by low spirits and fears that have no real cause),而“郁證”則有明確的致病原因,抹殺了中醫術語的異質性。
另外有些中醫術語,特別是臨床上涉及疾病名稱的術語,會有相近的西醫學術語,這時譯者須慎之又慎。比如“勞瘵”,指的是“病程緩慢的一種傳染性疾病,伴有惡寒、潮熱、咳嗽、咯血、納差、肌肉消瘦、困頓乏力、盜汗與自汗等癥狀”(it is a chronic infectious disease featured by aversion to cold,hectic fever,hemoptysis,cough,bad appetite,emaciation,fatigue,spontaneous perspiration and night sweat)[11],有譯者根據其中醫學術含義把“勞瘵”翻譯成tuberculosis(肺結核)。根據《現代高級英語雙解辭典》,tuberculosis的學術含義為 a kind of wasting disease affecting various parts of the body’s tissues,esp.the lungs(肺結核是一種消耗性疾病,影響人體的各個組織,尤其影響肺部)[12],與“勞瘵”相比,其內涵要小得多,只是涵蓋一小部分癥狀。而如果譯為consumptive disease,則較好地包括了術語的學術含義,也能保留中醫術語的個性化原質標記。
四 結論
隨著中西方在中醫領域交流的不斷深入,譯者需要發揮主體性,在實踐中不斷摸索有效的翻譯策略,使早期一些較為復雜冗長的譯語趨向于中醫英語術語。一方面,譯者需要把握字面含義與學術含義的不同,為此就需要精通英語與醫古文、熟悉中醫基本理論、通曉傳統與現代翻譯理論、掌握術語學要旨;另一方面,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受到源語醫古文、目標語英語、語境、歷時性與共時性等許多因素的制約。譯者需要努力協調好上述各種關系,在實踐中創造出比較理想的中醫術語譯名。
中醫翻譯不同于一般的科技翻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它更偏向于文化翻譯,因為中醫學與中國傳統哲學(如老莊、孔孟學說)天生就具有悠久的淵源關系,蘊含著不可分割的深邃哲理。譯者在具體翻譯實踐中須根據實際情形采用靈活的翻譯策略。由于中西文化及中西醫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許多概念很難在英語里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對應語,運用幾種翻譯方法來翻譯一個中醫術語已經成為較普遍的現象。
[1]許鈞.“創造性叛逆”和翻譯主體性的確立[J].中國翻譯,2003(1):9-11.
[2]楊武能.再談文學翻譯主體[J].中國翻譯,2003 (3):10.
[3]裘禾敏.論后殖民語境下的譯者主體性: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J].浙江社會科學,2008(3):87-88.
[4]陳大亮.誰是翻譯主體[J].中國翻譯,2004(2):6.
[5]查明建,田雨.論譯者主體性——從譯者文化地位的邊緣化談起[J].中國翻譯,2003(1):22.
[6]黃建華.雙語詞典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7]馮志偉.現代術語學引論[M].北京:語文出版社,1997.
[8]朱建平,王永炎.加強中國術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J].科技術語研究,2005(1):18.
[9]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辭源[Z].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10]《中醫大辭典》編輯委員會.中醫大辭典[Z].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
[11]李照國.中醫英語1000中級詞匯速記[Z].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2000.
[12]霍恩比.現代高級英語雙解辭典[Z].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2.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and TCM Term Translation
QIU Hemin
This author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and TCM term translation from the semantic approach.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translators are required not only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 between the literal meaning and the scientific meaning of TCM terms,but also to produce the appropriate versions with a good knowledge of semantics,terminology and TCM.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TCM term,semantics,literal meaning,scientific meaning
N04;H059;R22
A
1673-8578(2012)01-0024-04
2011-07-25
2011-12-14
本文系2008年度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NO:D08YY01)的主要成果
裘禾敏(1966—),男,博士,浙江旅游職業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多語種跨文化交際、語用學研究。通信方式:qiu815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