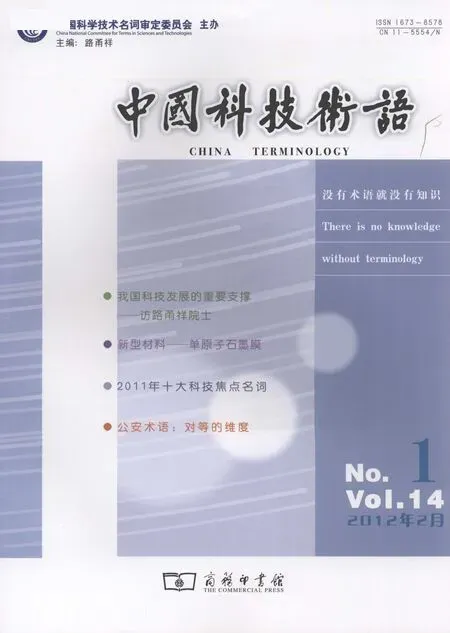漢德術語互譯的若干問題研究
黎東良 郭 劍
(1.山東大學(威海)翻譯學院,山東威海 264209 2.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北京 100717)
漢德術語互譯的若干問題研究
黎東良1郭 劍2
(1.山東大學(威海)翻譯學院,山東威海 264209 2.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北京 100717)
漢語和德語屬于不同的語系,它們之間的差別給漢德術語互譯帶來了很多困難。根據在國內和德國多年的翻譯實踐,從漢德術語互譯的對等、選詞、排列秩序、直譯還是意譯等方面出發進行探討。
漢語,德語,術語,互譯
引言
在漢德術語互譯的過程中,簡單化的、一一對應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這是因為漢語和德語屬于不同的語系,它們之間的差別給漢德術語的互譯帶來了很多困難。雖然國內一些同行也在相關教材里討論了漢德術語的互譯問題,但是由于一些客觀原因,使得他們目前的論述往往淺嘗輒止,不夠深入。筆者曾在國內和德國為大型企事業單位和跨國公司擔任過翻譯,根據多年的翻譯實踐,擬從漢德術語的概念對等、互譯選詞、詞語排列秩序、互譯時的增減字、直譯還是意譯等方面出發,對漢德術語的互譯問題進行探討。
一 漢德術語互譯的概念對等
不了解的人往往會認為每一個漢語術語總會有一個德語術語與之對應,事實上多數的漢德術語在概念上是對等的。但是,情況并非總是如此。具體舉例如下:
1.中文詞“三無產品”與德文詞“No-name-Produkt”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規定必須有中文廠名,中文廠址、聯系電話、許可證號、產品標志、生產日期、中文產品說明書,如有必要時還需要有限定性說明等等,缺少的均視為不合格產品,上述要求缺少其中之一,均可視為“三無產品”。有人會認為德語詞“No-name-Produkt”與“三無產品”對應,其實不然,因為該詞指neutral verpackte Ware ohne Marken-od.Firmenzeichen[1],意為中性包裝的無商標或者無生產廠家的產品,不一定同時無商標和無生產廠家,日期總是存在的。
2.中文詞“城市”與德文詞“Groβstadt”
我們知道,城市按其規模可分為大、中、小型。根據國務院在1963年頒布的“城市人口詞條”的規定是:在中國,凡工商業集中、居住人口10萬以上的地方可設市;凡工商業相當集中,居住人口3000以上的地方,可設鎮。而根據2010年版的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w?rterbuch(《杜登德語通用大辭典》)[2],德語詞“Groβstadt”的內涵是:groβe Stadt (mit einer Einwohnerzahl von mindestens 100 000),翻譯成漢語是大的城市(居民至少10萬)。這說明在德語里,只要某個城市人口達到10萬,就是大城市了;而在中國設市的起點是人口10萬。如此一來,中國的任何一個小市都稱得上德語里的“Groβstadt”。所以,漢德術語互譯的過程中要考慮到國情不同的背景。
3.中文詞“牙醫”與德文詞“Zahnarzt”“Dentist”
中文術語“牙醫”在德語里有2個對應術語,分別是“Zahnarzt”和“Dentist”。但是二者還是有區別的:Dentist指Zahnarzt ohne Hochschulprüfung[2],即未經大學考試、無博士學位的牙醫;Zahnarzt指Arztfür Arztheilkunde(牙科醫生)。由此可見,Zahnarzt跟中文里的“牙醫”對應最佳。
4.中文詞“文章”與德語詞“Artikel”“Aufsatz”“Beitrag”“Abhandlung”
中文術語“文章”與德語術語Artikel、Aufsatz、Beitrag、Abhandlung的內涵和外延并不一致。根據《漢英雙語現代漢語詞典》[3],文章指:(1)篇幅不很長的單篇作品,(2)泛指著作,(3)暗含的意思,(4)關于事情的做法。
而與“文章”對應的德語詞的內涵分別是:(1) Artikel:Aufsatz,Abhandlung,Beitrag;(2)Aufsatz: kürzere Abhandlung über ein bestimmtes Thema;(3) Beitrag:Aufsatz,Artikel in einer Zeitung,Zeitschrift od.in einem Sammelband verschiedener Autoren;(4) Abhandlung:schriftliche[wissenschaftliche]Darstellung,l?ngerer Aufsatz[4]。由此可見,Artikel是個總概念,包含了Aufsatz、Abhandlung、Beitrag的意思; Aufsatz指針對某一主題較短的文章;Beitrag指登在報紙、雜志或者論文集里的文章;Abhandlung指書面的(科學的)論文,較長的文章。
5.中文詞“壽命”與德文詞“Lebensalter”
在科技文獻里,中文詞“壽命”與德文詞“Lebensalter”的內涵并不一樣。根據第四機械工業部標準化研究所編寫的《可靠性基礎》[5],在電子儀表可靠性方面,對不可修復的產品,“壽命”指發生失效前的工作時間或工作;對可修復產品,“壽命”則指相鄰失效(故障)間的工作時間。根據DIN4004L[6],“Lebensalter”在德文里指Zeit von der ersten Inbetriebnahme zu einem Stichtag,翻譯成中文是從首次投入使用到某一次抽樣日期之間的時間。顯然中文詞壽命與德文詞 Lebensalter的內涵不一樣。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中文里若說某城市是一座“大學城”,那里的大學一定很多;而德語里“Universit?tsstadt”的內涵卻是 Stadt,in der sich eine Universit?t befindet,意思為只要某城有一所大學,就是德語里所謂的“大學城”了。德語里將中文術語“信息社會”翻譯為“Informations-gesellschaft”,但是,將“信息高速公路”則翻譯為“Datenautobahn”(也有人翻譯成“數據高速公路”)。
總之,在進行漢德術語互譯時一定要注意概念是否對等。否則,輕則給術語界和翻譯界帶來更多困惑,重則給國內招商引資以及外貿出口造成重大損失。
二 漢德術語互譯的選詞
漢德術語互譯選詞問題是相當復雜的,盡管有像中文“我有一本書”和德文“Ich habe ein Buch”這樣幾乎完全對應的句子,但是畢竟很少。因此,漢德術語的互譯選詞不是個簡單的問題。下面舉例說明:
漢德語里各自都有高、大、快、特、極等概念,但在互譯選詞時就有明顯的變化。例如漢語里說“我身高一米八”,在德語卻只能是“Ich bin 1.8 Meter groβ”,這里中文的“高”翻譯成德文后變成了“groβ”,然而實際上德語詞“hoch”對應中文詞“高”,“groβ”對應中文詞“大”。中文詞“葛洲壩”(位于湖北宜昌的水利工程)翻譯成德語后變成了“Gezhou-Hochdamm”,“大壩”變成了“高壩”。中文詞“大學生”對應德語詞“Student”,沒有形容詞專門對應“大”。中文里“最好的一塊”在德語里卻是“L?wenanteil”(獅子的部分)。中文詞“高等數學”對應德語詞“H?here Mathematik”(較高等的數學)。中文詞“特快專遞”對應德語詞“Schnellere Post”(較快的郵件)。中文詞“筆直”對應德語詞“schnurgerade”(像繩子一樣直),“kerzengerade”(像蠟燭一樣直)。中文詞“酷熱”在德語里則是“Affenhitze”(猴子似的炎熱),“Mordshitze”(謀殺似的炎熱)。
還有一種常見情況是一個中文詞對應多個德語詞。例如,中文詞“票據”在德語中有很多對應詞,“發票”對應德語詞“Quittung”,“飯票”對應德語詞“Essensmarke”,“戲票”對應德語詞“Theaterkarte”,“飛機票”則可以是“Flugschein”或者“Flugticket”,“鈔票”對應德語詞“Banknote”,“選票”對應德語詞“Wahlzettel”。又如,中文詞“打開”在德語里有幾個對應詞,德語動詞“?ffnen”指把一個密封了的東西打開(eine Büchse ?ffnen指開罐頭),“aufbrechen”指把一個關閉了、鎖住的東西打開(die Tür aufbrechen為開門),“aufschlieβen”指用鑰匙打開(den Schrank aufschlieβen指用鑰匙把柜子打開),“aufmachen”為打開一個器官或合上的東西(den Mund為把嘴巴張開,Koffer aufmachen為把箱子打開),“aufschlagen”指通過數次擊打來打開(den Nuss aufschlagen指把核桃打開)。
三 漢德術語互譯的詞語排列順序
漢德術語互譯的詞語排列順序問題具體而言,是指在進行漢德互譯時會出現漢德詞語排列順序一致與不一致的地方。例如中文詞“大學講師”“黑板”與德語詞序相對應分別為“Universit?tsdozent”和“Schwarzes Brett”;但中文詞“累死”“學前教育”“系列文章”在德語里的表達順序則相反,分別為“todmüde”“Vorschulerziehung”“Artikelserie”。研究漢德術語互譯后的詞語排列順序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粗看起來這中間似乎毫無規律可言,但是,筆者通過大量的國內外翻譯實踐,總結了幾條規律如下:
1.中文里帶有“無”“不”“防”“面向”等前綴的詞語翻譯后出現在德語復合詞后
例如:中文詞“無國籍的”對應德文“staatlos”,中文詞“無競爭力的”對應德文“wettbe-werbsunf?hig”,中文詞“無核武器的”對應德文“kernwaffenfrei”,中文詞“無情的”對應德文“erbarmungslos”,中文詞“不透水的”對應德文“wasserdicht”,中文詞“不退色的”對應德文“farbecht”,中文詞“不計其數的”翻譯成德語后為“zahllos”,中文詞“面向實踐的”對應德文“praxisorientiert”,中文詞“面向消費的”對應德文“konsumorientiert”,中文詞“面向需要的”翻譯成德語后為“bedarfsorientiert”。
2.德語的副詞作定語放在被修飾的名詞后,翻譯成中文后位置相反;漢語介詞短語作定語翻譯成德文時一律放在名詞之后
例如:德語“das Geb?ude dort”翻譯成中文為“那幢大樓”,德語“die Zeitung heute”翻譯成中文為“今天的報紙”,德語“die Lage heutzutage”翻譯成中文為“如今的形勢”。而漢語介詞短語作定語的例子有:漢語“關于物價的討論”翻譯成德語為“die Diskussion über den Preis”,“關于國際形勢的報告”翻譯成德語為“der Vortrag über die Weltlage”,“朝南的房間”翻譯成德語為“das Zimmer nach Süden”,“對他的恨”翻譯成德語為“der Hass gegen ihn”。
3.在表達時間和地點時,中文總是遵循大概念在前的規則,若同時有時間和地點的短語,漢語總是時間先于地點,德語則相反
例如:中文“公元2010年1月1日于漢堡”翻譯成德語為“Hamburg,den 1.Jan.2010”,中文“北京大學物理系”翻譯成德語為“die Physikfakult?t der Universit?t Beijing”。此外,漢語里總是說“十月初”“十月中”“十月底”“年頭”“年尾”,德語里則為“Anfang Oktober”“Mitte Oktober”“Ende Oktober”“Anfang des Jahres”“Ende des Jahres”。
4.漢德語都有各自的固定表達,互譯要遵循目的語的要求,不能違背目的語的詞序
在進行相應的互譯時,我們一定要遵循目的語的要求,不能違背目的語的詞序。例如,中文里只講:師生、工農兵、工廠和農村、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男女青年、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德語里只講:Entenbraten,methodisch-didaktiscb,leben und leben lassen,faul,dumm und gefr?βig,beschreiben und analysieren,weit und breit,hin und her等等。
四 漢德互譯是直譯還是意譯
古往今來,關于翻譯定名的原則有很多:1889年,嚴復在《天演論》里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傅雷先生提出了“神似說”;錢鐘書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則提出了“入化說”。有不少人提出翻譯只能是一種意譯。實際上,在翻譯時是直譯還是意譯,這在西方有過長期的論爭[7],國內也不例外。漢德術語互譯時該采用直譯(w?rtliche übersetzung)還是意譯(sinngem?βe übersetzung)呢?筆者認為要視情況而定,因為翻譯定名的目的是為了傳達原文的思想,而直譯和意譯都只是方法。
總體來說,應用性語體(比如科技文獻)因詞義明確,大多只需直譯,例如:“Obwohl unser Auge kein Licht mehr wahrnimmt,ist noch eine Strahlung vorhanden,die als ultraviolettes Licht bezeichnet wird”,這句話可直譯為“盡管我們的眼睛不再覺察到光,但仍然存在一種被稱之為紫外線的射線”。又比如:“Normale Korrosion:In Deutschland(Industriegegenden)betr?gt Rostungsge-schwindigkeit im Jahr etwa 0.5 kg/m2,in l?ndlichen Gegenden 0.125 kg/m2,j?hrlich Verlust über 120 000 t Stahl”,這句話可直譯為“正常腐蝕:在德國(工業地區)年腐蝕速度為0.5公斤/平方米,在農村,則為0.125公斤/平方米,年損失超過120 000噸鋼”。但是,文藝性語體在互譯時卻不一定總能直譯,需要意譯。
針對是直譯還是意譯的問題,西方翻譯界提出了“等效翻譯”的原則,強調譯作對受眾的影響要與原作對受眾的影響等效,其著眼點是兩種語言背后的歷史文化、語言習慣、思想感情的傾向性,而非糾纏于千差萬別的個性。在實際的翻譯中,能堅持等效翻譯的原則,就能更好地實現譯作與原作的形似與神似。其中,奈達博士提出了“動態對等”概念很吸引人注目[8]。國內還出現了歸化與異化之爭,王東風先生認為這是直譯與意譯之爭的延伸[9]。
總之,采取什么翻譯方法和理論,這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以諾德為代表的“功能翻譯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新的翻譯理論[10]。在文學翻譯方面,該理論有很強的生命力,首先,它降低了源語文本的地位;其次,它重視接受者;最后,它提升了譯者的主動性。例如,魯迅先生作品《孔已己》里有一段情節:“‘茴香豆’的‘茴’字不是草字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么”[11]。在翻譯這句話的時候,“草字頭”和“茴”對德語國家的讀者而言是陌生的,譯者用Ich zeichnete ihm das Wort hin(我寫給他看,“茴”字怎樣寫),這就巧妙解決因文化的不同造成的不可譯的問題。
五 結論
總之,漢德術語互譯是一項系統的工程,不僅涉及各種學科,還是一項接力事業,必須由通曉漢德術語的中外人士來完成。語言本身也是在不斷發展和變化的,我們對漢德術語互譯的規律性認識不一定能夠反映出語言不斷變化的實際情況。所以,對漢德術語互譯規律之探索不是靠幾代人、幾篇文章就能解決的,然而,每一次努力、每一次探索必將縮短我們對漢德互譯規律由不知到知之的距離。
[1]Kunkel-Razum,Kathrin et al.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w rterbuch[Z].überarbeitete Auflage.Mannheim.Leipzig.Wien.Zürich:Dudenverlag,2010:7.
[2]Kunkel-Razum,Kathrin et al.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w rterbuch[Z].überarbeitete Auflage.Mannheim.Leipzig.Wien.Zürich:Dudenverlag,2003:5.
[3]凌原.漢英雙語現代漢語詞典[Z].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
[4]新漢德詞典編寫組.新漢德詞典[Z].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5]第四機械工業部標準化研究所.可靠性基礎[Z].北京:第四機械工業部.
[6]Dreehsen,Birgit.Qualit tssicherung bei EDV-Systemen,Auswahl,Einsatz und Betrieb von Hard-und-Software[M].Duesseldorf:VDI Verlag,1996.
[7]劉重德.文學翻譯十講[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公司,1991.
[8]譚載喜.奈達論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公司,1991.
[9]王東風.歸化與異化:矛與盾的交鋒[J].中國翻譯,2002(5):24-26.
[10]諾德C.譯者有所為[M].張美芳,王克菲,主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11]魯迅.吶喊(Aufruf zum Kampf)[M].佚名譯者.北京:外文出版社,2002.
[12]馮世則.忠實于何?——百年來翻譯理論論戰若干問題的思考[J].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94(1):103 -116.
[13]郭建中.文化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9.
[14]黃天源.直譯和意譯新探[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8(1):74-78.
[15]李全安.“直譯與意譯之爭是一場什么樣的爭論[J].中國翻譯,1990(5):18-22.
[16]劉宓慶.漢英對比與翻譯(修訂本)[M].譯論叢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17]劉宓慶.文體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
[18]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M].書林譯學叢書之六.臺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19]申丹.論翻譯中的形式對等[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7(2):34-39.
[20]孫致禮.文學翻譯應該貫徹對立統一原則[J].中國翻譯,1993(4):4-7.
[21]許淵沖.翻譯的藝術(論文集)[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
[22]夏征農.辭海1989年縮印本[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
[23]王京平.德語翻譯教學新概念——翻譯課的設計與實施[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0.
[24]鄒培國.現代德語構詞法[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4.
[25]Bolling,Sigfrid.Technik[M].Berlin: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1991.
[26]Stner K,Erich.Das fliegende Klassenzimmer[M].Aufl.Hamburg:Dressler Verlag,2006:162.
[27]Kiefer,Philip.Internet-Begriffe einfach erkl?rt[J].Düsseldorf,DATA BECKER,2008.
[28]Stepanowa,Fleischer M D,Wolfgang.Grundzüge der deutschen Wortbildung[M].Leipzig:VEB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1985.
Mutual Translation of German-Chinese Terms
LI Dongliang GUO Jian
Chinese and German belong to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y and the difference has brought a lot of difficulties to the mutual translation.The author discusses mutual translation issues of German-Chinese terms,such as the corresponding,diction,subsequence,mutual translation,etc.
Chinese,German,terms,mutual translation
N04;H059
A
1673-8578(2012)01-0031-05
2011-06-30
黎東良(1963—),男,湖北黃梅人,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德英語對比語言學,術語與翻譯,語言與文化等。通信方式:davidlehman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