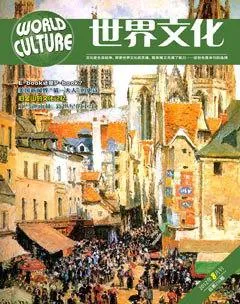天才藝術家:還有多少心思沒對世人說
以前,人們會縱容、愛惜地恭維藝術家都是來自天國的精華,意思是說對于這些人的舉止言談,大可不必在意。如此“忽略”他們,我們將錯過多少異樣的風景啊。
作者手記
對于天才的藝術家,在不同的文化區域中,被人們視為特異的事情,確實是大量存在著的,偶然的巧合,確實可以說明一個規律性的問題,但是在具體的事件上,人們一般都會在享受這份被視為靈異現象帶來的奇妙感覺。拉斐爾·桑蒂出生在1483年4月6日,這一天是耶穌受難日——宗教上一個悲壯的日子。而他的死亡日期也是一個4月6日,那是1520年4月6日。
拉斐爾的父母就像為他而來到世上,他的母親把他哺育到8歲后,去世了。他的父親又將他教育了三年,也離他而去。現在從零星的記載來看,在他父親活著的時候,他已經能從事藝術的工作了。好了,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拉斐爾的父母在塵世完成了最初對這位天才的教養之后,被上帝召回了天國,而“拉斐爾”正是《圣經》中天使的名字,事情果真如此?還是完全來自歷史的巧合?我們無從知曉。
作為一位敏感,并且極富藝術才華的畫家,實在是無從知道拉斐爾桑蒂內心深處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孤兒身份,他也許真的讓自己相信,其有著非同一般的身世。有一個場面是被真實記載下來的,畫家在彌留之際,讓人將他畫的《基督顯圣容》(1518—1520)搬到床前,這是在堅定自己內心編造的他來自天國這個神話嗎?畫家短暫且輝煌的生命中,他一直是異性的寵兒,與許多女人交織在一起,這是年輕畫家一直在苦苦搜尋母愛的行為嗎?他塑造的圣母形象,有著一般畫家筆下所缺少的世俗女性的完美性,成為那個時期人文主義藝術的典范,或者說正是這一點,反映出他內心中戀母情結比一般的人更為強烈?
天才們的心思很難讓人讀懂,他們的天賦異稟已經與一般人有了不小的距離,再加上一些傳奇的身世,更使他們有意無意間為自身營造了獨特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在我們看他們時,就包含了頗多迷離的色彩。列奧納多·達·芬奇的研究者通過蛛絲馬跡的分析,認為這位藝術家有同性戀的傾向,這種結論真不好置以可否。
先簡單說一下達·芬奇的身世,他有一個私生子的身份,研究發現其母親的身份低下,他在很小的時候就與母親分開了。達芬奇是一個早熟的天才,14歲做學徒時已經畫得相當出色了。對于這樣的孩子,敏感應該是他最明顯的特質,這時的他可能就是要用自己的才能證明他的出色與其母親的了不起,也可以說他沒有真正的童年。及至年長,他的心思完全放在對新知識的研究和設計構想上,這有他大量的手稿為證,在那個普通人猶不知科學為何物的時代,沒有像虔誠的教士侍奉上帝一樣,沒有把全副精力投入其中的獻身精神,他的科學成就仍令我們現代人瞠目結舌。
在達·芬奇身上兼具了細膩與嚴謹的氣質,也可以把這種特質解釋為感性思維與理性思考的表現,或者解釋成母性和父性襟懷,當他收留流浪的綽號“撇旦的翅膀”薩萊為學徒時,當看到少年身上的頑劣、聰明、單純和無所畏懼等等混雜在一起時,還有就是其相貌與他的理想美——他們有相像的地方(應該說達·芬奇有明顯的自戀傾向),他看到了自己少年時代的缺失,這時,在他的身上,多少年尋覓的母愛轉化成一種母性的情結,對父親的諸多不滿(包括遺棄了自己的母親),轉化為“我”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父親。人的特定情感就在一個適合的際遇中得到了釋放,而特殊的感情紐帶很多時候還是單向的,無疑也會在這個人的情感與思想中成為一種糾結,呈現出復雜的狀態。列奧納多·達·芬奇與薩萊之間的關系,自然也就成為后人的一種錯讀。
藝術家都有一個敏感的心靈,其實何止敏感,深入地了解到他們的內心,有的時候還極為脆弱。雕刻家羅丹與畫家莫奈有很好的交往,他們曾在一起共同辦過印象派展覽,并且終生來往。而羅丹對莫奈的晚年生活頗有微辭,認為他的生活太過于安逸享受了,畫家有自己漂亮的大花園和寬敞巨大的畫室,顯示著主人的富足。
莫奈也是人,我們先不要看他的物質生活,這些對于他來說,也許都是為了滿足心理的某種需要,并不能代表他的人生趣味。他的繪畫需要陽光,明媚的光線一直要投射到畫家的心里,擯除掉心理創傷為他帶來的精神陰影。藝術家敏感的心靈為他作出了選擇,興許他要比其他任何人都熱衷于改善自己的物質條件,以此撫平難以復合的心理重創。
他的年輕時代生活極為拮據,不幸的妻子就因患病得不到很好的醫治而去世。對于自己摯愛妻子的離世,內心的傷痛也許只有他本人知道。還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就在莫奈愛妻彌留之際,她的膚色開始起著色澤的變化了——血色在漸漸地退去,這個現象引起了畫家的密切關注,不禁脫口讀出妻子臉上的色調變化,而忽略了所在場合。作為一個“印象主義”的創始者(印象主義因他的畫作《日出·印象》而得名),對色彩變化的敏感就是他的職業病了。
你道莫奈是個迂腐的人嗎?錯了,印象畫派剛出道時,人們不理解,所以很少購買這些畫家的畫,莫奈把畫放到畫店里,用不了多久,就被賣出了,于是引起了買家的注意。原來是畫家自己托人買回了自己的作品,為的是不要長久地滯留在畫店里,給人以沒人要的印象。他的畫家朋友也公認莫奈有著商人般精明的頭腦。
對于藝術家來說,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的酷愛,就是其行為方式躍出世俗的塵格,在常人眼中就顯得不合時宜,去菲薄這樣的人,只能說明這種非議缺少一種文化的境界。藝術家們就是這樣生活的一群。
莫奈在他晚年繪制了巨幅創作《睡蓮》,其中光影的燦爛繽紛,成為他的登峰之作。他的《干草垛》系列也成為畫家探索光線變化的力作,干草垛成為他的鐘愛。畫面上幾乎表現了光線在瞬間的變化,莫奈用自己的心理感悟,為人們創造了視覺的盛宴。在印象派的作品前,文學性的描述,哲理的分析統統可以置于腦后,你只需要帶眼睛來看就可以了,也正是這一點,他才需要平穩客觀的心情來觀察自然。莫奈要說出自己的真實,他鐘情于自然,而并非要表現豪華家具上的迷離光線,以顯示其物質生活的優渥,他一生始終駐留在自己的藝術表達方式上,為描繪自然中的光而達到苛刻的程度,以致每隔20分鐘就要在另一張畫布作畫,來適應不同時間段的光線變化。
莫奈對物質的需求,正反映出他對藝術的態度:不要再因為不幸而令情感挫傷,影響到對自然的觀察。
真說不好邏輯的思考與表述是為天才們的戲法,還是他們的特異思考顯露出的人之常情,會令我們會心地莞爾一笑。薩爾瓦多·達利講述了自己的一段趣聞:
我獻身于各種想干和不想干的古怪行為。我33歲了。我剛接到一位最杰出的年輕精神病醫生的電話。他才在《米諾陶》中讀到我關于“偏執狂活動的各種內在機制”的論文,他向我表示祝賀,我對這樣一個題目的正確科學認識(一般而言,這是極為罕見的)令他吃驚。他想見見我,當面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我們商定當晚在我位于巴黎高蓋街的畫室里會面。這臨近的會面使我十分激動,整個下午,我都在努力起草一份我們要談的事情的大綱。實際上,我滿意我的各種觀點(就連超現實主義團體中最親近的朋友們,也把它們看成是自相矛盾的心血來潮的產物)會在一種科學的環境中加以考慮。我一心想使我們初次交換意見這件事能正規地、甚至有幾分莊嚴地進行。在等待年輕的精神病醫生到來之際,我繼續憑記憶畫一幅肖像,我正在把它畫成諾埃依子爵夫人。這幅用銅版制作的畫,搞起來很難,為了看清我畫在光潔如鏡的褐色銅片表面上的素描,我注意到在反光最明亮的地方能清楚地辨認出我作品的細節。因此我在鼻尖上貼上一塊三厘米的方形白紙片來作畫,這塊白紙片的反光完美地顯示出我的素描。
六點整,有人按門鈴。我收起銅版,給來訪者打開門。雅克·拉康進來了,我們馬上開始一場非常緊湊的專業性討論我們驚奇地發現,由于同樣的原因,我們的觀點與公認的構造主義論斷是對立的、在兩個小時內,我們以真正激動的辯證方式談論著。雅克·拉康離開時,答應定期跟我接觸,以便交換意見。
他走后,我在畫室里來回踱步,盡力概括我們的談話內容,更客觀地估量我們之間暴露出來的少數不同點。可有一點令我困惑不解,那就是這位年輕的精神病醫生不時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看,這令我不安。仿佛一種奇怪的微笑想掀開他的嘴唇,而他克制著不讓自己顯出驚奇來。他在致力于對我的面貌(那些使我心靈激動的想法讓它富于生氣)進行形態學研究嗎?當我去洗手時(這個時刻正是人們能最清楚地弄明白不論什么問題的時刻),我解開了這個謎。不過這次是鏡子給了我答案。在那兩個小時內,我忘記除掉貼在鼻尖上的小白方紙片,以一種客觀嚴肅的語調,極為認真地談論著先驗的問題,卻毫沒料到我鼻子的可笑樣子!可有哪個犬儒主義的故弄玄虛者能把這個角色演到底呢?
從上面引用的畫家本人文字來看,薩·達利是在標榜自己的一生將異于常人嗎?我看他正常得很!他的天才始終沒有把他弄神經,藝術只成為他一生戲弄世人的超級把戲,而沒有成為他的生命。一個最好的證據就是在他的晚年,他請年輕的藝術家為他代筆了,事情被揭露出來之后,世人為之嘩然。這在凡·高的內心想象中,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有烏鴉盤旋的麥田》是文森特·凡·高的絕筆,面對這幅繪畫,應該請心理學家為我們解讀其中的死亡氣息。實在地說,這位畫家的人生充滿了苦難和命運的捉弄,但是他都以對自己藝術的堅強信念,堅韌地活著,可以說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之火,點燃了藝術的光焰。沒有人真正理解他的藝術,兄弟關照他,在他看來或許只是感情的慰藉與支持,摯友保羅高更遠離他而去,到了太平洋上的小島上生活,他再也找不到打架宣泄的對手了,他的理性與感性長久以來一直產生著強烈的對抗,繪畫與文字也不能排解越來越擁塞在胸中的積郁,這一切有可能連畫家本人也不能清晰地察覺。
在看似一切如舊的生活軌跡中,結果就會突然降臨,他日常生活中一個微不足道的事情,就突然使他的思考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他是將自己視為麥田上的烏鴉了嗎?因為它們在盜食成熟的麥穗,他在扣動扳機之前肯定自己是一個完全無用的人了?心靈就在這一刻被捻為灰燼,這一切也都是猜測而已。
奧地利畫家埃貢·席勒的藝術風格就像奇異的流星,光華燁燁,1918年維也納發生大規模的流行感冒,死了很多人,席勒就是一個極為神經質的畫家,他害怕極了,把門窗關嚴,終日恐懼地待在屋中,然而死亡還是降臨了,他在28歲的美好年華即回歸天國。
畫家席勒的死,他內心神經質的易脆也許就是其擺脫不了的夢魘。
讀美術史之余,關注此類問題,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去認識藝術家們的藝術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