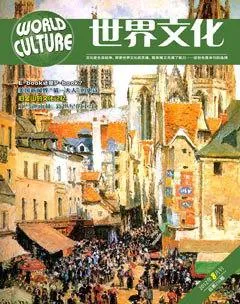讀山颯《柳的四生》
又收到閻純德寄贈的書,除了他撰寫或主編的著作外,還有一本帶腰封的裝幀十分新穎的《柳的四生》,作者山颯。腰封上印著一行醒目的字:法國前總統希拉克親自致信山颯——您的語言,您的故事以及您的微妙的思想使我感動。山颯是誰?心中不由充滿疑惑:純德為何將它和自己的新著一起寄給我們?
翻看作者簡介:山颯Shah Sa,旅法作家、畫家。本名閻妮。生于北京,現居巴黎……這才恍然大悟:這山颯原來就是純德的寶貝女兒閻妮呀!
純德是我們北大學友,河南濮陽人,人北大前便以“鄉子”、“濮之陽”等筆名寫詩。他的詩讀起來就像感受到濮陽鄉野吹來的縷縷清風,質樸、厚重,又靈動、清新,在燕園詩壇是獨樹一幟的。他也是校田徑隊員,課余在北大東操場上常可看到他矯健的身影。對枯燥的訓練,他也像寫詩那樣投入,除完成教練規定的課目外,他還常刻意為自己加碼:在腿上綁上沙袋,再套上沙背心,一圈一圈練習負重跑。他似乎對自己從事的每一件事,都在心中預設一個目標,執著、勤奮,一絲不茍地去追求。可以想見這位學友今后對人生、對事業,也會同樣嚴肅、認真。
畢業后,大家在各自崗位上忙碌,自然不會像在學校時經常見面,有時從報刊上讀到彼此詩文,都會格外欣喜。而“文革”一來,彼此連這點音訊也得不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回國休假時從父親與純德通信中,得知他仍在北京語言學院任教。父親對他課余不惜耗費大量時間、精力,主持編撰我國第一部《中國文學家辭典》贊許有加:“您是學人,非一般出版家,我深深敬重。”我們還得知,他于1974年被派往巴黎教授中國語言文學。回國后,應出版社少兒組編輯之約,撰寫了散文集《在法國的日子里》,為“文革”十年在閉關鎖國中生長的青少年,打開了一窗觀察、了解法國與西方社會的窗口,不僅得到茅盾、嚴文井等著名作家的支持,也受到青少年和廣大讀者的歡迎。從那以后,我們雖恢復了聯系,但見面機會仍不多。我們知道他后來又應聘到法國、意大利多所大學任教。繼《作家的足跡》《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研究》等著作之后,還出版過《伊甸園之夢》《歐羅巴一個迷人的故事》《在巴黎的天空下》等詩集、散文集。他的夫人李楊當年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才女,在他們夫婦熏陶與栽培下,他們的天資聰慧的愛女閻妮,自幼便習書法、學詩、操琴,10歲出版第一本詩集,14歲就成為作協最年輕的會員……
上世紀80年代應邀去純德家時,他的夫人和女兒都不在,只有閻妮的小花貓在一旁作陪。這貓大約平時備受閻妮寵愛,跳上、跳下,一刻也閑不住,還會把頭伸進閻妮的水杯里喝水。它既是閻妮的玩伴,也常激發她的靈感:她曾寫過一首《鼠年,致老鼠》的詩,告誡老鼠:“自己勞動,干事不要偷偷摸摸”,還打算把貓介紹給老鼠做朋友。寫得天真活潑,充滿童趣,在全國少年兒童詩歌大賽中榮膺一等獎。時光荏苒,仿佛眨眼之間,當年那個準備讓貓和老鼠做朋友的小詩人,已經變成享譽法國的作家,而且取了個頗有些怪異的“山颯”的筆名,令我們殊感意外。
中國人對柳是情有獨鐘的,不僅因為春風里它那萬千翠碧絲絳隨風舞動時的婀娜多姿的身影,更由于它對環境不苛求,插一根枝條就能隨遇而安的脾性,千百年來,多少騷人墨客為我們留下過多少膾炙人口的詩句:從《詩經·采薇》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到魯迅先生的“卻折垂楊送歸客,心隨東棹憶華年”……柳已成為中國人習慣的寄托情感與思緒的某種特殊的文化載體。我們很想知道,而今,在閻妮——山颯的筆下,它又象征著什么呢?正巧,那段時間我們得到一個去鼓浪嶼療養的機會,在整理行裝時,特意把這本《柳的四生》帶了去。
《柳的四生》正是借用柳樹插一枝即可再生的特性和千百年來民間關于人前身后世、輪回無常的傳說,圍繞“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哲學命題,通過精心編排的柳、鬼、琴、仙人、貴人、劍、俗人、月亮八個章節,用時空交錯的剪輯手法,創作的一部當下頗為流行的“穿越小說”。它不同于“意識流”、“先鋒派”,對于我們這些習慣于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敘事手法的人來說,初看時,頗覺云遮霧罩,撲朔迷離。比如第一章明明寫的是明末一位前皇族后裔所生的一對孿生兄妹春毅、春寧,一天夜里春寧聽了嬤嬤給她講人生生死輪回,幻想來生變一只蝴蝶。半夜她被春毅搖醒,借著風力隨哥哥飛到洞庭湖,從港灣里泊著的一艘船的窗口飛進船艙,見到一個和春毅一般大小的男孩兒重陽。第二章的敘事便從這從小就熟讀詩書的富商之子重陽展開,說他在岳陽樓下遇一道人,道人說他日后會有不期之遇,并揚名天下,富可敵國……卻預言這一切不過是過眼云煙。重陽后來經歷了家道中落、父母亡故、姐妹遠嫁等變故,窮困潦倒。一位由柳樹幻化的女子綠衣以身相許,令他凄清的生活發生了重大改變。綠衣不求錦衣玉食,唯愿夫妻長相廝守,但重陽卻一心苦讀準備科考。綠衣無奈,明知是永訣,也強忍痛苦,送重陽上路……正當讀者還在為春毅、春寧,重陽、綠衣的命運糾結時,第四章卻把讀者帶到了現代的北京,主人公靜兒是當今處處可見的“白領”、“女強人”,大學畢業后,到紐約讀MBA,后來幫朋友忙,代理一個品牌。沒想到越做越大,朋友退出了,這公司倒成了她自己的事業。她像一只不停地旋轉的陀螺,被鞭子抽著,身不由己地忙策劃,忙洽談、忙辦展、忙推銷,今天北京,明天新加坡……盡管她“少女時代就渴望愛情,結婚,生子”,但“這人生之路,走起來才發現是相反的一條”……然而,無論時空如何變幻,從靜兒以及她的日本友人森田身上,讀者也都分明看到綠衣、重陽、春寧、春毅的身影。
我們在鼓浪嶼,正趕上時晴時雨,陰晴不定的季節。雨天,正好靜坐窗前,伴著淅淅瀝瀝的雨聲,細讀《柳的四生》。隨著書中人物及他們各自的命運、經歷,去思考、領悟與感知:什么是生命,什么是人生……待天氣轉晴,我們便又穿行在鼓浪嶼高高低低、彎彎曲曲的小巷,去探訪那一座座有近百年歷史的長著榕樹、香樟、鳳凰木和開滿三葉梅、炮仗花的院落,去感受它那深厚的文化蘊藉與人世滄桑。然而,許是受到山颯的那種將古、今,神、鬼,人、物,隨意穿越、變幻的敘事手法的影響,頭腦里不期然地從眼前事物衍生出許多有趣的聯想。譬如在晃巖路與福建路交匯小廣場上,在雞蛋花樹下那賣雞蛋花的文靜的姑娘會是誰演化的呢?春寧還是綠衣?菽莊花園外藍色遮陽傘下,那高高的戴著墨鏡和一頂美國西部牛仔式的帽子,悠然自得地彈著吉他的音樂人志愿者,會是現今的春毅,重陽,抑或是森田嗎?在龍頭街新華書店對面,有一家名叫“謝馥春”的十分時尚的化妝品店,門旁有一副對聯:胭脂水粉梅妝影,冰麝龍涎醉客心。小店同它近旁常常顧客盈門的老字號“黃勝記肉松店”,“葉氏屋仔麻糍”或80后、90后青年男女最愛光顧的賣茯苓糕、仙草汁和水果、香腸、土豆泥和鳳梨制的乞士的“小馬哥乞士馬鈴薯”店的格調迥然不同。它時尚、清雅、別致,出入也多是靜兒這類的高級“白領”。由于購買力的限制,一般80后、90后女孩兒是不會輕易問津的。不知道店里有沒有靜兒欲在香港亞洲化妝品大展上重點推出的“最新款化妝氧氣瓶”?我們真想請山颯轉告靜兒:鼓浪嶼每天游客如織的龍頭街上,也有很旺的人氣與商機,她不妨來這家名叫“謝馥春”的化妝品店考察考察……
我們原以為純德多次赴國外授課、講學,是國內外知名學者,靠他的關照,女兒閻妮取得這樣的成就,并不意外。然而,事實并非如此。1990年閻妮北大附中畢業時,由于成績優異,被保送北大,但隨即又獲得每月4000法郎的去法國留學的獎學金。走父母走過的路,讀北大中文系,曾是她的夢想,而且,對她來說,這條路顯然要平坦得多。而去法國留學,僅靠那點獎學金是遠遠不夠的。父母不是大款,經濟上不能給她多少支持,得靠自己打拼。可貴的是閻妮自幼就承襲了父母在困難面前從不低頭的秉性,毅然決定去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獨自去開創人生的路。到法國后,先在巴黎阿爾薩斯中學學法語,兩年后轉入法蘭西神學院學哲學。她說她“第一次感到了貧窮”,因為在法國是不許隨意打工的,而“打黑工”,不僅錢少,也沒有保障。語言還不過關,又舉目無親,孤獨、想家……她只能咬牙隱忍著,有一點點空余,就埋頭苦讀,一本《法漢字典》都翻爛了。由于學費太貴,她連語言學院也沒上過,卻硬靠四年苦讀,打下了獨立用法語寫作的基礎。她認為留學最可寶貴的是讓她“尋找到了個人的獨立——命運上的獨立”。
在法蘭西神學院學習時,她認識了88歲高齡的抽象派畫家巴爾蒂斯日藉夫人的女兒春美,經春美推薦,她毅然輟學去瑞士擔任了巴爾蒂斯的秘書。這又是她人生路上一次重要抉擇。初到法國的四年,她為了生活被迫中止了寫作,而對她來說“不寫作就不是我自己”,擔任巴爾蒂斯的助手后,她又可以用工余時間寫作了,她多么高興啊!她不僅要寫,而且還要用法語寫!那時,她法語表述能力雖有一定水平,但要寫出法國人認可的小說畢竟不那么簡單。因為“用一種與母語截然不同的語言寫作,因表達受限制而備覺痛苦,猶如一場需要投入整個生命的冒險”。好不容易寫成的章節,法國朋友看了卻說:“寫得不錯,但……這不是法語。”而她卻沒有放棄,在巴爾蒂斯的大木屋里,依舊堅持用法語寫她的小說。處世低調,為人質樸、謹嚴的老藝術家對閻妮也鐘愛有加,常給她談人生,談藝術。她牢牢記住巴爾蒂斯的教誨:“不要試圖模仿夏爾多布里昂(法浪漫派作家),你永遠也成不了夏爾多布里昂,要走自己的路。”她決心吸納法國與西方文化的優長,寫自己熟悉的富有中國歷史、文化積淀的小說,在中法文化交流上闖一條新路。
她終于漸漸擺脫語言表述與思維邏輯上的隔膜與生澀,用法語思維與書寫不再是疙疙瘩瘩,而漸漸成為一種心靈的享受與宣泄。而且,正由于她有著豐厚的中國文化積累,寫作時,有選擇地將中國人習慣的思維、審美與行文方式,融入文字里,這兩種不同文化、語境的微妙交融,有時竟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法國讀者對她某些不合自己日常習慣的用詞與表示方式,并不苛求,反而覺得她行文與敘述含一種富有東方韻味的新鮮感與古典美。這或許正是她的作品為法國讀者接納并深受歡迎的原因。除了《柳的四生》之外,她還用法語創作了《天安門》《圍棋少女》《女皇》等多部長篇小說,并被轉譯成多種文字。與此同時,她還潛心作畫,她的畫作與她的小說一樣,既有西方文化藝術的特色,又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特有的韻味。據說,在法國人們心目中,山颯已成為與著名畫家趙無極齊名的現代中國留法藝術家。2009年她榮獲法國文化藝術騎士勛位。
《柳的四生》是山颯十多年前創作的,難免有些幼稚與粗糙。然而,卻沒有時下流行的某些“穿越作品”的荒誕不經。她并非嘩眾取寵,她關注的是人生的大主題,讓讀者為故事人物的經歷、命運糾結的同時,也啟迪人們思考:人生與生命的價值。
我們高興地看到,純德曾作為中國文化的使者,應邀去國外施教多年,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過重要貢獻。現在仍孜孜以求主持并參與世界漢學史的研究。而女兒閻妮——山颯也疾步追趕上來,而且,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實在是值得祝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