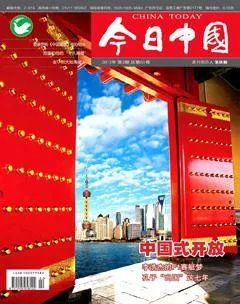我親歷的《中國建設》創辦始末
我于1949年參加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參加了英文雙月刊《中國建設》雜志創辦全過程,歷任《中國建設》辦公室主任、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在《中國建設》(現稱《今日中國》)雜志即將迎來60周年之際,自己所經歷《中國建設》創辦始末的點滴往事,一一涌現在眼前。
《中國建設》雜志的誕生
自新中國成立后,在思考未來工作目標與重點時,宋慶齡希望加強自己擅長的對外宣傳工作,在《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抗戰時正式創辦于1939年的英文刊物,以下簡稱《保盟通訊》)成功向世界發布中國真實信息的工作經驗基礎上,著手成立國際宣傳機構,突破西方新聞封鎖,以非官方渠道,將新中國的信息傳播到全世界。
為此,宋慶齡做了較充分的準備,并接連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寫了多封信與正式報告,還委派專人前往北京匯報,急切地盼望得到他的意見。
1950年1明,周恩來建議宋慶齡可以先辦個對外的刊物。他認為,應當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紹新中國的情況。建議宋慶齡以她與各國人民建立友誼的長期經歷和豐富經驗創辦一本對外宣傳的刊物。
宋慶齡完全同意。于是1951年1月,宋慶齡在北京方巾巷寓所會見了剛從美國回國的陳翰笙、顧淑型夫婦,商談辦刊事宜。并且委托陳翰笙到上海與金仲華一起,依靠中國福利會的力量籌辦刊物。同時,宋慶齡邀請正在美國的愛潑斯坦、邱茉莉夫婦和耿麗淑盡快返回中國參加辦刊。她認為愛潑斯坦是最佳編輯人選,有豐富的新聞工作經驗與編輯《保盟通訊》的經歷。耿麗淑在外有廣泛的人脈資源與推廣經驗。因此,讓耿麗淑負責雜志的推廣發行工作也是十分稱職的。
宋慶齡決定為雜志取名為《ChinaReconstructs》,中文原意是中國的重建。這個名字是有深刻意義的。因為孫中山先生曾經辦過一個名為《建設》的刊物。《中國建設》這個名字不僅標明這個雜志的主旨是報道新中國的建設,而且還借以紀念孫中山先生。
1951年8月30日,宋慶齡在上海常熟路157號中國福利會會議室主持《中國建設》籌備會議。會議確定了刊物的編輯方針、讀者對象及報道內容,決定“這本雙月刊的讀者對象是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國家的進步人士和自由職業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國的人。它特別針對那些真誠要求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進的自由職業者和科學藝術工作者”。刊物將重點報道中國社會、經濟、文教、救濟和福利方面的發展,以使國外最廣泛的階層了解新中國建設的進展以及人民為此所進行的努力。
在那次會議上,宋慶齡提出要成立一個由社會知名人士組成的編委會,編委會成員也是由宋慶齡提出的。主任:金仲華(上海市副市長、國際問題專家),副主任陳翰笙(著名經濟學家)。其他編委委員是:錢端升(政治學家)、李德全(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長)等等。她還提出,邀請耿麗淑到中國,從事雜志的推廣發行。宋慶齡強調,出版英文版的《中國建設》要繼承和發揚它的前身《保盟通訊》向全世界各地傳播中國真實情況的優良傳統。
宋慶齡對編輯方針有明確的要求,她要求多寫人民群眾的努力和業績,因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她還強調實事求是。根據宋慶齡的要求,編輯部作出具體規定:每期必須有一篇觀點新穎的文章,一篇扎實的文章,還要有一篇生動的文章。具體表現為,雜志按既定編輯方針,在籌劃各期報道觀點與內容時,強調:寫好每期首篇的“致讀者”,結合各期的重點內容,進行分析與提升,表明雜志對當前中外形勢吸重大事件的鮮明觀點(宋慶齡曾親自寫過《致讀者》);深度報道國內的熱點和重點問題,多由本刊記者深入采寫撰稿,以主題文章或若干文章從各個角度透析主題;約請權威人士或專家學者撰寫通俗而觀點鮮明的重要文章(創刊初期宋慶齡、金仲華、陳翰笙及社會知名編委均親自為雜志撰稿;以后也很重視約請各界專家學者撰稿或訪談)。
1952年《中國建設》第1期正式出版,為英文雙月刊(1955年改為月刊),第1期印刷1萬冊,向國內外發行。
雜志創刊號的彩色封面為土地改革中翻身農民的喜悅形象;封底為木刻,內容為重建的鋼鐵基地鞍鋼。發刊詞宣告:“正如《中國建設》的刊名表明,它將集中報道我國的重建和新的建設以及我國人民的生活的變化……它將用權威的文章、生動的特寫、典型的圖片、插圖和表格來記錄中國人民的生活,并將報道他們是如何克服困難和解決問題的。”
創刊號上發表了宋慶齡的文章《福利事業與世界和平》,還有其他知名人士的文章,如陳翰笙的《中國工業的新發展》、李德全的《人民的保健事業》、趙樸初的《城市的善后救濟工作》、傅作義的《制止洪水為害》等。
雜志的推廣與發行
宋慶齡十分重視雜志的推廣與發行。首先,宋慶齡推舉耿麗淑返回中國,專門從事推廣與發行工作。其次,宋慶齡堅持主張走自己獨立發行的路。當時,所有對外的刊物、書籍皆依靠國際書店,而宋慶齡堅持強調雜志的民間性與高效率,要求自己發行,以區別于官方渠道。第三,宋慶齡堅持親自為雜志寫文章,向知名人士約稿,并以林泰的名字向國外友人郵寄每期雜志,帶頭做推廣發行工作。
自己發行的好處在于:一、與讀者直接聯系。針對讀者來信,我們及時了解到讀者的愿望與口味,幫助編輯調整采稿的方向與內容。二、我們對來信做到每信必復,而且規定回信不能超過兩周。還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特殊的需要,如提供旅游信息、代購物品等,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三、使發行與推廣更加深入。我們堅持自己負責發行工作,可以根據雜志的特點策劃推廣發行方案,開展有針對性的推廣活動。當時,全社上下都重視發行與推廣工作,記得我們曾主動到各國際會議的會場去現場設攤,宣傳推廣我們的雜志。
事實證明,宋慶齡的決定是對的。《中國建設》的發行量在當時是最大的。那個年代,只有《中國建設》能夠打入美國市場,在美國的書店、報攤上公開出售。當然,《中國建設》雜志的非官方性質很重要,這是宋慶齡特別強調的。
周恩來總理也多次對我們強調堅持非官方這個問題,告誡我們,一定要明確,《中國建設》是孫夫人出版的雜志,不是官方喉舌,不要唱高調,雜志一定要符合宋慶齡的語言與風格,政治性不要強。周總理還告誡我們:要內外有別,對內宣傳與對外宣傳要有區別。要有的放矢,考慮到國外讀者的接受程度。要堅持自己的風格與特色,也就是宋慶齡的風格與特色。陳毅和廖承志也多次強調,要求我們報道新中國各方面真實的信息,陳毅曾給雜志題詞“事實勝于雄辯”,就是讓我們用事實來講話。我們一直把這些指示作為雜志的指導方針。
宋慶齡對雜志的關心
記得早期中國福利會工作人員還不多的時候,宋慶齡經常到辦公室來,跟大家聚一聚,在花園里一起喝喝咖啡、喝喝茶、聊聊天。她給我的印象是非常親切,就像慈母一樣。
宋慶齡對雜志的方方面面都很關注。她細心閱讀每期雜志,及時把她的意見與想法告訴我們。她始終關心雜志的編輯方針并親自撰寫重要文章,前后共為雜志寫了三十多篇文章,內容題材廣泛。她的文章不但文字優美流暢,而且能做到深入淺出,文風非常好。
每期雜志我們都送給宋慶齡看,她看后會及時提出意見。
有一次,她提出批評,說雜志拖期太厲害。如果雜志不按期出版,到了美國就成了舊聞。她要求我們一定要解決新聞不新和拖期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定難度,因為雜志的生產過程很長。其中有些環節不是我們自己能控制的,如約稿、印刷、發行等。雜志出版后發到美國,路上就要走一個月。根據宋慶齡的指示與要求,我們積極整改,想了很多辦法。
宋慶齡對雜志的另一個意見是印刷質量問題,責成我們要設法改進。
她有時把我們找去當面提意見,但大多數時間以信函表達她的意見與想法。很多時候,宋慶齡是通過金仲華來關心指導雜志社工作的。宋慶齡與金仲華很熟,也很信任他。金仲華也很關心雜志,他每次來北京開會,都會抽空到雜志社來,及時轉達宋慶齡的意見。有時宋慶齡會直接給我寫信,如1960年11月5日來信評述過去11期雜志的優點,及提出今后改進的意見。
“文革”中,宋慶齡對雜志受到“四人幫”的干擾十分痛心,在她給很多朋友的信中都談到了此事。那時,雜志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偏離了既定方針。我也由于堅持正確路線,在“文革”一開始就受到沖擊,被打倒并下放到農村長達8年之久。直到“文革”結束才得到平反。
轉眼宋慶齡創辦《中國建設》雜志已經60周年了。我慶幸能在宋慶齡的領導下工作,特別是曾參與了《中國建設》雜志的籌辦與發展,親聆她的教誨。“文革”后,我雖調離了雜志社,但作為一個“老中建”,我欣慰地看到雜志經過“撥亂反正”,終于又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面貌煥然一新,實現了宋慶齡生前的愿望。
現在,我從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的職位上退了下來,又義務參加了中國福利會和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的工作,為向世人弘揚宋慶齡精神發揮我的余熱。宋慶齡雖然已經離開了我們,但她的精神將永遠激勵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