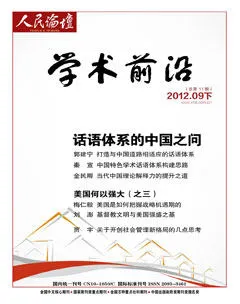當代中國理論解釋力的提升之道
【作者簡介】
金民卿,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導。
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與意識形態等。
主要著作:《大眾文化論——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分析》、《文化全球化與中國大眾文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初步形成》等。
摘要 在當代中國,增強理論自覺首先體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主體的自覺上,表現為:自覺實現自身的馬克思主義化,達到對馬克思主義的真學、真懂、真信、真用;打造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自覺提升當代中國理論的解釋力;自覺樹立自主的文化標準權意識,抵御西方文化標準和學術話語的“普世化”;自覺形成戰士與學者相統一的風格,在搞好理論研究的同時承擔起同錯誤和反動思想傾向進行理論斗爭的使命。
關鍵詞 理論自覺 理論主體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一個時期以來,增強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不僅是理論宣傳部門的號召,而且也越來越成為學術理論界的共識性追求。自覺和自信首先是主體本身的一種認知和境界,理論學習、研究和宣傳歸根到底是理論主體的思想創造過程,離開理論主體來討論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就會將自覺和自信外在化和虛化,最終失去討論的意義。立足于當代中國的時代特征和文化語境,我們把關注點集中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主體的理論自覺上,這種理論自覺主要體現在自覺實現自身的馬克思主義化、自覺提升當代中國理論的解釋力、自覺樹立自主的文化標準權意識、自覺形成戰士與學者相統一的風格等幾個方面。
自覺實現自身的馬克思主義化
不容否認的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下中國有一種自發論傾向。一些人認為,我們國家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國家,人們不用學習就能夠自發地掌握馬克思主義,能夠自然而然地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當代中國正在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人們親身經歷了這種實踐,因而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由此,那些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知識分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主體。事實并非如此。
首先要清楚的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大眾性的生活常識體系和習慣性的話語體系,而是包括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在內的、具有嚴密邏輯的科學理論體系。列寧在談到馬克思主義時,就反復強調它的理論完整性和邏輯嚴密性。他指出:“馬克思的觀點極其徹底而嚴整,這是馬克思的對手也承認的”①,“馬克思學說具有無限力量,就是因為它正確。它完備而嚴密,它給人們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觀”②。毛澤東也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性和理論體系性,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③。作為深邃的真理體系和科學的方法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是對社會生活和無產階級實踐的高度理論抽象,具有特定的話語體系、邏輯層次、概念系統和理論架構,其深度意義并不直接呈現在人們面前,需要認真研究和長期學習才能夠把握。這就需要擁有系統化的理論思維訓練,具有理解和把握理論體系的能力和素質,關心并從事理論創造、闡發、傳播的知識分子。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體。首先,并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接受者和傳播者。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就開始見諸中國報刊書籍,一些知識分子以不同方式、動機、態度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1898年,胡頤谷就在其譯著《泰西民法志》中介紹過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梁啟超、朱執信等也介紹過馬克思的生平和學說。但是,這些知識分子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性,沒有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例如,梁啟超在《新大陸游記》談到科學社會主義時就說過:“極端之社會主義,微特今日之中國不可行,即歐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將不可勝言。”④ 其次,僅僅了解甚至熟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并不必然就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因而也就不能直接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體。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當然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例如五四時期的文化主將胡適,同李大釗、陳獨秀等一起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高潮,對馬克思主義也有所了解,但他站在實用主義的立場上反對馬克思主義,因此不可能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體。同樣,對馬克思主義不堅定的知識分子也不能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建黨初期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陳公博、周佛海、任卓宣(葉青)等,后來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真正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和精髓的人,例如中共黨史上的著名人物王明等,盡管熟讀馬列經典,但只是教條主義地理解而不得精神實質,因而也沒有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體。
那么,究竟什么樣的知識分子才能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才能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體呢?歷史事實表明:只有那些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的知識分子,才能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體。這就是說,知識分子要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體,首先要有一個自身的馬克思主義化的轉變過程。在此方面,李大釗和毛澤東很具代表性。十月革命后,李大釗經過深入分析認識到,俄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十月革命勝利,一個關鍵原因就在于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十月革命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馬喀士的功業”。⑤由此,他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性和革命實踐性,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堅定信仰并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五四之前,毛澤東的“頭腦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及空想社會主義的有趣的混合物”。五四之后,毛澤東認真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著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迅速實現世界觀的根本轉變,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用他的話說就是:“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⑥不久就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⑦,明確了馬克思主義在黨內的指導地位,并完全實現了自身的馬克思主義化。
世界上沒有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自發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要真正擔當起推動理論創新的歷史責任,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主體,就必須自覺地實現自身的馬克思主義化,也就是必須認真學習、真正弄懂、堅定信仰和切實運用馬克思主義,達到對馬克思主義的真學、真懂、真信、真用。所謂真學,就是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全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而不是敷衍潦草地、表面膚淺地、浮光掠影地僅僅了解馬克思主義。所謂真懂,就是切實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科學掌握并真正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而不是僅僅記住馬克思的個別話語和詞句。所謂真信,就是真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敢于捍衛馬克思主義,樂于宣傳馬克思主義,真正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分析社會、理解人生的科學理論指導,而不是表里不一、三心二意、人格分裂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真用,就是在科學研究和社會實踐中真正運用并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教條主義的、脫離實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關于理論家的論斷極富啟發性,他指出: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理論家,“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這樣的理論家“能夠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并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⑧當代中國的學者需要深入領會毛澤東的這個論斷。
自覺提升當代中國理論的解釋力
理論解釋力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程度的重要尺度,能不能用獨立的、系統的、嚴密的理論體系,對自身的實踐成果和發展經驗作出深度的解釋、總結、提升,反映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的理論思維能力、文明發展程度和總體成熟狀況。當代中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開拓前進,形成了豐富的實踐成果、理論成果、制度成果,積累了鮮活的經驗,這些都需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主體進行科學的理論提升。
從理論上升華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實踐經驗,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發展實踐的雙重需要。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世界性的科學思想體系,必須同各個國家的具體實踐、各個民族的歷史文化、不同時代的具體特點相結合,才能真正對這個國家和民族產生科學指導意義,才能發揮其真理性力量,其自身也正是通過吸收各個民族的文化和實踐成果而得到豐富發展。正如毛澤東所說:“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⑨另一方面,中國豐富的實踐需要在理論上深入總結和提升,實踐經驗是片段的、分散的和感性的,只有經過理論提升才能成為系統的、完整的、理性的認識,人類實踐如果總是停留在遵循經驗的層面,則往往限于對前人的重復而處于爬行狀態,只有在系統的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才能更符合客觀規律、更具有主動性和自覺性,從而不斷實現新的飛躍。
這就是說,在理論上系統總結中國實踐經驗,在升華中國經驗的同時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當代中國思想理論界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而要擔當這樣的歷史責任,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自覺提升當代中國理論的解釋力。為此,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必須自覺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了解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大眾需求、分析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創造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話語體系,不斷推進理論創新,把自己鍛造成為真正合格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主體。
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發展,是提升當代中國理論解釋力的重要前提。不必諱言,馬克yk7end7Tj0rp0MJY9u22ww==思主義畢竟是產生于歐洲而傳入中國的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屬于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盡管它同中國文化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溝通和融合,但二者之間的異質性依然存在。如果僅僅教條主義地照搬馬克思主義的詞句,離開中國文化傳統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移植,就很難對長期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大眾產生吸引力和說服力。這就需要當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主體,不僅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同時必須深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形成扎實的民族文化根底,把握兩種文化之間的契合點,使馬克思主義在民族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深入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深處,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與此同時,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注入到中國文化當中,實現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現代轉型,實現民族文化的馬克思主義化,在雙重轉化的基礎上實現融合發展,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更加豐富,理論更加完善。
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時代特征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對中國實踐作出深度總結和科學闡發,是提升當代中國理論解釋力的關鍵環節。一方面,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充分發掘和吸納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容,借鑒國外思想文化和學術理論發展的最新成果,構建符合科學理論發展規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相對完善獨立的學科體系、理論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充分體現中華民族理論思維的當代水平,體現當代中國學術理論的自主獨立性,打破理論路徑依賴和學術話語依賴;另一方面,用這種獨立的學科體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深入解釋、分析、總結、提升中國實踐經驗和中國發展道路,深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認識,升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成果、理論成果、制度成果,概括出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的、開放融通的新觀點、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不斷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范疇體系、概念系統和理論架構。
深入分析和科學回答當代中國的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理論支撐。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提升當代中國理論解釋力的目的所在。當代中國的理論工作者,必須追隨時代進步和實踐發展的步伐,深入探索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社會主義的制度本質和建設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規律和發展道路。站在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準確把握世界發展大勢和人類文明的最新走向,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及其具體變化,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發展趨勢,深入研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研究并回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實踐所提出的新的歷史性課題,分析和解決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發生的重大變化和存在的重大問題,為鞏固、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出理論貢獻。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回答和解決與群眾根本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現實問題,特別是人們感受最深切、議論最熱烈的社會分配不公、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斷拉大的矛盾,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理論分析和對策思考,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有效抵制市場經濟的負面因素,不斷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努力解決社會公平問題,切實提高普通群眾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消除社會矛盾激化的隱患。在此基礎上,不斷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發展著的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中國化”,不斷把黨帶領人民創造的成功經驗上升為理論成果,實現理論創新成果的“馬克思主義化”,不斷豐富和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自覺樹立自主的文化標準權意識
標準是個大問題,文化標準權是國際思想文化交流和意識形態斗爭中的核心權力。增強理論自覺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樹立思想文化的自主標準權意識,抵御西方文化標準和學術話語的“普世化”。
應該說,由于發展水平的時間差,西方發達國家在生產、生活甚至于在文化領域都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評價標準,諸如質量標準、環保標準、GDP指標等,對于這些符合人類共同發展要求的評價體系,我們完全可以拿過來作為參考,以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中國人在參考和使用西方發達國家制訂的各類標準時,不應該忘記這些標準本身所包含的利益因素和意識形態內涵,尤其要警惕某些國外勢力惡意使用某些所謂的統一“指標”來詆毀中國的國家形象。例如,常有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國人)拿人均GDP等數字說事,目的就是丑化和誤導中國,摧毀我們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再如,在國際上頗有影響的“透明國際”,總是按自己的標準把中國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列為高腐敗率國家,極大地損害了中國國家形象。一些西方評價機構借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謂通用性標準,通過所謂的評級,干預中國的經濟活動,榨取中國的利益。2003年底,中國銀行業謀求到海外上市,而“標準普爾”就在此時將中國13家商業銀行的信用級別都評為“垃圾級”,與此同時,它高調肯定境外投資者參股中國商業銀行的行為,為國際壟斷資本攫取中國的國有資產造勢。
西方發達國家操控標準權的現象在思想文化領域頗為嚴重,他們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作為普世的標準,對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思想文化進行評判。“歷史終結論”、“普世價值論”等就是這樣,它們采用偷梁換柱的手法,把歷史與西方資本主義歷史劃等號,把民主、憲政、自由等帶有人類共同價值的美好詞語同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劃等號,在此基礎上認為只有西方文明和政治制度才是最優秀的,人類歷史的發展只有在西方的歷史中才能說明,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已經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制高點。其背后的價值觀旨趣在于,非西方國家應該服從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文明模式,放棄自身的文化傳統和人文精神,放棄自身的文化主權,從而實現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控制。
這種西方文化標準普世化的傾向在國內思想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響應。一些人根本沒有察覺或故意掩蓋西方文化標準背后的政治指向和潛在邏輯,卻以此為標準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大加攻擊,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些已被西方人發明創造出來的、被西方社會的發達史證明了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的”萬能法寶,而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存在著權力的軟約束、腐敗、權大于法、民主化程度低等弊病,都是由共產黨專制政體造成的。一些人打著“民主”的旗號,否定共產黨的領導,要求實行多黨競選、民眾普選等方式,實行所謂的“憲政”,用西方式的憲政民主制度代替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一些人以適應全球化和思想解放的名義,把普世價值論、歷史終結論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平移到國內,大加贊賞并奉為圭臬,以此為標準來拷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我國的意識形態,并依照西方意識形態理論框架提出一系列所謂的“理論”或“主義”,企圖“替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學術話語上,一些人把新自由主義、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視為學術標準,仿佛不使用這些話語就是學術水平的缺失,反之才是學術英雄、思想精英,只要有學者對這些做法提出質疑和批評,馬上就會遭到“資格”與“合法性”的質疑。
在這種情況下,文化標準權的自覺就顯得尤其重要。處在全球文化相互激蕩的時代環境中,中國的思想理論和學術文化,可以借助西方的一些文化標準,但決不能陷入西方文化標準普世化的陷阱,應該努力建構和推行我們自己的文化標準,通過自主的文化標準,贏得獨立的理論話語權,同時也帶動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
其實,在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進程中,黨和國家政府歷來都有明確的標準。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就明確提出了判別思想領域是非的六條“有利于”標準:是否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否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是否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是否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毛澤東特別指出,“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⑩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把毛澤東這一思想發展為四項基本原則。他反復強調,在任何情況下決不允許動搖這些基本原則,“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思想文化領域的標準。
這些標準符合客觀真理的要求,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符合中國人民群眾的意愿。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界應該理直氣壯地堅持這些標準,并在此標準的引領下,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民族優秀文化、全球性話語同本土性話語、意識形態話語同學術性話語的有機結合,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話語體系,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發出中國的強大聲音。
自覺形成學者與戰士相統一的風格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最后有這樣一段話:“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一方面,他是一個堅強的戰士,是一個真理的捍衛者,他同一切剝削階級的各種自私的、虛假的意識,同各種反動的錯誤思想進行堅決的不妥協的斗爭,在這種斗爭中既不能猶豫更不能怯懦,這就是一個戰士的風范;另一方面,他是一個嚴肅的科學家,是一個真理的探索者,他的結論絕不是一時感情沖動的結果,不是激憤的產物,而是建立在長期科學研究基礎之上,飽含著學者的良心和科學的嚴謹。正如列寧在評價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所說的,他是“嚴峻的戰士和嚴正的思想家”。
五四運動時期,陳獨秀有過關于“研究室與監獄”的精彩論述。1919年6月8日,他在《每周評論》第25號上發表了《研究室與監獄》的短文:“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陳獨秀的這段話,展示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風格,即戰士與學者的有機統一:所謂入研究室,就是要堅持嚴謹的學術精神搞好科學研究、探索真理;所謂入監獄,就是要敢于為捍衛真理同各種錯誤思想以及反動政治統治進行不懈的斗爭,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
其實,思想交鋒和斗爭歷來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基本路徑和規律,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同各種錯誤思想的斗爭中創立、發展并不斷勝利的,列寧對此早已指出:“馬克思的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也是如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于四項基本原則的沖擊始終沒有停止過,馬克思主義過時論、民主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論等錯誤思潮的干擾更是不絕如縷。對此,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和高度自覺,在同這些錯誤思想的斗爭中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明確提出:“對于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近年來,胡錦濤也多次講到,要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
當前,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關鍵時期。站在不同立場、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社會思潮紛紛出現,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對于馬克思主義也產生了各式各樣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多元化”、“歧義化”的聲音屢屢出現在報刊媒體之中,影響著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把握。更有甚者,打著解放思想的口號,反對社會主義,倡導資產階級自由化、民主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思潮;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否定共產黨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主張多黨制和資產階級的憲政主義;打著思想多樣化旗號,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宣揚指導思想多元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等。
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主體,一方面,必須承擔起學者的責任,以嚴謹的學術精神搞好理論研究,提出建立科學思想基礎上的有說服力的理論觀點,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另一方面,必須承擔其戰士的責任,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理論方向,正確處理原則捍衛與理論創新的關系,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與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關系,以高度的理論自覺抵御各種不正確的理論觀點,同錯誤和反動的思想傾向進行不妥協的理論斗爭,同時也要反對打著解放思想、學習借鑒等旗號,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偷換指導思想的企圖,在理論斗爭中駁倒錯誤思想,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
注釋
《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8、309頁。
《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7、814頁。
梁啟超:《梁啟超游記》,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年,第300頁。
《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9頁。
斯諾:《西行漫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第131頁。
《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頁。
《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
《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3~234頁。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390頁。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4頁。
《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48頁。
責 編/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