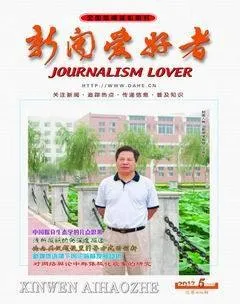民族形象的超越與普及
【摘要】《新兒女英雄傳》中的新英雄形象,通過表征民族意識,滿足了民族自我認知的超越性要求;通過民間倫理對民族意識的轉譯,又同時滿足了民族自我認知的普及性要求。然而民間倫理在轉譯民族意識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窄化了民族意識,使形象本身出現了模式化、平面化的傾向。作為新文學建構民族形象的一次嘗試,解放區新英雄形象的生成機制充分展示了民族形象建構過程中超越性與普及性的互促與互限。
【關鍵詞】民族形象;新英雄形象;超越;普及
自19世紀中后期中華民族以弱者身份進入世界語境之后,民族自我形象的塑造中就一直存在著改變弱勢地位的超越性要求,并蘊涵著將之向全民族普及的沖動。《新兒女英雄傳》中的新英雄形象既滿足了民族自我認知的超越與普及的雙重要求,也因此呈現出模式化、平面化的偏頗,其生成機制充分體現了民族自我形象在超越性與普及性之間的兩難抉擇。
新英雄的超越:受政治理念指引的民族意識
民族意識是自我與他者競爭中,尤其是在民族深陷于戰爭時最可貴也最令人振奮的精神品質。《新兒女英雄傳》中牛大水、楊小梅等新英雄形象之所以激動人心,就因為他們本質上是以民族為重、為民族奉獻的理想民族意識的具體表征。文中的英雄人物之一黑老蔡曾對“英雄”做出這樣的定義:“有能耐的人很多,就看走明路還是走暗路了。有的給鬼子辦事,落一個漢奸的臭名,還不得好下場。有的人為咱們中國人爭光露臉,鬧個民族英雄,走到哪兒老百姓都是歡迎的。”[1]65民族意識成為新英雄形象的核心價值,他們不再因本領或能力煥發光彩,而是借表征民族意識呈現神圣性。正確的民族意識會賦予人某種神奇的能力,而錯誤的民族意識則會令具備特殊才能的人喪失能力。因此,甘愿為民族流血犧牲的牛大水,可以由一名普通農民成長為擁有非凡槍法、膽識過人的英雄。而原本槍法奇絕的張金龍卻因為投降了日本人,喪失了原來的能力,在與游擊隊員的射擊比賽中狼狽落敗。
通過牛大水與張金龍的對比,《新兒女英雄傳》強烈地凸顯了民族意識之于英雄的重要意義。在艱難的民族抗戰之中,民族意識的神圣光輝的確能令每一個中國人熱血沸騰。然而系之于精神品格的民族意識若缺乏有效的啟發與規范,是會產生波動甚至走向反面的。張金龍也曾一度加入抗日隊伍中,卻最終因無法克服懶惰、散漫等性格弱點,墮落為漢奸。文本通過張金龍的變化軌跡表達了對于單一民族意識標準的隱憂,新英雄形象為了滿足超越性的民族自我認知要求,還需要明確正確民族意識的獲得途徑和保持方式。正如孫犁在談論應該怎么對待戰時的英雄文學時言及的那樣:“今天,我們的戰爭,我們的英雄,跟舊時代的戰爭和英雄性質是不同的。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不很了解這一點,以致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的戰爭和英雄常被作歪曲的描寫。只說勇敢、英雄……這種字眼,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重要的還要區別怎樣的勇敢和怎樣的英雄。”[2]針對這一問題,牛大水等人的共產黨員身份做出了詳盡的解答。
《新兒女英雄傳》中那些擁有正確民族意識,立場堅定的新英雄都具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共產黨員。牛大水原本只是一個只知有家不知有民族的農民,經過共產黨員劉雙喜的現身說法,大水才踏上了舍小家顧大家的英雄之路。啟發牛大水的并不是劉雙喜這個具體的人,而是他所象征著的共產主義政治理念。共產主義的政治理念不僅啟發普通人獲得了民族意識,更杜絕了他們在通向英雄的漫長歷程中的動搖與墮落,保證他們成長為新英雄,最終實現民族自我對他者的超越。當牛大水被何世雄嚴刑拷打時,身體的痛楚使他試圖以死解脫,但一想到“‘我是個共產黨員……’,他氣一壯,心一橫,覺得痛也不那么厲害了”[1]141,共產主義的政治理念使牛大水剛強堅定。文本借助類似情節的多次重復申明正是共產主義政治理念使民族意識的獲得與正確實施成為可能。
鮮明的民族意識使新英雄形象既昭示了民族發展的理想方向,而政治理念又保障了民族意識的獲得與保持,因此新英雄形象是穩定而自足的,其迸發出的光明、未來、理想等審美特質與精神元素,與民族自我認知的超越性要求產生了共鳴與交流。
新英雄的普及:民間倫理對民族意識的解說與窄化
《新兒女英雄傳》在滿足民族自我認知的超越性要求的基礎上,還試圖對這種超越性進行普及,使英雄成為民族自我認知的普遍特性。為了達到普及的目的,《新兒女英雄傳》始終強調英雄與普通人之間并不存在難以逾越的界限。文本試圖通過塑造偉岸高大而又平凡普通的新英雄形象,使讀者在產生崇敬感的同時獲得認同感:“英雄”就在自己的身邊,而自己也有可能成為“英雄”。郭沫若為《新兒女英雄傳》所作的序言,非常敏銳地把握到了新英雄的普及功能,“讀者從這兒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勵,來改造自己或推進自己。男的難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樣嗎?女的難道都不能做到楊小梅那樣嗎?”[3]那么該如何成為“英雄”呢?《新兒女英雄傳》所提供的方法就是要復制英雄所表征的核心價值。郭沫若形象地將此表述為:“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無知,只要你有自覺,求進步,有自我犧牲的精神,忠實地實踐毛主席的思想,誰也可以成為新社會的柱石。”[3]
新英雄形象的普及性固然令人激動,然而對于文本預設讀者——中國最普通的農民而言,復制其核心價值卻絕非易事,無論是民族意識還是政治理念都遠遠超出了他們的認知范疇。為了彌合核心價值與預設讀者認知范疇之間的天塹,使新英雄形象完成普及的使命,《新兒女英雄傳》引入了民間倫理,通過預設讀者們所熟悉的民間倫理對核心價值進行了日常化的解說。比如文本利用預設讀者對“家”的理解對超出他們認知水平的“國”進行了類比和解釋。主要英雄牛大水與楊小梅是夫妻,英雄少年牛小水是牛大水的親弟弟,精神導師黑老蔡既是牛大水的表哥,又是楊小梅的表姐夫,革命同志劉雙喜、高屯兒則是他們的同鄉。人物的親緣、地緣關系與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組織關系重疊交織在一起,親緣與地緣中的長幼親疏秩序形象地解釋了社會與組織關系中的上下協作聯系。除了利用“家”的結構闡明“國”的網絡外,文本還進一步地預設讀者們對“家”的珍愛,也因此被引導向了對“國”的忠誠與奉獻,就像新英雄那樣由對家的愛上升到對于國的保衛。此外,通過“家”所生發出的親密、和睦等情感也同時表征了“國”的凝聚能力。新英雄之間基于共同目標而產生的互助關系,被表述為“親如一家”。在以“家”來解析“國”的同時,文本還以道德水準對政治理念進行了提示。文本中不惜以生命來實踐共產主義理想的新英雄們同時還是道德上的完人。無論是黑老蔡、劉雙喜,還是牛大水、楊小梅,他們政治上的逐漸成熟始終都伴隨著良好的個人道德品質的展現,這使得預設讀者能夠較為輕松地通過自己所熟悉的道德標準對他們進行識別。與此相反,那些非英雄則全部是聲名狼藉、道德敗壞的。作為漢奸、叛徒的張金龍登場時就已經是個二流子,在家打罵妻子、虐待孩子,在外拈花惹草,惹是生非。預設讀者對于道德敗壞者的鄙夷與仇視,也很自然地就加諸在了他的身上。
民間倫理的引入使得新英雄身上超越性與普及性交相輝映。然而民間倫理在對核心價值進行普及的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窄化了核心價值。因為民間倫理自身具備穩定的邏輯,當文本借用民間倫理的通俗特點對核心價值進行解說時,民間倫理自身邏輯也不可避免地參與其中,對核心價值進行干擾。面對著既是游擊隊領導,又是自己兄長的牛大水,牛小水陷入了稱呼的尷尬之中。當他稱呼牛大水為“哥”時,牛大水嚴厲地訓斥了他并一定要讓他叫“隊長”。“哥”與“隊長”的稱呼顯然來自“家”與“國”兩種不同的價值標準,而“隊長”對“哥”的排斥,又表明了兩種價值標準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分歧。可是文本的敘事邏輯,卻是借助“哥”所隱含的長幼秩序來確立“隊長”的權威地位,兩者又無法真正地截然分離。因此牛小水雖幾經教育,卻還是會稱呼牛大水“哥”,甚至有些時候連牛大水對此也渾然不覺了。《新兒女英雄傳》本可以此為突破口,辨析其中的錯綜復雜,但呈現復雜顯然并非文本敘事的重心,文本急于通過民間倫理所擁有的廣泛的接受基礎,來使核心價值獲得推廣,因此對此只是一帶而過。
對于民間倫理與核心價值之間復雜關系的有意無意的忽略,不僅造成了民間倫理對核心價值的干擾,有些時候還會造成民間倫理對核心價值的反敘述。《新兒女英雄傳》中的新英雄形象往往完美無瑕,而反面形象則一無是處,甚至在外貌上也呈現明顯的分野。這最終導致新英雄形象在整體上出現了臉譜化、平面化的趨勢,使得新英雄的超越意義顯得有些牽強。
民族形象的兩難:超越性與普及性的難題
以牛大水、楊小梅為代表的新英雄形象,既令人神往又不免刻板膚淺,雖試圖滿足超越性與普及性的共同要求,卻又總是難以兼顧甚至謬以千里。這批新英雄形象,在超越與普及之間的輾轉徘徊,也是困擾著新文學民族形象建構的重要命題。
自進入世界語境中,原本穩定自足的民族自我,就面臨著來自“他者”的不斷挑戰,要應對這一挑戰,民族自我必須對自身進行重塑,以此來確認自身、凝聚力量。作為歷史現實折射且有著極強社會參與意識的中國新文學,也始終貫穿著對自我形象進行敘述、歸納的價值追求,留下了大量關于民族形象的鮮活敘述與深刻剖析。從民族自我認知的文學表達這一角度來看,無論是阿Q式的否定性的自我認知,還是牛大水、楊小梅式的理想性的自我認知,都傳達著同樣的信息:民族自我具有哪些特征,又將向何處去。由于擔負著民族自我認知的功能,所以他們雖屬于作家因時代、民族交相激蕩,觸機而發的想象產物,卻還要突破想象層面,在現實層面滲透到民族整體,發揮啟發、激勵民族自我意識生長、深入的作用。因此,無論阿Q,還是牛大水、楊小梅都在獲得了具有超越性的核心價值后,面臨著如何普及核心價值,進而對民族在現實層面超越他者產生影響的問題。民族形象的成功與否是由超越性與普及性共同左右的,超越性的追求內含著普及性的實現,而普及性的解決方法又制約著超越的真正實現。從阿Q到牛大水、楊小梅,新文學所進行的種種民族形象的嘗試都是在不斷地尋找兩者之間最佳的平衡點,甚至包括從文言到白話,從歐化到大眾化、民族化的形式演進也都受此驅動。然而正如新英雄形象所表現出來的矛盾與尷尬一樣,兩者總是難以達到理想的平衡狀態。新文學就這樣在一次又一次的艱難跋涉中,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記錄下了民族自我艱難的生發與凝聚,也為今天民族形象的建構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
參考文獻:
[1]孔厥、袁靜.新兒女英雄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2]孫犁.論戰時的英雄文學——在冀中《前線報》文藝小組座談會上的發言[M]//胡采主編.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文學運動·理論編二.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1283.
[3]郭沫若.《新兒女英雄傳》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