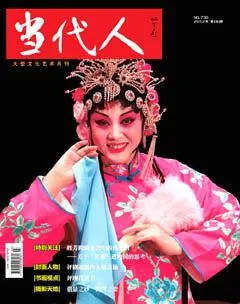探險“三八線”
2010年9月,我赴韓參會,有幸隨團探訪了“三八線”。
三八線是位于朝鮮半島上北緯38度附近的一條軍事分界線。第二次世界大戰末,盟國協議以38度線作為蘇、美兩國對日軍事行動和受降范圍的暫時分界線。日本投降后就成為朝鮮和韓國。的臨時分界線,通稱“三八線”。1950年,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應朝鮮之邀,中國派志愿軍抗美援朝。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朝鮮板門店簽訂。協定仍以三八線為朝、韓分界線。由于戰爭的原因,此時的所謂“三八線”已經是犬牙交錯的軍事控制線,比如東部韓國在三八線以北控制著大片土地;西部在三八線以南有部分疆域卻歸朝鮮管轄。協定規定,雙方在長約248公里的實際控制線上,各退2公里為非軍事區,這就是說,有4公里為“真空”地帶,只有飛禽走獸可以自由來往。
近60年來,“三八線”上時而劍拔弩張,時而相安無事。韓國為了利用那塊休閑多年的肥沃土地,采取免賦稅、免兵役等優惠政策,鼓勵有膽之士去開荒種地,這一優惠政策竟造就了無數百萬、千萬大戶。
從首爾出發,旅游車向北駛上高速公路。能說流利臺灣普通話的韓國導游開始介紹通往“三八線”的高速路:“這條高速公路是由韓國現代集團出資修筑的。集團董事長鄭周永,1915年出生在今朝鮮江原道通用一個世代務農的貧苦家庭。小時候,他曾偷了家里賴以生存的賣牛錢到漢城謀生。先做米店生意,又做汽車修理、房地產、汽車制造等,以致發展成龐大的現代集團,富可敵國。但偷賣牛錢的事一直耿耿于懷、愧疚難當。于是他在1998年上演了一場趕著500頭牛浩浩蕩蕩進入朝鮮的戲劇場面,轟動了朝鮮半島,世界各大媒體也爭相報道。鄭周永總算償還了多年舊債,了卻了一樁心病。他投巨資修建這條直達‘三八線’的高速公路,就是想一旦南北和好,他便常回家看看。”
一個小時后,旅游車進入軍事區。大概因為是旅游團,我們并沒有下車受檢。但導游經歷了盤查、驗證、登記等手續才得以通關。
旅游車開到位于“三八線”上的汶山站。一座座貨柜倉庫虛位以待,寬敞的售票大廳空蕩蕩的,游人在這里爭相加蓋車站印章,以示到此一游。車站不遠處停放著一輛破爛不堪的火車頭。只見火車頭銹跡斑斑、彈痕累累、滿目瘡痍。1951年6月朝鮮戰爭期間它就停在了這里,已經59年原地不動了,昭示著戰爭的悲哀。導游說:“2000年6月,韓國總統金大中在平壤與朝鮮金日成主席舉行會晤,就恢復韓朝鐵路連接達成一致。2009年5月17日,來自韓國和朝鮮的列車分別從韓國汶山站和朝鮮金剛山站出發,進行停戰后56年來首次跨越韓朝軍事分界線的列車試運行,隨后關閉。何時正式開通,翹首以待。”
旅游車帶我們來到臨津閣嘹望臺。高高的瞭望臺上安放著一排高倍望遠鏡,從望遠鏡看出去,是一片雜草叢生的荒涼地,滿目凄慘、荒無人煙。導游說,這里曾多次發生“旗桿戰”和“廣播戰”。“旗桿戰”是說朝韓雙方為了壓住對方國旗,旗桿越樹越高,我們所看到的朝鮮旗桿高158米,據說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廣播戰”是說當年朝韓雙方用高音喇叭打“宣傳戰”,無數高音喇叭每天十幾小時對播,持續了半個世紀。
不遠處的望鄉臺更加凄涼,只見高架的鐵絲網上掛滿了祈福彩條,仿佛是悲痛欲絕的一片哭聲。
導游告訴我們:“上世紀70年代至今,韓國方面曾在非武裝地帶附近先后發現四條朝鮮地道。最有名的第三地道能在1小時內通過武裝士兵1萬人,地道口距韓國總統府只有52公里。”我們每人發了一頂安全帽,沿斜坡走下地道。斜坡很陡,迫使游人不由自主地緊走,像有人推著一樣。下到底部,便是地道口。地道寬2米,高2米,據說長1635米。內壁是暗紅色的花崗巖,上部搭有支架,不時有水滴下來,地面用廢舊輪胎切割組裝后鋪成。如此堅硬的花崗巖是用雙手在秘密情況下開鑿出來的,難度可想而知。
離開地道,一座四角尖頂建筑映入眼簾,古樸端莊。導游說那是鐘樓,吊著一口碩大的銅鐘,是人們祈禱和平的和平鐘。但愿我們聽到的是悠揚的和平鐘聲,而不是恐怖的槍炮聲。因為朝、韓只是停戰,而非和平,隨時可能戰火再起。
在一個張開的由兩個半球組成的大型雕塑前,游人爭相拍照。這個雕塑設計巧妙,兩個半球上開下連,裂縫處象征“三八線”,北半球切面上部雕刻著朝鮮地圖,南半球切面下部雕刻著韓國地圖,如果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朝鮮半島圖。兩個半球外邊都有幾個銅人用力推合。我和老伴趕緊各站一邊,好似在為兩邊的銅人助力,期盼著早日實現半島和平。
(責編: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