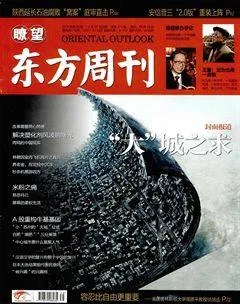周振鶴:真正的市場經濟與行政區劃沒有關系
12卷本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學術意義上的行政區劃變遷通史,其主編周振鶴數十年來致力于研究行政區劃變遷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是我國知名的行政區劃研究專家。
周振鶴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曾擔任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行政區劃與地名學會行政區劃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社會兼職。日前,就近來我國多地行政區劃調整情況,周振鶴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專訪。
《瞭望東方周刊》:怎么認識近年各地撤市改區的現象?
周振鶴:行政區劃的變遷,有時候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有時候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有時候是為了文化變遷的需要,這是很正常的。近年,我國區劃調整是較為頻繁的,而且每次都是大規模的調整,這使得我國行政區劃有些混亂。
過去,城市建成區才叫市,農村不能叫市,也不叫區。但自1980年代以后,我國推行撤縣改市,縣級市就開始出現了,這就使得城市跟農村不分了。縣變成市以后,城市人口怎么統計?是不是整個縣的人口都是城市人口?從縣改市到縣改區、直轄市的縣改區,以至于到市管縣,市的概念就變得比較混亂了。一個“市”,應該是面積比較小、人口比較集中、工商業集中的地方。
《瞭望東方周刊》:行政區劃不斷變遷的原因是什么?
周振鶴:大都是為了經濟發展才這樣搞的,真正的緣由不是為了行政需要。原來進行撤縣改市就是把最好的地方變成一個市,希望用這個市來帶動農村。但實際上并沒帶動起來,所以后來撤縣改市也就停止了。
最近這些年,比如說安徽省,為了避免馬鞍山等地向南京看,就把巢湖分成三部分;還有蘇州,因為昆山被江蘇省直管了,就把整個吳江市變成區。吳江區跟吳江市有什么區別呢?變成吳江區就等于讓蘇州市跟上海接壤了,蘇州就有—個區那么大的一塊地可以利用了。不變成區,吳江作為縣級市有自我發展的需要,那么蘇州的發展余地就沒有了。
背后的根源是我國還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經濟。
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的行政區劃定下來后就不需要改,因為它的經濟發展是完全市場調節的,而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經濟發展是沒有范圍限制的。連跨國公司都突破國界了,經濟的發展肯定是要突破行政區劃限制的。要知道,真正的市場經濟是跟行政區劃沒有關系的。
《瞭望東方周刊》:那么,行政區劃存在的意義是什么?
周振鶴:意義就是政府要做好這個區域里頭的公共服務。這塊兒歸你負責,你要把這塊兒的公共利益搞好、衛生搞好、交通搞好、不要有污染,這才是政府要做的事。經濟發展可以由政府去調控,但也就是限于調控而已。
《瞭望東方周刊》:從歷史上來看,我國是不是也很重視行政區劃?
周振鶴:在中國,行政區劃非常重要,就是因為我國歷史上是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行政區劃如果弄得不好,政令就不容易直達到基層,下情也不能很容易地直達中央,所以就有一個歷史的變化過程。
最近一段時間的行政區劃調整,也是走向市場經濟的一種陣痛,經濟的變遷需要改變行政區劃來適應。從中央到省、市、縣,區劃調整牽扯利益很復雜,每一層利益都可能對行政區劃的變遷發生影響。比如說,我國很多城市是副省級城市,怎么會有副省級這么一個概念的?這就是說經濟地位提高了,行政地位也要相應地水漲船高。
《瞭望東方周刊》:我們似乎對“市”更有感情,比如前段時間河南有個村要改成“村級市”。
周振鶴:這就“很荒唐”了。村不好嗎,為什么要變成一個市呢?在中國古代,市本來就是集鎮的意思,是歸縣管的,就是“縣管市”,比如現在的日本還是這樣。
我國現代意義上的第一個市是廣州。1920年左右,陳炯明在原廣東南海縣把市區的范圍當成一個市,跟南海縣平行,這就是我國第一個城市行政區。從這以后,市就開始有了。
市發展起來后,需要各種城市生活的配套資源支持,這樣一來又把市周邊的縣附屬到市底下去了,變成市管縣。比如,上海市本來由周圍江蘇省各個縣來保障城市供應,但周圍的縣都是江蘇省的,于是到1958年就把江蘇省的十個縣劃歸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