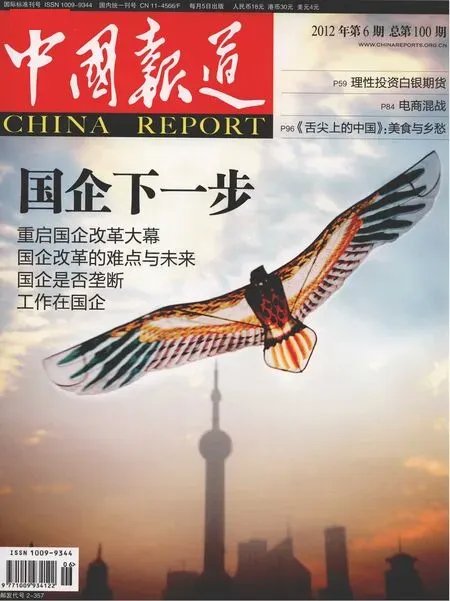國企是否壟斷?
肖江平
肖江平 北京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

2009年11月13日,重慶等待加氣的出租車排起長隊。
我國的《反壟斷法》實施已近4年,“壟斷”和“反壟斷”早已成為耳熟能詳的詞匯。但在日常生活中的理解與法律上的理解差別很大,有時甚至大相徑庭。在國企壟斷這個論題上,就比較明顯。
壟斷源自市場地位
從經濟學角度理解,壟斷的本義是指獨占的市場,廣義是指獨占、寡占和壟斷競爭的市場。獨占,即一個相關市場中只有一個企業,最常見的是自來水市場、輸電市場。寡占,指相關市場中只有幾個企業,常見的是電信市場、成品油市場等。
經過多年改革,國有企業數量雖然越來越少,但其平均規模越來越大,在相關市場的市場地位越來越高,因此其壟斷行為的影響面也越來越大。比如,在成品油零售市場,雖然零售商很多,但從產業鏈上看,僅僅是由“兩桶油”——中石油和中石化這兩家大型國企控制著。再如電信市場,雖然產業鏈較長、市場主體很大,但基礎電信服務僅由移動、聯通、中國電信等幾家電信國企提供。
但是,如果從反壟斷法上看國企壟斷,應當僅僅是指國企實施的壟斷行為,包括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聯合限制競爭、經營者集中,以及涉及國企的行政性壟斷。這些概念都有相應的內涵和外延,這些行為在反壟斷法上也有相應的構成要件。對這些行為的認定,還需要有反壟斷法執法機構和有管轄權的法院的認定。那么,如何理解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國企壟斷呢?
判斷壟斷有標準
在各國反壟斷法的宗旨和規制立場上看,本不應有國企和民企之分,更不應當有國企壟斷和民企壟斷的差別。但是,在許許多多的市場壟斷行為中,國企作為壟斷行為主體的概率要比民企更高,更引人關注。那么,日常用語中的國企壟斷有哪些可以依據《反壟斷法》進行規制?
首先是國有企業濫用市場支配行為排除限制競爭、牟取超額利益的行為。國企特別是大型國企,在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自來水等市場上擁有很高的市場地位,大多具備市場支配地位。如果這些國企利用市場支配地位排擠競爭對手、牟取超額利益,就可能構成壟斷。
比如,電網企業在電力接入時強制用戶購買其指定的電表和其他設備,這就涉嫌獨家交易。市區的用戶要求接入電、自來水、固定電話,當地的電網、自來水公司、電信企業(往往是國有)如果以不合理的借口不予接入,則可能涉嫌拒絕交易。前不久國家發改委反壟斷局啟動了對聯通、中國電信價格歧視的反壟斷調查,也是規制部分電信運營商提供差別待遇的例子。
如果沒有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在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自來水等領域的提供商制定過高的銷售價格、過低的購買價格,也就涉嫌壟斷高價和壟斷低價。這些行為應當受到《反壟斷法》規制。
其次是國有企業通過壟斷協議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比較常見的是大型國企的固定價格即串謀定價的行為。
還有涉及國有企業的行政性壟斷。此類行為的主體雖然是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但從現實的案例來看,受益方是國企的情形非常多。比如,有的縣、區政府,濫用行政權力,發布“紅頭文件”,限定或者變相限定吃財政飯的單位購買、使用其指定的品牌的煙、酒、農藥、化肥和住宿、餐飲等 商品和服務,其直接受益者往往是當地國企。此外,違反法律規定的經營者集中也會構成壟斷。
告國企壟斷,難!
前不久,最高法院頒布了有關壟斷民事訴訟的司法解釋。媒體的解讀大多認為司法解釋賦予了原告訴權。事實上,根據我國《反壟斷法》第50條和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因壟斷行為受到損害欲請求賠償的,當然具有相應的訴權。只是司法解釋使訴權的實現有了更強的可操作性。也正因為如此,國企在壟斷民事訴訟中成為被告的可能性,特別是在基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成為被告的可能性,較之民企更大一些。
是否可以認為,這種可操作性增強之后,將會涌現出大量的訴訟,并且被訴壟斷行為人會因此大量敗訴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呢?顯然不能過于樂觀。
以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為例,行為人一般要對被告的市場支配地位以及濫用行為承擔舉證責任。僅僅是這一項,原告提交有說服力的證明往往需要付出較大的經濟代價。而這個代價僅在勝訴的情況下才可能由被告補償。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原告獲取被告市場地位數據的難度很大。當原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證明了行為、市場支配地位、損害和因果關系后,被告只需要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理由”即可。
在我國現行法律、法規賦予了國有企業以較多合法空間的背景下,正當理由的空間較大,正當理由的證明難度也較低。因此,不能把新的司法解釋理解為使普通市場主體在對國企壟斷行為的訴訟中擁有了較高的勝訴幾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