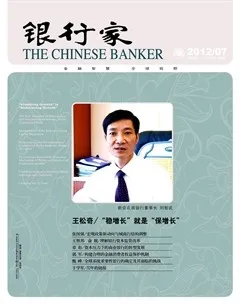“穩增長”就是“保增長”
自6月7日央行宣布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0.25個百分點開始,中國已經進入新一輪的貨幣政策寬松期。從5月份的數據看:PPI從4月份的下降0.7個百分點到5月份急降至1.4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仍然停留在個位數及CPI已降至3.0%,說明中國經濟短期要應對的已不是通脹而是通縮,是經濟增速下降過快連帶引發的就業和稅收大幅下降等新問題。我認為,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央政府在每個經濟發展轉折期出臺的重大戰略決策都是正確的,即使是2008年年底出臺的那個倍受詬病的4萬億刺激計劃,其必要性也不容置疑。本次宏觀經濟政策調節方向的轉變由防通脹轉向穩增長,在中國這種獨特的政策語境下,全國人民都知道,所謂“穩增長”就是“保增長”。這是最高決策層在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出臺4萬億刺激計劃、中央銀行自2008年9月至2010年12月7次下調利率以來的又一次擴張需求政策的開始。如果說上一次的擴張政策針對的是全球性經濟衰退,那么,本次擴張政策要解決的則是前景莫測的歐債危機及美日經濟回升乏力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拖累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增長率下滑問題。
地球人都知道,中國近兩年一直在宣傳的政策主基調是“轉型”和“調結構”,在去年3月的“兩會”上溫總理宣布了中國政府將正式下調“十二五”時期的年度經濟增長指標,但一旦經濟增長率出現將達7%左右的跡象時,方方面面都開始著急,在年度GDP達40萬億以上時,GDP每少增一個百分點就代表少增加4000多億元的社會財富及相應的就業損失。所以,大家著急也確有其道理。我一直認為,降低經濟增長率不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調結構的必要條件,當然更不是充分條件。在經濟收縮和下滑態勢已十分明顯、PPI這個先行指數已出現通縮趨向時,不失時機地首先在貨幣政策上改變名為穩健實為緊縮的調節方向(如2011年全年情況那樣)是第一要務,然后再研究財政政策、稅收政策、促消費政策等等,促成各種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如果像坊間財經評論家那樣,貨幣政策剛剛出現松動信號就提出通脹威脅及干擾調結構和發展方式轉型等問題,振振有詞地說什么既要防止經濟過熱又要防止經濟過度下滑這些振蕩空氣式的話,那純粹是在干擾中央的正確決策。
從多年來的經驗看,在中國這種政府主導型經濟里想保增長將年度GDP增速提至8%以上甚至達于9%左右可謂易如反掌。最簡便的做法就是上項目如上高鐵、上機場、上公路、上城鎮基礎設施、上生活用水生態水利等類項目,這些項目一上,經濟增長馬上加速。事實上,放眼全世界,也只有中國政府能在決策和執行上做到這一點。多年來,政府干的這些事常常成為一些經濟學家攻擊的對象,殊不知,這正是中國政府主導型經濟的比較優勢所在,那些實行民主政治體制的國家在應對經濟衰退時即使是看到了擴內需上項目的積極作用,但受制于體制和制度因素,想上項目,預算不僅難于獲得足夠的支持票數,即使決策得到足夠票數支持,項目土地征用拆遷又是無法解決的難題。所以,生活在中國,中央政府有絕對權威,國家有錢,老百姓手里也有錢,想搞什么項目就搞什么項目,想提升增長率就能實現增長率提升,我們國人應當洋溢自豪感和幸福感才對,不要動不動把這些視為中國經濟的弊端。一些經濟學家動輒就說“經濟增速低一點兒沒關系”、“對經濟下滑要從容面對”云云實際上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的行為表現。我記得艾倫?格林斯潘在一本書中曾感嘆:美國的經濟學家和政治領袖們無論怎樣調動自己的智慧也很難使經濟增長率達到3%以上,但中國常常輕而易舉地使GDP年度增速達到8%、9%甚至超過10%。格林斯潘說的是美國,其實歐洲和日本的情況也大體相若。由此可見,想增長就增長,想提速就提速實際上也是一種體制優越性的表現。
政府主導、過度依賴投資的經濟弊端,我們的決策層早已了然于胸,“十二五規劃”要解決的正是這樣的問題,制定的扶持國內消費需求,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大力發展服務業、支持環保節能項目、壓縮過剩產能、發展新興支柱產業等方針已窮盡了國人的對策智慧,所以無須多說。在制度性改革方面,大力發展民營經濟解決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問題,中央文件的各種語言十分清晰明確,所以,現在經濟學家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走下去了解些民情和基層情況,聽聽地方政府怎么想、企業怎么想、城鎮居民怎么想、農民怎么想,這比憑借教科書原理批評政府政策會多費些氣力,但會更“接地氣”,更容易提出切近實際接近市場發展規律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