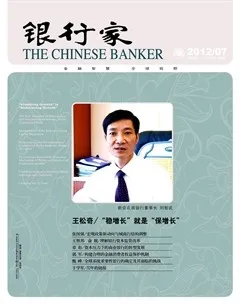一起偽造債權文書辦理 強制執行公證引發的訴訟
基本案情
某公司于1999年10月11日向某商業銀行某支行(下稱某支行)借款900萬元用于營運資金周轉,雙方簽訂了《人民幣短期借款合同》。為確保債權實現,1999年10月25日,某支行與某集團公司簽訂《最高額抵押合同》和《最高額保證合同》,約定由某集團公司以其所有的一塊土地使用權作最高額抵押擔保,同時提供最高額保證擔保。借款合同到期后,某公司由于經營管理不善,未償還到期貸款本息。
2002年1月30日,某支行、某公司和某集團公司三方簽訂《還款協議書》,約定:甲方(某公司)欠乙方(某支行)貸款本金900萬元,利息50萬元;現甲方同意于2002年2月10日前歸還上述款項,若不能還款,甲、丙(某集團公司)雙方愿意直接接受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協議經三方簽字并蓋章后生效。該協議下方有甲、乙、丙三方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簽名,其中代表甲、丙方簽名的均為陳某。同日,某市公證處出具《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公證書》,證明上述《還款協議書》上各方的簽字、印章均屬實,并賦予該公證書強制執行效力。2002年3月8日,某市公證處應某支行的申請,出具《強制執行公證書》并確定執行標的金額。2002年8月19日,某支行向某區法院申請對某公司和某集團公司強制執行。
某區法院于2002年11月13日裁定拍賣某集團公司用于抵押的土地使用權。執行過程中,某集團公司致函某區法院提出異議稱,拍賣底價遠低于市場價值,會造成債權人和某集團公司重大損失。在對某集團公司土地使用權進行拍賣過程中,由于土地使用權存有爭議,某區法院于2002年12月20日裁定案件中止執行。2004年3月30日,某支行與某集團公司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其后,某支行在法院拍賣抵押土地使用權并收到相應執行款項后,出具了《同意涂銷抵押登記證明》。
2005年7月20日,某支行與某資產管理公司簽訂《債權轉讓協議》,將本筆貸款結余的本金400萬元及相應利息轉讓給某資產管理公司。債權轉讓后,某資產管理公司又將該筆債權轉讓給第三人,該受讓第三人就該筆債權向某區法院申請恢復執行,于2006年8月17日申請凍結了某集團公司對某建筑裝飾工程有限公司70%的股權。
2007年3月,某集團公司向某區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1)認定2002年1月30日簽訂的《還款協議書》不成立。(2)判令某公司、某支行共同賠償某集團公司經濟損失5萬元并承擔所有訴訟費用。某集團公司同時向法院申請對《還款協議書》上的“陳某”簽名及某集團公司印章真偽進行司法鑒定。
2008年1月22日,司法鑒定中心出具鑒定結論:《還款協議書》上需鑒定的簽名和印章均屬偽造。案件于2008年7月移送某中院一審審理。某中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的《還款協議書》上原告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簽名,經過鑒定是虛假的,故認定原告未在《還款協議書》上簽字。原告在某區法院的執行案中已實際履行了抵押擔保責任,因此認定原告已實際履行了《還款協議書》的主要義務,且某支行作為債權人予以接受,根據《合同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在簽字或者蓋章之前,當事人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故本案中《還款協議書》應認定成立。且原告在2002年11月13日在致某區法院的函中既提到抵押擔保,又提到連帶責任,可與《還款協議書》的內容相印證。原告請求確認《還款協議書》不成立依據不足,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某集團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某高院提起上訴。某高院認為,本案爭議的《還款協議書》是以給付為內容且經公證的債權文書,具有強制執行效力。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事人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債權文書的內容有爭議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問題的批復》,對公證機關依法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如債權人或者債務人對該債權文書的內容有爭議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某集團公司起訴請求確認《還款協議書》不成立,系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批復規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故原審法院立案受理本案不當。最終,某高院撤銷原審判決,裁定駁回某集團公司起訴。
相關法律分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是:(1)當事人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債權文書內容有爭議時,能否通過民事訴訟解決;(2)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債權文書虛假的法律后果。
當事人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債權文書內容有爭議時,能否通過民事訴訟解決。本案中,某集團公司以印章、簽名系偽造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確認經公證后的《還款協議書》不成立。而某支行認為其爭議的保證合同所從屬的借款合同法律關系已在某區法院執行立案,某集團公司不得就同一法律關系另行提起訴訟,法院應駁回起訴。我們認為,在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債權文書進行強制執行的執行案件中,當事人對作為執行依據的債權文書內容有爭議時,當事人應當先向執行法院提出執行異議,由執行法院認定公證債權文書確有錯誤,作出不予執行的裁定生效后,當事人才能就爭議內容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如果在執行程序沒有終結的情況下,法院受理當事人對公證債權文書提起的訴訟并進行實體審理,則有違“一事不再理”的原則。具體到本案,某中院以《還款協議書》已實際履行為由判決駁回了某集團公司的訴訟請求,沒有對原執行案件產生影響。但假設某集團公司在某區法院已執行立案但尚未處分完畢抵押物(即《還款協議書》尚未實際履行)的情況下,又以《還款協議書》是虛假的為由,向某中院提起訴訟,而某中院受理并判決《還款協議書》不成立,則有可能導致兩個法院對同一事實的認定結果不一致,甚至產生執行回轉的法律后果。
有鑒于理論和實踐上的爭議,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作出《關于當事人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債權文書的內容有爭議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問題的批復》(下稱《批復》),明確規定:經公證的以給付為內容并載明債務人愿意接受強制執行承諾的債權文書依法具有強制執行效力;債權人或者債務人對該債權文書的內容有爭議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公證債權文書確有錯誤,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執行的,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就爭議內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對相關問題的處理方式,故某高院二審時直接依據該司法解釋的規定,裁定駁回某集團公司的起訴。
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債權文書虛假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某集團公司認為,既然經公證的《還款協議書》因蓋章和簽名被認定為虛假而不成立,則某集團公司也無需承擔保證責任。我們認為,判斷債務人是否仍須承擔責任,首先要明確“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的法律性質。
“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的法律地位,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于2000年9月發布的《關于公證機關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執行有關問題的聯合通知》(下稱《通知》)有所規定。2007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對公證機關依法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的,對方當事人可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執行,受申請的人民法院應當執行。公證債權文書確有錯誤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執行,并將裁定書送達雙方當事人和公證機關。”該條規定明確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債權文書可以作為人民法院的執行依據。
“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在實踐中一般以經公證機關公證的《還款協議書》為表現形式(通常在對《還款協議書》進行公證的公證書中,公證機關會加上“本公證書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表述)。對于這種《還款協議書》的法律性質,我們認為應理解為是對原合同(借款合同、借用合同、無財產擔保的租賃合同)的補充協議,而不是一份重新約定雙方權利義務的新的合同。一般認為,《補充協議》是指當事人對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合同內容,通過協商的辦法訂立補充協議,該協議是對原合同內容的補充,因而是原合同的組成部分。《還款協議書》一般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再次明確債務給付金額和給付期限,債權人和債務人對此都沒有疑義;二是載明債務人不履行義務或不完全履行義務時,愿意接受依法強制執行的承諾。從合同內容和訂立的目的來看,《還款協議書》是合同當事人為了節約違約救濟成本、提高解決爭議的效率而采取的措施,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經過充分協商,再次明確債權債務關系,對給付內容沒有疑義后,同意將原合同不經過法院審理而直接進入強制執行程序的補充約定。究其本質,是對原合同沒有約定的違約救濟方式通過協商的辦法訂立的補充協議,并沒有對原合同的主要權利義務條款進行變更,是非實質性的合同條款的變更。也就是說,簽Cj7PhGQ+App7uFK/Lq1w62wm3N18Dn1WjSaYtkWHp88=訂了《還款協議書》并不導致原合同關系的消滅和新合同關系的產生。在原合同已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前提下,補充協議由于存有瑕疵而未能成立的,不會影響到原合同的效力。
因此,本案中雖然《還款協議書》經過鑒定簽名和公章系偽造,即便法院最終認定《還款協議書》未成立,也不會導致原《最高額保證合同》無效,某集團公司仍須按照原保證合同的約定承擔保證責任。
相關啟示
本案屬于一起偽造債權文書辦理強制執行公證引發的擔保合同糾紛案件。雖然某高院最終駁回了某集團公司的起訴,沒有對銀行債權造成實質性影響,但案件所揭示的法律適用、被訴成因以及不良貸款的貸后管理等問題,應當引起商業銀行高度關注。
強制執行公證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本案原告某集團公司表面上的訴請是要求法院確認《還款協議書》系偽造而未成立,解除對其股權的查封,實質上則是通過另案提起訴訟程序,確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存在瑕疵,進而免除其保證責任。由于《還款協議書》上的簽名和印章確系偽造,在證據上銀行處于不利地位,若法院對此進行實體審理,很有可能作出對銀行不利的判決結果。因此,銀行只能從程序上入手,指出某集團公司訴請所屬的法律關系已由某區法院另案調處,現就同一基礎法律關系另行提起訴訟,法院應駁回起訴。本案訴訟發生于2007年,當時在審判實踐中對于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債權文書可訴性問題一直存有爭議,且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或司法解釋,銀行只能圍繞“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則進行答辯。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批復》,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了相關案件的處理原則,才明確了強制執行公證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
銀行信貸人員應當嚴格執行合同面簽制度。引發本案被訴風險的原因,主要是作為執行依據的債權文書上的保證人法定代表人簽名和其公司印章是偽造的。在銀行信貸實務操作中,由于信貸單位或擔保企業地處外地、負責人公務繁忙等種種原因,信貸員往往只是通過郵寄、非現場簽署等方式完成法律文書的簽訂,或者依賴公證機關去完成合同的簽訂,未能做到雙人現場核實法律文書的簽字蓋章,極易產生風險隱患從而引發風險事件。對于直接導致權利義務發生變化的重要法律文書,例如借款合同、擔保合同、催收函等,信貸人員一定要嚴格執行雙人面簽制度。
對于涉及擔保合同的債權債務關系謹慎采取強制執行公證的方式。《通知》明確規定了六種債權文書可以辦理強制執行公證,擔保合同并未納入其中。這是因為公證機關的基本職能是證明而非審判,對于債權債務關系復雜的,當事人只能通過審判或仲裁進行確認。銀行為了加快清收處置進度,往往通過“還款協議書”的形式將擔保債權轉變為貨幣給付之債,再通過強制執行公證的形式進入法院執行程序。但是,公證程序并未設置如訴訟般嚴謹的舉證、質證等程序,也未賦予當事人如兩審終審般的救濟渠道,極易產生爭議。本案中,就是因為對于擔保人在承擔了抵押擔保責任后,是否還須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的問題約定不明確,才最終引發了訴訟,既增加了借款人的財物負擔,也影響到債權人不良貸款的清收處置進度。
(作者單位:中國工商銀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