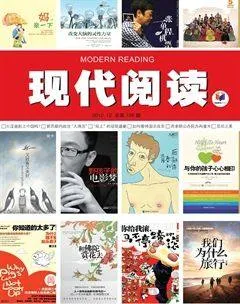中西方戰略的差異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這部他的唯一一部中國問題專著中以一位資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獨特視角,探尋了中國人的戰略思維模式;用世界視角國際眼光,重新解讀中國的過去和未來。
中國人是實力政策的出色實踐者,其戰略思想與西方流行的戰略與外交政策截然不同。在漫長的動蕩歷史中,中國的統治者認識到,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得到解決,過分強調對具體事件的完全駕馭有可能會打亂大同世界的平衡。潛在的敵人比比皆是,帝國永遠不可能享有絕對安寧。如果中國注定只能有相對安寧,它同樣暗含相對的不安寧。在陷于沖突中時,中國絕少會孤注一擲,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戰略思想更符合他們的風格。西方傳統推崇決戰決勝,強調英雄壯舉,而中國的理念強調巧用計謀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積相對優勢。
中西方的這一對比反映在兩種文明中流行的棋類上。中國流傳最久的棋是圍棋,它含有戰略包圍的意思。對弈開始時棋盤上空無一子,對弈雙方各有180枚子可用,子與子沒有差別。兩位棋手輪流在棋盤任何一點上落子,占據有利地形,同時設法包圍吃掉對方的子。棋手在棋盤各處同時展開廝殺。棋盤上每落下一子,對弈雙方的實力對比就略有消長,雙方都在實施自己的戰略計劃,并同時應對對手的棋。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結束時,棋盤上雙方的地盤犬牙交錯,一方常常僅占有微弱的優勢。
而國際象棋的目標是全勝,目的是把對手將死。絕大多數的國際象棋比賽靠消耗對方實力或偶爾靠一著妙手取勝。唯一的另一種可能是雙方握手言和,即雙方均無希望取勝。
如果說國際象棋是決戰決勝,圍棋則是持久戰。國際象棋棋手的目標是大獲全勝,圍棋棋手的目標是積小勝。下國際象棋,棋盤上雙方的實力一目了然,所有棋子均已擺在棋盤上。圍棋棋手不僅要計算棋盤上的子,還要考慮到對手的后勢。下國際象棋能讓人掌握克勞塞維茨的“重心”和“關鍵點”等概念,因為開局后雙方即在中盤展開爭奪,而下圍棋學到的是“戰略包圍”的藝術。國際象棋高手尋求通過一系列的正面交鋒吃掉對手的棋子,而圍棋高手在棋盤上占“空”,逐漸消磨對手棋子的戰略潛力。下國際象棋練就目標專一,下圍棋則培養戰略靈活性。
同樣,中國獨具一格的軍事理論也與西方截然不同。它產生于中國的春秋戰亂時期,當時諸侯混戰,百姓涂炭。面對殘酷的戰爭(同樣為了贏得戰爭),中國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種戰略思想,強調取勝以攻心為上,避免直接交戰。代表這一傳統的最著名人物是孫武(尊稱“孫子”),《孫子兵法》一書的作者。
《孫子兵法》問世已2000余年,這部含有對戰略、外交和戰爭深刻認識的兵法至今仍然是一部軍事思想經典。20世紀中國內戰時期,毛澤東出神入化地運用了《孫子兵法》的法則。越南戰爭時期,胡志明和武元甲對法國及美國運用了孫子的“迂回”和“心理戰”原理。即使在今天,《孫子兵法》讀起來依然沒有絲毫的過時感,令人頗感孫子思想之深邃。孫子為此躋身世界最杰出的戰略思想家行列。甚至可以說,美國在亞洲的幾場戰爭中受挫,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違背了孫子的規誡。
孫子與西方戰略學家的根本區別在于,孫子強調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談軍事。歐洲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認為,戰略自成一體,獨立于政治。
西方戰略家思考如何在關鍵點上集結優勢兵力,而孫子則研究如何在政治和心理上取得優勢地位,從而確保勝利。西方戰略家通過打勝仗檢驗自己的理論,孫子則通過不戰而勝檢驗自己的理論。
孫子對戰爭的理解和論述既沒有歐洲一些戰爭論著中的激情,也不頌揚個人英雄主義。《孫子兵法》冷靜的特點反映在卷首: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由于戰爭后果嚴重,慎重乃第一要義: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攻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孫子認為,勝利不僅僅是軍隊打勝仗,而是實現發動戰爭時設定的目標。上策不是在戰場上與敵人硬拼,而是折其士氣,或是調動敵人,使其陷入不利境地。戰爭復雜殘酷,因而知己至關重要。戰略于是演變為一場心理上的較量: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最理想的情況是指揮官擁有絕對優勢,從而完全可以避免交戰。其次是深思熟慮,并在后勤、外交和心理上做了充分準備后,給敵人致命一擊。孫子告誡道: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
也許孫子最重要的深邃思想是,在一次軍事或戰略的較量中,一切因素互為影響:氣候、地形、外交、情報、供應和后勤、力量對比、歷史觀,以及出其不意和士氣等無形因素。無論哪個因素,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造成軍事形勢和相對優勢的變化。
因此,一位戰略家的任務不是分析具體形勢,而是弄清這一形勢與它形成的外部條件之間的關系。沒有一種局面是一成不變的。任何現象都是暫時的,都在不斷發生變化。戰略家必須洞悉變化的走向,為己所用。孫子用“勢”這個詞表達這一特征,而西方沒有類似的概念。在《孫子兵法》中,“勢”指力量強弱及總體趨勢的不斷變化。
孫子認為,善用勢的戰略家恰如水沿山坡順勢而下,毫不費力就能找到一條最快、最容易的路線。一位成功的指揮官會耐心等待,而不是急于交戰,以避開敵人的鋒芒。他仔細觀察戰略形勢的變化并加以引導。他研究敵人的備戰狀況及士氣,積蓄己方力量,利用敵人心理上的弱點,直至出現打擊敵人薄弱環節的有利戰機。于是他出其不意,神速調兵遣將,沿著阻力最小的道路“順勢而下”,奠定優勢地位。《孫子兵法》論述的不是如何征服領土,而是如何在心理上壓倒敵人。這也是當年越南與美國打仗的戰法。
通常,中國的政治家把戰略形勢看做全局的一部分:善惡、遠近、強弱、過去與未來皆互相關聯。西方人認為,歷史是走向近代化的過程,是戰勝邪惡與落后的過程。而中國人的歷史觀強調的是衰落與復興的周期,在這一過程中,人可以認識自然與世界,卻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結果是與之融為一體。戰略與治國方略成為與對手“互斗互存”的手段,目的是化強敵為弱敵,同時加強自己一方的勢,或者說戰略態勢。
當然,“以計取勝”雖是理想結果,卻不易實現。從古至今,中國不乏殘酷的戰事,多在本國,偶爾也在國外。一旦爆發戰爭,例如秦統一中國、三國時期的戰爭、對太平天國運動的鎮壓以及20世紀的那場內戰,生靈涂炭,慘烈程度不亞于歐洲的世界大戰。最殘酷的戰事源于中國內部體系的崩潰,換言之,體現為一國內部的一種調整。對中國而言,國內穩定和抵御日益逼近的外國入侵同等重要。
中國古圣賢認為,世界永遠不可征服,明君只能希冀順應世界潮流。中國是片福地,中國人在這塊樂土上生息繁衍。從理論上講,中國文化或許可以惠及周邊鄰國。然而漂洋過海迫使異族人皈依中國文化,對中國人沒有榮耀可言,天朝禮儀因而無法向遙遠的異域傳播。
這也許是中國遺棄航海傳統的深層含義。19世紀20年代,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論及歷史哲學時指出,中國人極少漂洋過海,而是固守其遼闊的陸地板塊。陸地把人束縛在“數不清的依附關系上”,而海洋卻促使人“跳出狹隘思維和行動的禁錮”:“亞洲國家宏大的政治結構缺乏掙脫陸地束縛、走向海洋的能力,盡管它們自己瀕臨大海,比如中國。在它們眼里,海洋意味著極限,意味著陸地的終結。它們從未用積極的眼光審視過海洋。”西方人則漂洋過海,把貿易觸角伸向全世界,到處傳播其價值觀。黑格爾認為,在此意義上,困于陸地的中國——其實中國曾是世界上頭號航海大國——“與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失之交臂”。
中國挾其獨特的傳統和千年養成的優越感步入近代。這個獨特的帝國聲稱它的文化和體制適用于四海,卻不屑于去改變異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卻對與外國通商和技術革新漠不關心;它文化發達,卻受制于一個對西方探險時代的來臨一無所知的政治統治集團;它在遼闊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體系,卻對即將威脅其生存的技術文化大潮茫然無知。
(摘自中信出版社《論中國》 作者:[美]亨利·基辛格 譯者:胡利平